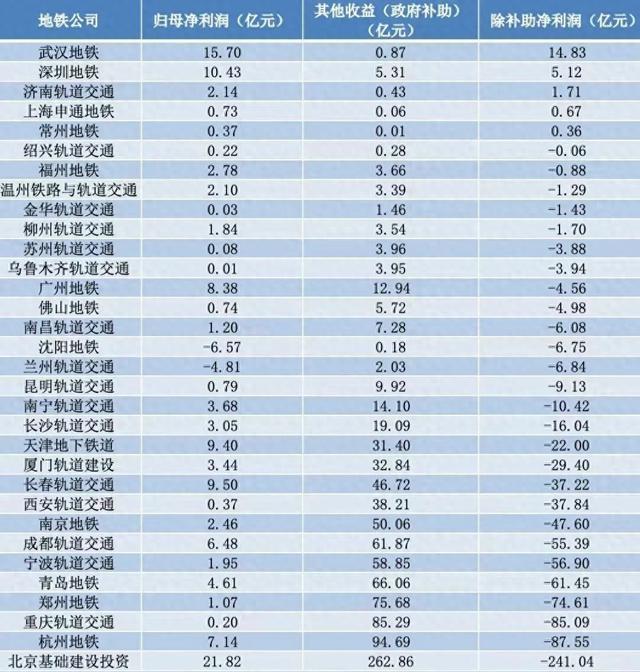美媒:獨坐地鐵的亞裔美國人開始發現彼此,在站臺和車廂裏挨在一起
《紐約時報》4月26日文章,原題:我珍愛地鐵生活,害怕失去它 自從1994年7歲時搬到紐約,我就開始乘坐地鐵。當時許多車站只接受代幣,貼着塗鴉的車廂也算是裝飾了車站。每個工作日的早晨,臉都不洗,睡眼惺忪,肚子空空的,我跟着父親穿過十字轉門。
地鐵使我們一家能夠住在布魯克林更便宜地方的同時,在曼哈頓下城和日落公園的華人社區上學和工作。但這意味着我們有時會在地鐵裏待幾個小時,比在家裏相處的時間還長。後來,因爲我們是無證移民,父母讓我獨自乘地鐵去唐人街的學校上學和回家。我很早就學會了在公共場所小心翼翼,提防任何可能攻擊我的人,或者更糟的是,質疑我的移民身份。在地鐵裏,我總感到更安全點。在地面上,我孤身一人,是弱者和“非法的”;而在地面下,我安坐於一羣人當中,是一個手裏拿着書的乘客,和其他人一樣,希望能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和一個空座位。
現在,離35歲生日只有幾個月,我坐地鐵的時間比使用其他任何交通工具的時間都要長。與其他地方相比,我覺得在地鐵裏會有一種歸屬感。但是,最近車站發生了幾起可怕的襲擊事件,我母親以前去日落公園上班的那條線上也發生了槍擊事件,我的歸屬感正在消失。於是,我到推特上呼籲大家分享自己的地鐵回憶。結果,荒誕的故事噴湧而來,但更多的是暖心的故事:好心人幫助迷路者、病人和醉漢,乘客急起身幫別人拿行李,讀者因書結緣,以及因偶遇而結下終生友誼。
如果說人行道上的紐約人不慌不忙、漠然而恬淡,那麼在地鐵裏,我們是憤怒、欣喜、恐懼、舞動、啜泣的一族。既然如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地鐵成爲我們集體痛苦的聚集地也就不足爲奇。在站臺往往能夠感受到無房者和失業者的挫折,沒有經濟、情感或醫療支持的人的焦慮,移民、亞裔和其他非白種人的擔驚受怕,因爲他們又一次成了替罪羊。
地鐵有一種獨特的力量將紐約人聚集在一起,但在這場疫情中,它也將我們推得越來越遠。當對疫情的恐懼達到頂點時,當我被吼、被吐口水、被推搡得無法忍受時,我和其他許多紐約白領一樣,選擇在家裏工作,實在要出遠門,就乘坐出租車。
現在我回到了地鐵。我注意到獨自坐地鐵的亞裔美國人開始發現彼此,在站臺和車廂裏挨在一起。這往往是不知不覺的,但它幾乎總是伴隨着我們眉頭和肩膀的細微放鬆,我們的高度警惕性稍微得到緩解。也許,在這樣一個公共空間裏,信任周圍的人甚至超越了一個寶貴的座位和一份高薪的工作,是我最想追求的地下夢想。(作者王乾,陳俊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