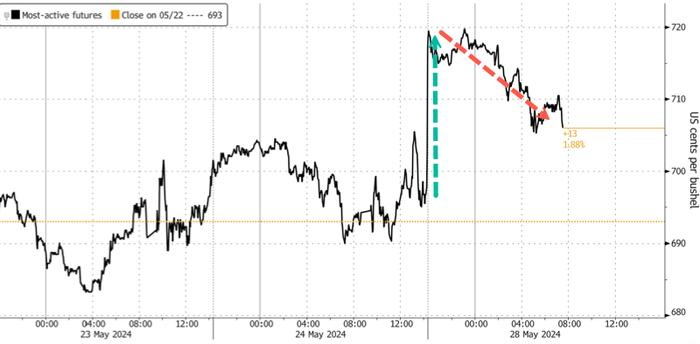程亞文:俄羅斯問題“西方化”爲何失敗
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已因俄烏衝突發生決裂,“一夜回到解放前”。曾經,俄羅斯也表達過融入西方大家庭的願望,並與西方國家一度交好。但冷戰結束後的西方在對待俄羅斯時,爲何不能像戰後對待德國那樣,將曾經的敵人納入同一個體系共享繁榮?俄羅斯問題西方化爲何以失敗告終?
回到20世紀上半葉,作爲當時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德國,對歐洲來說是一點也不亞於今天俄羅斯的一個“大麻煩”。與當時的歐洲政治家們一味致力於對德國圍追堵截相反,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很早就爲德國問題歐洲化,找到一個巴黎和會主導者們沒有想過的方案:建立自由貿易聯盟、提供國際貸款和改革國際幣制。
凡爾賽和約的戰勝者們在制定基於削弱德國的政策、建構迦太基式的和平時,沒有深入想過在一個工業化迅猛發展、貿易依賴關係極爲繁雜的時代,“整個世界是一個市場”,對戰敗國經濟的全面打壓,摧毀的不僅僅是戰敗國,更是相互聯結的國際經濟體系,進而也會殃及自身。二戰結束後,歐洲逐漸建構起一體化的經濟聯盟,全球也形成自由貿易體系,就十分清楚地證明了凱恩斯的遠見。最近70多年來,德國不再被歐洲人認爲是一種威脅,相反成了歐洲經濟政治秩序的一大支柱。
凱恩斯當年對德國問題的解決方案,爲什麼沒套用到俄羅斯身上呢?一種說法是西方國家基於對蘇聯的記憶,一直對俄羅斯心有餘悸,因而刻意防範。這種說法是有邏輯欠缺的,戰後西方國家對德國難道就不“心有餘悸”嗎?可能還是需要回到凱恩斯的方案來找原因。
在凱恩斯當年爲德國問題歐洲化苦思冥想的時候,不知他有沒有想過:他的方案實際上存在空間限度,即在將德國納入一個與其他歐洲國家共同的分享體系中時,這個體系想進一步擴容其實是很難的。在凱恩斯所處的時代,世界還是以歐洲爲中心的,亞非拉等廣大區域大部分還是歐洲的殖民地,這其實構成了他那套方案能夠成功的基礎。在一個以歐洲爲中心、世界其他區域爲邊緣的國際秩序中,爲了歐洲所能控制的世界資源和市場,也爲足夠少數歐洲工業化國家實現共同繁榮,這些工業化國家可以相互合作以便在內部建立秩序,同時將暴力外部化,即如佩裏·安德森所說,歐洲體系具有雙重特徵,“在覈心區域維護和平,而在殖民地等邊緣地區實行暴力”。
二戰結束後,歐洲殖民體系逐漸瓦解。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國際秩序的明規則,是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爲中心,體現國家主權平等原則。但“中心—邊緣”的等級性國際秩序,並未真正消失,而是作爲潛規則和隱秩序延續至今。只是以往在殖民秩序下以直接驅使爲特徵的絕對等級性權力秩序已不復存在,代之以“共同而有差別”的國際秩序,即所有國家表面上主權一律平等,但在實際運行中仍存在着權力差別。
“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是這種秩序的主要表達,所有國家都需遵守相同的“規則”,但這個“規則”的真實內涵其實並不是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爲中心,而是以西方國家爲中心,七國集團每年年會討論的不僅僅是七個國家的事情,也是整個世界的事情,它們商議好了再推動轉變爲全球“規則”。“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是“以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誰是規則制定者纔是關鍵所在。
戰後以來的美國霸權和上世紀70年代後建立起來的七國集團,就是當代版本的全球性“中心—邊緣”秩序的體現。凱恩斯的方案在這種秩序中是可行的,但如果去中心化,這個方案就會遇到瓶頸。一個很多後發國家沒意識到也不願看到的現實是,世界並不需要那麼多工業化國家。在全球性分工體系中,規則制定、貨幣供給和工業品生產,實際上是少數國家的事情,其他國家如果也想加入其中,就有可能瓦解少數國家的優勢地位,這是掌握規則制定權和貨幣主導權並以知識產權維持技術優勢的先發國家不願看到的。中國最近幾十年來出人意料的經濟增長,打破的正是戰後以來的“中心—邊緣”國際秩序,進而觸及以西方國家爲中心的潛規則。美國將中國定義爲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擺出一副不將中國打垮絕不罷休的架勢,主要原因就是它認爲中國的發展動了西方國家奶酪。
如果說在蘇聯解體後的最初幾年,俄羅斯對成爲西方國家還懷有念想的話,那麼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個念想已一步步破滅,甚至對與西方國家搞好關係、實現共同發展都已不抱希望。70多年前吸納德國成爲少數工業化國家的空間,今天已經沒有了,德國問題歐洲化的解決方案,也已不可簡單套用成今天的俄羅斯問題西方化。現在俄羅斯既未能加入歐盟,也未能走進北約,相反還進一步受到北約東擴的威逼,這反映了當今世界迄今爲止最爲有效的區域共同體以及世界最大軍事集團的擴容限度及其本質所在。
俄羅斯之前對成爲西方國家一員的期望,與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定位,是嚴重錯位的。西方並不需要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不可能給俄提供成爲發達經濟體的空間,而是希望它永遠處在初級產品提供者的邊緣位置。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國家以自己而非聯合國的名義對俄發起一系列欲置之於死地的制裁,這也讓其他非西方國家再度警醒,它們看到了70多年前的國際秩序和權力結構在當代回潮。在美國總統拜登炫耀北約的團結時,非西方國家也清楚看到當代國際關係在“主權平等”名義下的實質,少數西方國家壓倒性的“暴力”集結能力和對不順從者的脅迫,仍是當今國際秩序的一個核心特徵,也是當今世界的問題根源所在。(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