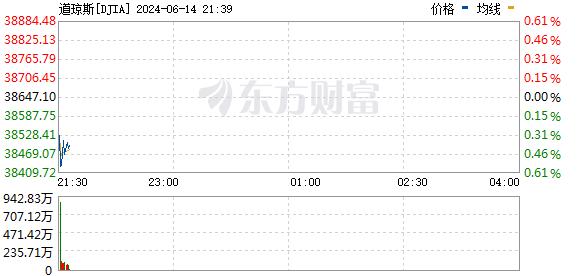WeWork興衰:品牌還是網絡?
來源:李翔李翔(gh_b19aab226944)
5月北京疫情,把兩部講創業公司的美劇看了一遍。一部是講Uber的《超蓬勃SuperPumped》,另一部是講WeWork的《初創玩家WeCrashed》。
Uber和WeWork這兩家在2010年前後誕生的公司,一度是美國乃至全世界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這兩家公司也有很多的交集和相似點。比如它們都是Benchmark投資的公司,後來也都得到了軟銀大手筆的支持。兩家公司都有一個“無法無天”、“超級熱血”的創始人,然後兩家公司今天也都被拿來當作獨角獸泡沫的代表。我查了下,2022年6月初,WeWork的市值是52億美元,Uber是500億美元。但在還沒有上市的時候,WeWork的估值一度高達470億美元,Uber曾傳出過估值1200億美元。
兩家公司的創始人也都被董事會驅逐出了自己創辦的公司。《初創玩家》裏面就有一個鏡頭,WeWork創始人亞當·諾伊曼打開電視,看到Uber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被Benchmark牽頭的董事會驅逐的新聞。然後在電話裏,他的同事緊張地問他:“我們跟Benchmark的關係還好嗎?”
看完美劇,想着什麼時候回頭再看一下寫這兩家公司的書。剛好,寫WeWork的書中文版剛出,名字叫《億萬負翁》(billion dollar loser),就先讀了這本,然後寫了這篇筆記。
1
第一個問題是,WeWork的估值邏輯是什麼,爲什麼在沒有上市的時候,曾經被投資人認爲價值可以高達接近500億美元,現在卻只值52億美元,幾乎只有曾經的十分之一?
一個原因是,WeWork身處在一個大市場裏,這個行業的天花板很高,如果它能證明自己可以在這個大市場中贏下一個大份額,那它就能證明自己的價值。這是風險投資人的邏輯。
Uber的投資人比爾·格利在跟卡蘭尼克翻臉之前,一直是Uber高估值的辯護者。他曾經跟人爭辯過,爲什麼Uber的高估值是合理的。這裏面就有一個怎麼看待Uber所處的市場的問題。如果你認爲Uber所處的市場是出租車市場,這只是一個1000億美元的市場,但是如果你認爲Uber對標的應該是整個行駛車輛的市場,那這個市場總量可以達到1.3萬億美元。公司的天花板一下就高了很多。
同理,如果認爲WeWork的市場是共享辦公市場,那麼整個市場的盤子就很小。但是,如果把公司所在的市場定義爲整個辦公空間和寫字樓,在美國,這個市場是15億美元。在全球,接近200萬億美元。(全是書裏的數據,沒覈實過。)
大市場中才會有大公司出現。所以書裏面就說,“哪怕2%的市場份額,就可以讓亞馬遜的營收看起來微不足道。”
接下來的問題是,線下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非常分散的行業,要做到市場份額集中,非常之困難。
這裏面當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房地產本身非常的重資產。如果你自己持有物業,會佔據大量的資本。就WeWork的例子而言,WeWork更像是一個二房東。它從持有物業的地產公司手裏把房子租過來,經過裝修之後再轉租給需要辦公室的公司。即便如此,也需要大量的資金。因爲公司需要跟業主簽訂一個比較長的租約,一方面是在拿物業的時候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有較長的租約,也好去做裝修等投入。這也需要大量的錢。絕大部分的房地產行業公司都有很高的負債率,這絕不是因爲房地產公司的創始人特別喜歡借錢。
2
除了錢的問題之外,另外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你怎麼能夠在一個分散的市場中去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並最終佔據一個大的市場份額?
21世紀有一個詞對創業者和投資人無異於魔法,這個詞叫:網絡效應。傳真機具備網絡效應,電話具備網絡效應,電子郵箱具備網絡效應,facebook具備網絡效應,微信具備網絡效應。簡單來說,網絡效應就是,加入這個網絡的節點越多,整個網絡的價值就越大,對其中每個節點的價值也越大。而且,網絡擴張到一定程度,它會裹挾着所有沒有加入網絡的節點,也必須加入。想想看,如果不使用微信你會有多不方便,這意味着你幾乎要失去所有的聯繫人。
但是對於像WeWork這樣的線下公司而言,就很難具備網絡效應。我的房東多租出去了幾套房子,跟我好像確實沒什麼關係。我不會因此獲益。
但是線下的原子世界的公司有另外一個武器:品牌。品牌可以幫助公司擴大市場份額,雖然品牌可能不能像網絡效應那樣,讓公司在這個市場中達到接近壟斷的地位。
我記得在書裏面看到過一句,WeWork一位核心高管跟創始人亞當·諾依曼的分歧之處就是,前者認爲WeWork應該做共享辦公領域的耐克,盡心打造並維護自己的品牌,讓越來越多用戶選擇自己。耐克賣鞋子,確實不能像facbook或者微信那樣具有網絡效應,裹挾越來越多的用戶加入一張網絡。但是耐克確實可以通過不斷把自己的品牌跟運動精神綁定在一起(這裏面當然也需要很多方法和耐心),賣出越來越多的運動鞋。到今天耐克也有接近2000億美元的市值。
但是在品牌還是網絡裏,亞當·諾依曼選擇的是網絡。他希望WeWork不是一家辦公室租賃公司,而是一個網絡公司。
他跟全公司宣佈,WeWork不是一家房地產公司,不是一個精品辦公場所,而是一個“實體社交網絡”。他把WeWork和另外兩家共享經濟巨頭相提並論,“我們碰巧需要大樓,就像優步碰巧需要汽車,就像愛彼迎恰好需要公寓。”
亞當·諾依曼還曾經跟Facebook的投資人和曾經的總裁肖恩·帕克這麼介紹自己:“我在做社交網絡,只不過是實體社交網絡。”在美劇《初創玩家》裏,也有亞當·諾依曼爲了吸引孫正義的投資,拼命要給WeWork增加一些科技元素的情節。
在他的設想裏,WeWork的會員本身會形成一個有價值的社交網絡,他們彼此之間可以交朋友、採購彼此的服務和產品等等。
在那之後,WeWork還提出過不少時髦的理念。比如,比照“軟件即服務”提出的“空間即服務”,公司不需要再打理自己的房地產物業,而是將實體空間的管理外包給WeWork。再比如,“Powered by We”、“WeOS”,公司可以把所有空間需求外包給WeWork。這也都是借用了硅谷科技公司的邏輯。
在WeWork的招股書裏,“社區”一詞出現了150次,“平臺”一詞出現了170次,“辦公空間”僅出現了9次。
3
如果能證明公司可以在一個規模巨大的市場裏面佔據一塊大的份額,那麼錢就不是問題。畢竟,這不就是風險投資人要解決的問題嗎?
WeWork在2012年時已經證明了自己可以盈利,《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那一年WeWork的利潤是170萬美元。也就是說它的單位經濟模型是跑的通的。如果單位經濟模型成立,如果快速大規模複製的瓶頸就是錢,那麼在2012年前後,市場上最不缺的就是錢。一方面,經濟整體正處於瑞·達利歐所說的擴張週期,爲了讓美國經濟快速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和隨後歐債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央行願意給市場提供錢;另一方面,2012年Facebook的上市,也刺激着風險投資人們去尋找下一家這樣的公司。
Benchmark合夥人鄧利維就對他的同事們說:“我們投點錢吧,他會搞出名堂來的。”之後有越來越多的人把錢放了進來。包括中國的私募基金弘毅投資,以及大玩家孫正義的願景基金。
風險投資人把錢給到創業公司,然後讓公司把錢作爲槓桿去獲得高增長和高市場份額。
領英的創始人裏德·霍夫曼提出了一套新的增長理論“閃電式擴張”。Benchmark投資的Uber和WeWork都是閃電式擴張的信奉者。儘管這兩家公司都已經走到了線下。
亞當·諾依曼在2012年時就已經想清楚,他希望儘可能快地做大規模。他曾跟人解釋說,他只有一個目標,“我的工作是讓公司不斷成長,大到不能倒下。”
2018年時,亞當·諾依曼去拜訪星巴克的傳奇CEO霍華德·舒爾茨。舒爾茨建議亞當不要執迷於增長,而是着手去解決公司未來會面對的問題。舒爾茨說,他自己希望星巴克能有6個月的時間不要增長,這樣就有時間去解決困擾星巴克很多年的問題。
舒爾茨的建議顯然跟閃電式擴張的邏輯是相反的。所以,在飛機上,亞當·諾依曼跟幾名員工分享完舒爾茨的建議,然後說:“去他媽的。”
亞當·諾依曼當然有權利決定自己採用哪種增長方式。不僅僅因爲他是創始人和CEO,也因爲他在董事會上擁有超級投票權。
這也是閃電式擴張時期常見的安排。因爲閃電式擴張需要花很多錢,花很多錢意味着要出讓很多股份去融資。爲了在能融到很多錢的情況下還讓創始人安心掌舵公司,那就只能給創始人超級投票權了。所以,扎克伯格有超級投票權,優步的卡蘭尼克有超級投票權,幾乎沒有哪個創始人沒有超級投票權的。對創始人的絕對信任,甚至能成爲投資人的競爭優勢。DST的Yuri Millner當年投資Facebook時創下了這個先例。他放了2億美金進去,把Facebook估值推高到100億美金,但是他沒有提任何要求,也不要董事會席位。
4
這個故事的結局現在來看,並讓人滿意。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創始人嗎?創始人肯定不是完全無辜的。在《初創玩家》裏有大量的關於亞當·諾依曼和他妻子的古怪行爲的描述,這讓這部劇特別好看。真實的亞當·諾依曼也確實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比如他向自己創辦的公司收品牌授權費,他自己買下樓然後租給公司等等。
WeWork後來跟這位創始人一樣呈現出一種失控的狀態,似乎什麼都想做一點:提供公寓服務的WeLive,提供教育服務的WeLearn,提供自行車服務的WeBike,提供送餐服務的WeEat,身房品牌WeMove,還有設想中的WeBank、WeSail等。書裏有一個細節說,WeWork的員工詢問會員關於WeWork做能量飲料的想法,對方回答說:“咖啡機時不時沒有牛奶,能先解決這個問題嗎?”
創始人失控跟超級投票權有關。Benchmark投資了WeWork的合夥人鄧利維在董事會決定給創始人超級投票權時說:“我只想留下一句話讓你們想想,絕對的權力一定會導致腐敗。”
孫正義在願景基金的LP會議上說:“我們創造了一個怪物。”但正是孫正義幾十億美金幾十億美金地給諾依曼錢,也是他一直在鼓勵亞當·諾依曼變得瘋狂一點,是因爲只有瘋狂的創始人才能創造出瘋狂的回報。《億萬負翁》的作者提出了一個假設,如果亞當·諾依曼沒有碰到孫正義,這家公司會發生什麼?作者的回答是:公司會在2017年的時候以十幾億美金的估值上市,增長會放緩,但是已有的WeWork辦公空間會帶來切實的收入和利潤。
但是,其實WeWork估值大幅回撤的核心問題還是在於:WeWork可以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去取得增長?是品牌,還是網絡?一家重運營成本的線下公司,是否有可能閃電式擴張?
今天看來,答案傾向於不能。它應該努力經營自己的品牌,一步一個腳印去增長,一點一點去積累市場份額,而不是寄希望於可以像互聯網平臺那樣能夠靠閃電式擴張迅速拿下一塊大的市場份額,甚至狂想最後可以獲得一個壓倒性的市場份額。
所以,還是有品牌的生意和網絡的生意的區隔。可能這也正是Facebook可以把上市公司名字改成Meta,但我們無法想象可口可樂或者耐克把公司名字給換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