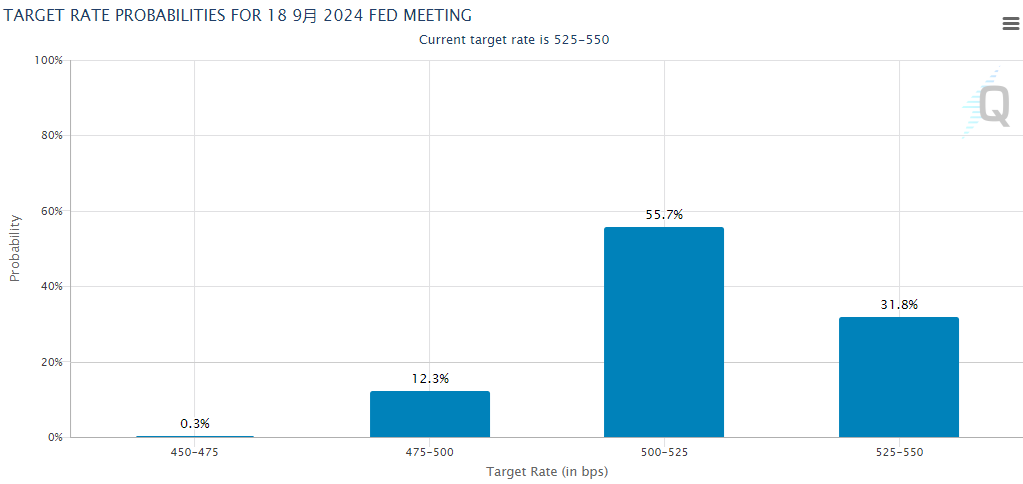執法人員的豁免權爭議:來自美國最高法院的庇護
編者按:本屆最高法院對美國民衆的權利做出了諸多限制,其中法院對於槍支攜帶權以及墮胎權的裁決更是引起了全美關注。然而,最高法院在另一批案件中,對於美國民衆如何通過法律途徑起訴侵犯自身的公職人員施加了種種限制。本文作者Matt Ford在分析最高法院的諸多裁決後指出,由於來自法院的庇護,民衆追究侵害個人權利官員責任的手段日漸減少,向法院尋求補救措施已經變得愈發困難。本文原載於《新共和》,作者Matt Ford,中譯略有刪減。

由本屆最高法院處理的,最引人注目的案件與美國民衆的憲法權利息息相關,包括推翻紐約州的控槍法律,取消了民衆在戶外攜帶槍支的限制;支持高中橄欖球教練在比賽後帶領團隊成員進行祈禱的行爲;以及否認了憲法中允許女性墮胎的權利。大法官們擴大了民衆在某些領域的權利,限制甚至消滅了另一些領域的權利。
然而,另一批同樣涉及到民衆權利的案件卻缺乏社會的關注。在這些案件中,最高法院討論了“當美國民衆的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們是否可以採取相應措施”的問題。民衆可以起訴相關官員嗎?他們能否向法院尋求補救措施?對於這些問題,大法官們給出了相當一致的否定答案。
當然,最高法院從未在某一項裁決中宣佈“政府官員不應該對其行爲負責”。但過去幾屆的大法官都在裁決中做出了暗示。這導致個人在法庭上爲自己辯護的能力不斷受到侵蝕,而那些侵犯他們權利的官員則完全不受懲罰。
當一名公務員(大部分情況下是警察)侵犯了自身的憲法權利時,美國民衆會如何反應?最直接的步驟是對他們提起訴訟。如果侵權者是州或地方官員,訴訟人在理論上可以使用1983條款(Section 1983)發起訴訟。這項重建時代的條款,允許訴訟人在聯邦法院對那些以官方身份侵犯個人權利的州或地方官員提起訴訟。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個人在聯邦法院以憲法爲由起訴警察或公職人員時,訴訟的基礎都基於1983條款。
在維加訴泰科案(Vega v. Tekoh)中,特倫斯·泰科(Terence Tekoh)試圖利用1983條款起訴一名洛杉磯警察。據悉,該警察在審問他時沒有發出米蘭達警告;身爲護士的泰科被指控性侵了一名病人。雖然檢察官在審判中使用了泰科在未收到米蘭達警告的情況下做出的陳述作爲證據,但陪審團認爲泰科的性侵犯罪名不成立。泰科起訴了該名警察以及其他人,因爲他們在審訊前沒有對泰科進行米蘭達警告,泰科的律師認爲這構成了脅迫。
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裁定,允許泰科進行上訴。法院指出,在刑事審判中,在警方未發出米蘭達警告的情況下獲取證詞,並在後續審判中使用該證詞的行爲違反了第五修正案(以法定程序來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但最高法院對此表示反對。法院最終以6票贊成、3票反對的結果,做出了遵循意識形態路線的裁決,裁定米蘭達規則純粹是預防性措施,不屬於1983條款的訴訟範圍。

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
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在爲法院撰寫判決書時解釋道,“雖然允許根據1983條款提出米蘭達索賠的好處微乎其微,但對法院而言,需要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他指出了“司法經濟”(指拒絕裁定一個案件中提出的一項或多項訴求,可以保護法律制度或特定法院的有限資源)的必要性;如果聯邦法院不得不重新審視州法院認定的事實,這將會侵犯司法經濟。他警告說,允許該訴訟將在州法院和聯邦法院之間造成“不必要的摩擦”。他還列出了潛在的“程序問題”,簡要概述了法院需要裁決的其他法律問題。雖然他強調了米蘭達本身作爲程序規則的侷限性,但阿利托明確表示,對泰科有利的裁決只會給法院帶來更多工作。
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反對意見中認爲,阿利托和大多數人完全誤解了法院的米蘭達判例。在她看來,過去的裁決清楚地將米蘭達規則描述爲一種獨特的憲法規則,而不是僅僅在審判中排除“未遵守該規則情況下收集到的證據”,並將其作爲執行第五修正案的預防措施;這創造了一個附帶的權利。卡根還強調了該裁決將會對那些權利受到侵犯的潛在訴訟人所造成的影響;與泰科不同的是,他們被陪審團判定有罪並在監獄服刑。
她引用過去的裁決寫道,原告“可能會在上訴或人身保護令中成功地推翻定罪”;但如此一來,他又該如何補救自己所遭受到的傷害呢?1983條款的意義就在於提供這樣的補救措施——因爲補救措施是“憲法保障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多數人通過否認補救措施損害了原告的權利。
卡根提到了法院幾周前對埃格伯特訴博爾案(Egbert v. Boule)做出的裁決。該案的核心問題同樣是“當聯邦政府的一名僱員侵犯個人權利時,個人是否可以向聯邦政府尋求賠償”。此案涉及到了一個不尋常的商人,他在美加邊境擁有一家名爲“走私者客棧”的旅店。此人通過幫助人們非法進入加拿大來獲利,同時也是在邊境巡邏的聯邦執法機構的線人。
這起訴訟源於一起事件:一名邊境巡邏人員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闖入了旅店老闆羅伯特·鮑勒(Robert Boule)的房子,將他推倒在地並打傷了他。據稱該名人員還對他進行了報復,因爲他向邊境巡邏人員的主管提出了行政申訴。博爾提起了訴訟,聲稱這名特工在最初的闖入事件中侵犯了他的第四修正案權利(旨在禁止無理搜查和扣押,並要求搜查和扣押狀的發出有相當理由的支持),在後續的報復中侵犯了他的第一修正案權利。
1983條不適用於聯邦官員,所以博爾在本案中不能依賴此條款來起訴特工。相反,他提起了所謂的“比文斯訴訟”(Bivens lawsuit),該訴訟以1971年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命名。在該裁決中,法院認爲,一個名叫韋伯斯特·比文斯(Webster Bivens)的個人有權起訴六名侵犯其第四修正案權利的聯邦緝毒人員。儘管國會尚未建立允許他發起訴訟的理由,但法官們認爲比文斯發起訴訟的原因隱含在憲法文本中。

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
比文斯案恰逢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從自由派大法官轉向中間派,又轉向保守派的時期。從那時起,後來的幾代大法官抵制將比文斯案的裁決擴大到其他憲法權利,並在某些情況下試圖削減該案件的影響。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法官在埃格伯特案中撰寫的多數意見,主張將比文斯的索賠主張進一步縮小。托馬斯總結道,如果聯邦政府爲公民提供了一種“替代機制”,讓他們在自身憲法權利受到損害時尋求補救,那麼下級法院就不能允許比文斯的索賠訴訟繼續進行。
他寫道:“只要國會或行政部門建立了一個具有足夠威懾水平的補救程序,法院就不能通過疊加比文斯案的裁決來提高補救標準。”換言之,因爲邊境巡邏隊有一個行政申訴程序(這個程序建議在這個案件中解僱這名特工),但由於未知的原因,該程序沒有能夠得到執行,導致了博爾不能援引比文斯案來起訴這名特工。托馬斯強調,行政部門的程序“不允許個人對結果提出上訴”的做法是完全可接受的。

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
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對此發表了異議。她指責多數意見設置了新的標準,通過近乎捏造事實的方式,來達到對代理人有利的結果。“現有的先例允許博爾在聯邦法院爲他受到的傷害尋求賠償,”她寫道,“法院爲了避免這一結果,不惜花費巨大的代價,改寫了它在五年前制定的法律標準,將對於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擴展到面目全非的程度,並從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找到了另一種補救結構。”法院關上了博爾索賠的大門,也限制了那些試圖通過比文斯案尋求索賠的訴訟人。事實上,法院將在何種情況下支持比文斯的索賠主張,已經變得難以確認。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對有罪不罰(impunity)的熱情並非永遠與意識形態路線保持一致。最好的例子可能是美國訴祖巴伊達案(United States v. Zubaydah),該案圍繞着中情局在“反恐戰爭”期間對在押人員使用酷刑產生的法律後果展開。原告阿布·祖巴伊達(Abu Zubaydah)今天仍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灣設施中。他和他的律師試圖傳喚兩名代表波蘭檢察官的前中情局承包商,據悉兩人與在中情局的黑牢中,對祖巴伊達實施的酷刑有關。
司法部根據國家機密原則尋求撤銷傳票,該原則允許政府對“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證據”實施扣留。但與美國的核武器設計或諾曼底登陸計劃不同的是,中央情報局對祖巴伊達的處理是衆所周知的公開記錄。在訴訟過程中,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結論是,國家機密特權不適用於公開的信息。
然而,在一個支離破碎的裁決中,最高法院命令下級法院駁回此案。“我們同意政府的觀點,有時進入公共領域的信息可能仍屬於國家機密特權的範圍,”大法官斯蒂芬·佈雷耶(Stephen Breyer)寫道,“政府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不論兩名承包商(米切爾和傑森)是否同意提供祖巴伊達尋求的信息,都會嚴重損害國家安全利益,即使這些信息已經通過非官方渠道公開。”
即使是在事實已經廣爲人知的情況下,這項裁決也將使人們更難追究政府在國家安全背景下犯下的違憲行爲。尼爾·戈薩奇法官(Neil Gorsuch)指出政府的主張是荒謬的。“我們討論的事件發生在20年前,”他在一份異議中寫道,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也參與了編寫,“這些祕密早已被破解。關於他們的官方報告,書籍和電影已經出版。儘管如此,政府仍試圖以涉及國家機密爲由駁回這一訴訟。今天,最高法院默許了這一請求。結束這場訴訟可能會讓政府避免更多的尷尬。但我們不應該假裝這一判決會守住任何祕密。”
在口頭辯論中,法院意外地發現了給國家安全主張提供如此廣泛的迴旋餘地所帶來的後果。祖巴伊達的案件主要圍繞獲得兩名承包商關於前者在波蘭遭受的酷刑的證詞。佈雷耶法官詢問祖巴伊達的律師,“祖巴伊達本人不能證明他的經歷嗎?”他的律師回答說,政府仍然將他的當事人單獨關押着。這似乎讓佈雷耶感到震驚,他指出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並問道:“你沒有申請人身保護令或採取其他方式讓祖巴伊達獲得自由嗎?” 律師回應稱,“在過去的 14 年裏,華盛頓特區一直存在着一項懸而未決的人身保護令程序。”
當涉及到有限制的豁免案件時,法院對有罪不罰的傾向達到了頂峯。有限制的豁免權(qualified immunity)是一種司法創造的理論,如果原告不能證明被公職人員侵犯的權利在當時是“得到明確確立的”,法院就可以駁回涉及1983條款的案件。這一框架經常幫助官員免於承擔其行爲的法律後果。該原則一直受到下級法院法官、不同意識形態的法律學者以及一些法官的批評。
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法院很少直接審理有限制的豁免案件。相反,它往往通過糾正下級法院的裁決,而非口頭辯論或多數人簽署的意見來解決這些問題。儘管一些大法官持反對意見,但最高法院依然拒絕進一步的審查,將下級法院難以解釋的決定予以保留。對於這屆最高法院而言,最好的例子是拉米雷斯訴瓜達拉馬案(Ramirez v. Guadarrama);法院在今年任期的最後一天宣佈,它不會受理該案件。
這起訴訟是由賽琳娜.拉米雷斯(Selina Marie Ramirez)代表她自己、她的兩個孩子以及她丈夫加布裏埃爾·奧利瓦斯(Gabriel Eduardo Olivas)的財產發起的。2017 年,奧利瓦斯經歷了精神健康危機,這家人撥打了911,在此期間他往身上澆上了汽油,並威脅要在家中點燃自己。當他的妻子和孩子懇求他別這樣做時,三名警察趕到了現場,其中一名警察明確警告另外兩人不要對奧利瓦斯使用泰瑟槍,因爲這可能會點燃汽油。
這兩名警官無視警告,對奧利瓦斯使用了泰瑟槍,引燃了汽油。由此引發的大火導致奧利瓦斯死亡,燒燬了他家的房子。拉米雷斯起訴警官對奧利瓦斯過度使用武力,並違反了第四修正案。起初,法院拒絕了警察發起的對於 “有限制的豁免權”的申請。隨後,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推翻了這一裁決,稱警官們享有豁免權,並認爲“鑑於警官們面臨的可怕場景,涉及對生命和財產的直接破壞,使用泰瑟槍並非等同於使用不合理或過分的武力。”
這一裁決遭到了第五巡迴上訴法院一些成員的強烈批評,後來整個上訴法院複審了這一裁決並維持了原判。最高法院的三名自由派法官也批評了其他法官拒絕重審此案的決定。索托馬約爾寫道:“根據這些指控,警官們選擇使用武力,是因爲他們知道這將直接導致他們聲稱試圖避免的結果;也就是說,爲了防止奧利瓦斯自焚燒燬房子。警察在接到警告說使用泰瑟槍很可能導致奧利瓦斯自焚的情況下,依然電擊了他。”然而,這種荒謬的做法並沒有能夠說服其他法官進行干預。
最高法院保護公職人員免受懲罰並非什麼新現象。這一做法大多建立在早先案件的基礎上,這些先前的案件縮小了1983條款或比文斯案的影響,也限制了其他追究官員責任的機制。值得強調的是,在美國民衆憲法權利的性質引起如此廣泛辯論之後,民衆更加關注最高法院對於某一項憲法權利的界定、擴大或縮小;在目睹了本屆最高法院的做法後,民衆也需要意識到,當官員侵犯這些權利時,要確保他們的責任會被追究。
責任編輯:吳劍 SF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