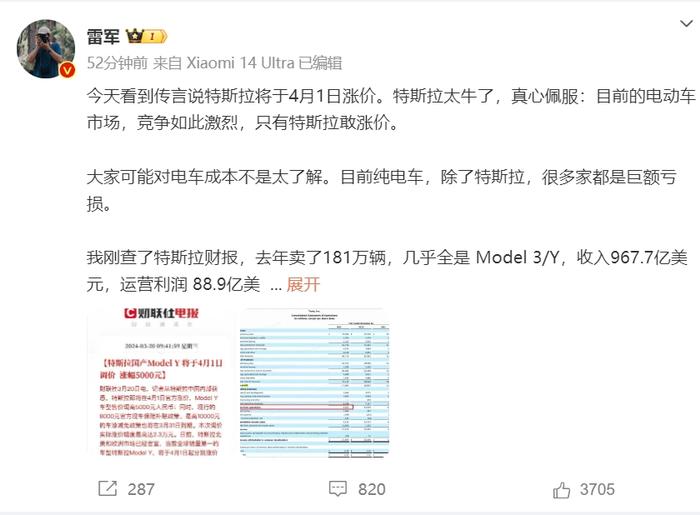760元推動一次網暴:起底“水軍產業鏈”
又傷害到許多普通人的心靈
這些行爲的發生
又往往伴隨着一系列的獲利行爲
760元能做什麼?2020年5月30日清晨,廣州市民李琳將這筆錢微信轉賬給一個陌生人,購買的是標價500元的10萬微博“殭屍粉”、160元的2萬點贊數和100元的1萬轉發數。數據是水軍賬號刷出來的,不代表真實的關注和互動,卻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引發了一場網絡暴力“海嘯”。
數據營造了虛假的聲勢,卻可能騙過平臺的算法,把微博推薦給更多真實的用戶。李琳在微博裏控訴,她的女兒被班主任“體罰吐血”,並附上了“血衣”照片。到了那日中午,這條微博轉發和評論都超過50萬,爬到了熱搜第一,話題閱讀量近6億。憤怒的流量如同海嘯,卷向了現實,當事班主任遭受網暴,個人信息被人肉搜索,學校迫於壓力令其停職。當地行政和執法部門全力調查此事,調取監控後卻發現,聳人聽聞的情節是編造的,“血衣”是用化妝品兌水染的。李琳和刷數據的“老闆”都因尋釁滋事罪獲刑。
互聯網構建了當下民衆的公共生活,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交織在一起,依附於虛擬空間的罪惡,也從隱祕處滋長出來。近幾年,公安機關網安部門連續開展“淨網”專項行動,持續打擊“網絡水軍”。今年下半年,全國範圍內正在開展爲期6個月的依法打擊整治網絡水軍專項工作。
“網絡經濟是信用經濟,網絡水軍的存在,會導致信息的虛假和失衡。”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懷勝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互聯網黑灰產業鏈中,網絡水軍附着於“網絡惡勢力”“網絡黑社會”上,損害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危害網絡空間的公共秩序,危害國家安全,侵害個人的人格權和名譽權。
而在一起又一起的網暴事件中,不時能看到網絡水軍的身影,以及越來越完整的黑色產業鏈條。
購買推廣
李琳的女兒6歲了,從幼兒園升上了一年級。2019年12月10日下午,她從學校接到女兒,發現女兒的秋衣秋褲溼透了。女兒告訴她,自己和另外四名同學在學校操場罰跑10圈,中間伴有咳嗽、氣喘和嘔吐。李琳一面帶女兒就診,一面在微信羣和朋友圈“聲討”老師,學校與教育局與她開了幾次協調會,但她認爲事情沒有獲得重視,學校偏袒老師。
李琳成長於單親家庭,極度缺乏安全感,總認爲別人會對她不利。自從認爲女兒被老師“體罰”,她就“陷進去了,變得有點沒辦法出來”。辦案人員透露,即使有監控視頻和諸多客觀的證據證實,李琳的女兒只是被罰跑了圈,嘔吐是因爲勞累,但李琳在供述中細緻地描述了女兒“吐血”“哮喘發作”的過程,“這些細節讓你覺得那段經歷非親歷無法獲知,如果不是看到監控,我們也會同情她。”
李琳是短視頻平臺美妝博主。在社交媒體上,她爲自己創作了虛擬身份:名校畢業,家庭美滿,正打算全家出國生活——這與她的真實生活存在落差,她學歷一般,曾經當過空姐,丈夫總是離開她滿天飛,她辭去工作後,主要承擔了育兒責任。
2020年3月,李琳在微博上註冊了賬號“小島裏的大海”,3月21日、3月28日、4月6日、4月11日和5月30日,多次發佈老師體罰學生以及孩子所在小學和校長不作爲的內容。在2020年5月30日之前,她的微博轉發量在1000次以內,閱讀量有上千萬,但這些流量在微博屬於不溫不火,並未引起大量“圍觀”。

微博賬號“小島裏的大海”發佈的“血漬”校服照片等內容。
但在2020年5月30日這天,李琳在清晨6點再發微博,描述“女兒坐到車上就大口吐血,弄的身上都是血”,並附上了一張此前沒有發表過的佈滿鮮紅“血漬”的校服照片。此外,她還稱在5月27日凌晨2時出門倒垃圾時,被班主任威脅及毆打。
與此前發佈的其他微博不同,李琳爲這條微博花錢買了“推廣”。據她供述,那張佈滿“血漬”的校服照片是“推廣人員”建議她增加的,目的是更好地佐證她的猜想。但她女兒並沒有吐血,於是她用化妝品兌上水,製作出了鮮紅的液體,淋在女兒的校服上。
“推廣人員”是誰?李琳說,她曾經給自己的美妝視頻購買一些點贊和評論。對於推廣她女兒的事,就找到原來買過點讚的人推廣自己的微博。出售這些推廣數據的人,是她在二手轉賣平臺“鹹魚”上找的。
隨後,李琳那條微博火了。在李琳付款4個小時後,附有血衣圖片的微博就上了熱搜。“有圖有真相”的驚悚細節吸引了大量關注,到中午時,這條微博的轉發量就達到589467,評論數爲566263,閱讀量爲181744355,而相關微博話題躥至熱搜第一,閱讀量5.4億,討論數19.6萬。
大量網民譴責學校和班主任,呼籲有關部門徹查此事。2020年5月30日中午,廣州市白雲區教育局發佈通報,稱聯合公安等部門介入,成立專項調查組進行調查。

2020年7月21日,警方在山東一居民小區,抓獲涉案嫌疑人4名,現場固定電子數據,查扣電腦、手機、賬務賬單等涉案物品一批。
2020年5月31日凌晨,廣州白雲公安通報了“反轉”消息。在2020年兒童節這天,李琳被警方帶走。據警方通報,李琳故意編造虛假信息,通過註冊微博、微信賬號方式,冒用其他家長身份惡意散佈傳播,並僱請人員進行網絡炒作,從而達到迫使學校開除涉事老師、索要賠償等目的,鑑於她的行爲嚴重擾亂公共秩序,社會影響惡劣,已經涉嫌尋釁滋事。
半年後,李琳以尋釁滋事罪獲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2020年11月20日,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李琳尋釁滋事案進行公開開庭審理並當庭宣判,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李琳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層層轉包的生意
炒熱“血衣案”的推手也沒能逃脫法網。2020年6月3日,李琳被控制後的第三天,警方抓獲了馬某。他供認,自己在網上發現名爲“某某自助下單社區”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下單,可以付費購買在各類社交平臺賬號的點贊數、轉發數和粉絲數等服務。馬某是“代理”,他通過閒魚等渠道發佈廣告吸引客戶,將客戶的需求在平臺上下單,從中賺取差價。
代理的上線是平臺,但平臺也分大平臺和小平臺,存在層層轉包的關係。2020年7月21日,廣州警方趕赴山東,在某居民小區找到了馬某的上線平臺。在那套民房裏,一名老闆帶領幾個年輕人成立了代刷工作室,工作室沒有註冊工商營業執照,“營業範圍”是給短視頻類、文章類、投票類、網課類等平臺增加點贊數、轉發數和粉絲數。
但工作室仍是網絡水軍鏈條上游接單的一環,工作人員並不直接參與代刷,只對自己搭建的“小平臺”進行日常維護,並進行售後服務。“小平臺”利用API接口程序與上家網站對接,可視作“大平臺”的分站。在“小平臺”後臺,警方發現了馬某替李琳進行微博漲粉、點贊、轉發的下單記錄。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在閒魚上用“推廣”等關鍵詞搜索,搜索到售賣代刷數據的帖子。賣家直接發表圖片,在圖片中用凌亂的手寫字體傳遞微信聯繫方式,用“黑話”來標明商品,比如用“芬”代替“粉絲”,“米”代替“元”。
記者以購買粉絲量的名義聯繫到了銷售人員彭成,電話那頭是個年輕男性的聲音。彭成告訴記者,他自己搭建了一個“小平臺”,手下有6名代理,目前生意忙不過來,仍舊在招代理。
彭成發來了自己“小平臺”的截圖。記者看到,其上可購買的產品涉及抖音、快手、嗶哩嗶哩、拼多多砍價、生活繳費,tiktok(抖音海外版)、小紅書、閒魚和王者榮耀,商品類型包括增加播放量、點贊、評論、轉發和粉絲。他稱現在不做微博的推廣。
“評論可能比較貴,點贊和轉發便宜,播放量等於不要錢。”彭成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抖音上刷100萬播放量,給客戶開價30元。代理賺錢,主要靠粉絲數和評論量,在抖音平臺上,代理對客戶的報價是100個粉絲6元,2~3角1條質量不等的評論,而根據他發來的平臺截圖,代理“拿貨價”是100個粉絲2~3元,評論每條1角左右。
記者發去一條抖音作品連接,並支付90元,要求爲作品所屬賬號購買價值60元的1000個粉絲,以及給作品增加價值30元的100條評論。彭成同意接單,“再送你10萬播放量”,他表示,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左右,粉絲量就能到位。
“(粉絲數量)不能上太快,上太快對號影響也不好”,而100條評論到位需要24小時左右。記者購買的是每條價值3角的“高質量”評論,他保證是“活躍真人、帶頭像資料,可自己定義圍繞某個方面去評論”。
何爲“活躍真人”?彭成表示,這與現實中的真人含義並不相同,是意味着“賬號質量超高,帶作品,帶頭像,高活躍”,每個操作者可以擁有多個高質量賬號,下單之後,操作者利用這批賬號是“純真人做任務,一個手機,一個賬號,一個IP”,而且“下單就跑,從來不延遲,24小時跑單”——這意味着24小時營業。
爲了保證這些“真人粉”的手打評論繞過審覈,彭成要求,每條抖音視頻下,最多購買300條“真人評論”,如果是定向的機器評論,則允許購買1000條。評論的內容方向也有限制,“國家詆譭,罵人的評論搞不來”。
而在他的發單平臺上,可以看到這些真人手打評論的實時進度,以任務完成百分比標明任務完成度。“我的上家就是老闆,他們有自己的機房和服務器,就是做這個的,售後秒回。”彭成說,這保證了評論內容的靈活性,可以根據變幻莫測的平臺審覈標準做出改變,或者聯繫客戶進行退款。
彭成說,他從五年前開始做水軍代刷生意,在此之前倒賣Q幣賺錢。Q幣是社交媒體上的一種虛擬貨幣,常被用於網絡賭博活動。彭成表示,自己不是專業的“引流”,不是根據用戶興趣去推廣,通過他增長的粉絲“90%以上都是死的”,如果賬號有賣東西的訴求,最好去找專業的引流公司,“走正規渠道打廣告引流,就是有點貴。”
記者下單購買後,不到一天時間,100條評論出現在記者推薦的抖音作品下。這些評論長短不一,多的有十幾個字,內容都與抖音作品相關,看起來就像是真實的網友評論。
這些評論來自何人?肖雅菁是廣州市白雲區檢察院檢察官,曾參與辦理“血衣案”,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通過水軍‘增粉、點贊、轉發’網絡信息過程中,有需求的客戶往往通過代理下單,代理將任務導入平臺,由後者負責組織‘生產線’式操作,最終完成信息擴散任務。這些平臺服務器多放在阿里雲或騰訊雲,由中間商家提供和維護。客戶需求經平臺分配最終‘落實’在自動電腦程序(俗稱‘殭屍號’)或掌握大量賬號的網絡水軍團隊(俗稱‘水手’)。‘水手’可能是一些社會閒散人員,也有的是在校大學生。他們針對‘網賺’項目將養號、刷單視爲兼職,有目的性地人爲進行虛假評論或轉發、點贊大量網絡信息,在完成特定任務的同時也獲取一定報酬。”
《中國新聞週刊》在一位網警處瞭解到,在水軍產業鏈中,細分爲技術流、卡商、接碼平臺等多種類別。虛假的評論主要有兩個來源,一種是水軍團夥通過“養號”,即掌握大量手機和手機號,註冊微信、抖音、快手等各類賬號後,進行一些規律性活動,如發表作品等,模仿真人的行爲,用來躲避平臺的審覈機制,這些仿真號(又稱“真人號”)成熟後,再交由電腦程序進行自動化評論。而另一種則爲人工評論,客戶需求通過平臺發包,承包商通常再通過微信羣或衆包平臺發佈任務,一些兼職人員領取完成任務後,再兌換爲相應報酬。
在“血衣案”中,涉嫌犯罪的情節在於發佈虛假信息,擾亂公共秩序,平臺“老闆”爲此承擔了尋釁滋事的刑事責任。廣州警方通報,在抓獲李琳後,警方又抓獲了爲她提供代刷服務的犯罪嫌疑人共5名,分爲兩個層級,其中第一層級爲馬某,第二層級爲平臺,該平臺所在的“工作室”被定性爲“非法提供推廣營銷等服務的營利性代刷平臺”,經初步統計,工作室的涉案流水逾2000萬元。
憤怒的流量
“‘血衣案’是一起較爲典型的水軍與公衆共同推動的熱搜案件。”肖雅菁認爲,之所以說是共同推動,主要在於教師虐待未成年人這個話題本身就能抓取公衆眼球,再加上網絡水軍的推動,就迅速形成了網絡輿情。然而讓她頗爲不解的是,李琳購買了部分廉價的殭屍粉,並不代表真實的關注,虛假的關注度是如何撬動了現象級的傳播?
2021年8月,新浪微博公佈了熱搜排名公式,爲(搜索熱度+討論熱度+傳播熱度)乘以互動率。每分鐘計算一次,取前50名進行展示。新浪微博相關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互動率是熱搜的一個衡量因素,這個數據可以衡量網友願意參與話題的程度,反映了用戶消費內容的意願。
互動率的計算也有一套後臺公式,分母是原創內容數量,分子是發佈內容的互動數據,即轉發、評論和點贊。這意味着,某個話題裏,如果原創內容較少,而對這些內容的轉發、評論和點贊數量又高,則容易上熱搜。“比如一個話題裏有1000條內容,被轉發100萬次,評論了200萬次,點讚了1000萬次,另一個話題原創數1萬條,但轉發、評論和點贊比較少,那麼前一個話題更容易上熱搜。”上述人士表示,這樣的設計能反映出微博話題真實的熱度。
水軍制造的虛假熱度能否奏效?上述人士指出,目前微博有反水軍程序,可以分析賬號的行爲、IP地址和使用設備,來判斷是否是水軍。“主要排查的是機器水軍。”該人士承認,對於水軍團夥養的“真人賬號”,判定是否爲水軍比較困難。“什麼是水軍?我現在想到的就三個標準:是不是人,收不收錢,是不是自由意志。平臺只能確定是人還是機器,其他兩方面依靠平臺很難判斷。”該人士認爲,平臺會將比較容易識別的機器水軍抓出來,“但是如果找出代刷的幕後黑手,平臺比較有難度。”
但是,在“血衣案”中,李琳僱傭的“水手”騙過了微博的反水軍程序,虛假的數據成爲她的微博衝上熱搜的墊腳石。肖雅菁還特別指出,當這條虛假指控引起關注後,一些粉絲數量成百上千萬的微博“大V”也轉發了此事,助推了事態的發酵。
一些“大V”熱炒社會事件,吸引注意力,背後有營銷的目的。在微博有500餘萬粉絲的王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觀察到的“大V”分爲兩類,一類是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投資人、經濟學家,以及情感博主等,他們靠專業積累創作原創內容,幫助網友答疑解惑,依靠知識變現,另一類則是營銷號,這類號缺乏原創能力,爲了吸引粉絲,甘願成爲網友發泄情緒的出口。
王三指出,營銷號不在意事實真相,當他們察覺到網民積攢起了某種情緒,就會替這類情緒代言,甚至會順應情緒對事件進行片面解讀,“拼湊材料,製造一個靶子,替網民當打手。”他說,有的營銷號會突破道德底線,對被指控者進行過度辱罵,引導網絡暴力。而由於有人帶頭“開打”,網民釋放情緒會更肆無忌憚,暴力的氣焰也就越盛。而當狂歡結束,情緒如潮水般退去,營銷號就能收割一大批粉絲,此後不論是引流還是帶貨,都能獲取收益。
這令網絡暴力成爲“流量密碼”。極端情緒挑動的狂歡,更容易令用戶動手指,轉發、點贊或者評論極端言論,堆積消費內容的數據,增加話題的互動率,將其推上熱搜。在某些微博大V眼裏,這即是“憤怒的流量”,是最好賺的一種。而這其中,也有水軍推波助瀾的影蹤。
在發言評價了一位明星後,芒果陷入到一場持久的網絡暴力中。她試圖反擊,但由於雙方地位並不平等,她是網絡透明人,對方是擁有百萬粉絲的明星,這令芒果處於被追着打的狀態,並遭遇了大量明星粉絲的辱罵和造謠,經歷了幾輪衝上熱搜的網暴。
那是在2019年下半年,芒果在微博上看到一位明星穿衣暴露的熱搜,她認爲這位明星是急於出名而低俗炒作,於是發了微博,評論這位明星利用色情打擦邊球炒作,她承認自己語氣較爲尖銳,但是她的微博粉絲少,“感覺對她(明星)造不成什麼影響。”但那條微博被明星轉發,對方看起來惱羞成怒,發言稱要“做個實驗”,讓芒果也感受一下“大家輪流不間斷不重樣罵你的滋味”,粉絲們被煽動,在鐵粉的組織下,“奉命出征”去罵芒果。“他們形成了一個組織的網暴團伙。”芒果說。
明星先就芒果發佈的“零轉評贊”的微博向法院提起訴訟,向芒果索賠精神損害撫慰金20萬元。芒果對此提起反訴,索賠精神損害撫慰金5萬元。北京互聯網法院綜合考慮雙方的影響力、公衆形象、過錯程度、傳播方式、侮辱及誹謗的性質、涉案侵權微博賬號的粉絲數量和微博瀏覽量、影響範圍等情況,做出一審判決。
法院認定,這位明星客觀上具有誘導、慫恿他人進行網絡暴力的言語意思表示,且其清楚該行爲的後果,可以認定爲實施了教唆行爲,部分網民發給芒果的微博私信言論,帶有侮辱謾罵、恐嚇威脅、人肉搜索之意,內容粗鄙不堪,具有人身攻擊性質,超出了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邊界,屬於故意嚴重貶損芒果人格的行爲,構成對芒果的侮辱。同時,法院也認爲芒果的言論構成了對這位明星的名譽權的侵犯。
最終,北京互聯網法院判決雙方在微博上公開賠禮道歉,明星賠償芒果主張的全部精神損害賠償50000元,芒果則賠償明星精神撫慰金5000元。雙方均提起上訴,北京市第四中級法院二審維持了原判。
芒果向《中國新聞週刊》講述了被網暴的感受。2019年10月14日那天,她打開手機,忽然看到無數的微博通知,她被無數網民狂轟濫炸的評論和私信辱罵,“沒想到有個明星會主動搜索轉發我一個‘網絡小透明’的一條微博,還教唆網絡暴力。”
不到半個小時,辱罵攻擊填滿了她的私信,負能量像潮水般將她淹沒。最令她受傷的是人肉搜索,她使用那個微博賬號近十年,微博裏有很多個人生活軌跡,明星的粉絲對她過去發表在社交平臺上的生活痕跡惡意解讀,對她真實生活進行造謠和抹黑。
接連上了兩個熱搜後,芒果發現自己被人肉搜索,個人信息遭到傳播,她去報警,並在微博裏貼出報案回執,她還就此前用詞不當嚮明星道歉,但也同時要求明星就網暴行爲向她道歉。
但是,芒果的道歉並不是完結,反而給炒作貢獻了劇情。芒果說,那些熱搜是營銷號炒作的,明顯偏袒藝人一方,宣傳她嚮明星道歉了,“但隻字不提這位明星煽動網暴,也該向我道歉”。
芒果認爲,在這場網暴狂歡中,她是被“獻祭”了:她成了明星炒作話題的“素材”。
“喫人”的利益鏈
在起訴的同時,芒果也想找到熱搜話題背後的推手,她以需要合作爲由,加了一些微信營銷號,獲取了他們的報價,其中包括多家知名MCN機構。其中兩家公司的報價單顯示,他們都擁有大批粉絲量在數百萬或上千萬的營銷號,這些“大號”可以創建熱搜話題,在其中進行創作和轉發微博炒熱度,轉發和發佈軟文的價格最高超過5000元。
MCN公司還提供“熱搜資源包”,將大號和僞裝成普通網民的小號組合售賣,共同創建微博話題,再加上網絡水軍的助推,給話題刷流量,將其推上熱搜。2021年底,當芒果詢問某明星的熱搜話題如何炒作起來時,其中一家公司的一位負責人向她介紹稱,“熱搜資源包一般包括5個大號10個小號,再加一些達人號,上榜以後再依據排名收費。”
這位負責人還承認使用網絡水軍,爲明星提供微博“真人評論”,評論方向可以由明星團隊提供。除了微博平臺,這些MCN公司還提供抖音、豆瓣等平臺的宣傳推廣和網絡水軍服務。
“營銷號的轉發,其目的其實不是製造多少轉發量,而是帶動起來多少轉發量。”作爲“大V”的王三說。王三舉例,如果是200多萬粉絲的營銷號去介入某個話題,或許其創作轉發的微博可以製造1萬個轉發,但是這1萬個轉發能實現“長尾效應”,可以帶動10倍的關注量來炒熱話題。
如何帶動更多的關注量?王三說,那就是要誇大事件,抓住網民的情緒。“營銷號公司的基本功課就是寫煽動情緒文案。”他說,在接單之初,營銷號會先判斷事件本身帶動情緒的潛力,“比如挑動一些羣體間的對立,或者特別聳人聽聞的惡劣情節,都是火的元素。”
如果情節平淡怎麼辦?“可以添油加醋,編造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僞但足夠聳動的細節。”王三舉例,比如男女關係中,一方想要在微博指控另一方,可以誇大親密關係中沒有第三方見證的情節和感受,“比如說對方冷暴力,這個詞兒本身就因個人感受不同,很難界定,對方又沒法否認。”
當網民憤怒的情緒被調動起來,緊接着就會出現“人肉搜索”,將負面影響蔓延至線下。王三指出,除此之外,在排山倒海的關注中,被指控者在互聯網世界的所有痕跡都會被網友嚴厲審視,其中一些人會將被指控者過去的一些表達打碎,進行歪曲和拼接,“製造一些黑料供大家批判,但其實不一定是真實的,這個人可能本來沒那麼壞,但就要塑造得更壞。”王三說,進行這類“再創作”的賬號,往往具有營銷性質。他認爲,順應網民的憤怒,是營銷號討好粉絲,從而增加粉絲的手法,背後都有營銷的利益考量。
如今抖音和微博都披露了營銷號所屬的MCN機構,“官宣”了部分營銷號的營銷功能。但大多數營銷行爲仍難以辨別,網民仍有可能被一些不夠公正的“意見領袖”所引導。
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杜明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網絡營銷本質上是一種廣告,可以進一步明確該性質,要求其遵循《廣告法》,披露其利益關係,從而防止傳播對象被誤導。“互聯網有放大器的作用,我們在線下沒有規制好的問題,到了線上就會很凸顯。”杜明懷說,在現實生活中,營銷方式層出不窮,這些打着擦邊球的“軟廣告”仍存在監管的困難。
2013年“兩高”的司法解釋第七條規定,對有償刪帖和明知是虛假信息還提供有償發佈,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爲,依照情節嚴重程度可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但法學界的一些人士認爲,此條規定有待更加細化,不易落地。
作爲一線檢察官,肖雅菁認爲,上述司法解釋條款的出臺,是基於保障網民能夠公平地獲取信息來源,保障了知情權,令網絡信息不被人有意識地操控。但在司法實踐中,這個條款在打擊“黑公關”的同時,有時也會誤傷“白公關”。因爲按照司法解釋規定,只要提供有償服務幫人刪帖則入罪,但一些行爲人爲他人提供通過投訴或申訴渠道刪除虛假信息的服務,這些行爲沒有很強的危害性,也沒有采取欺騙手段,在入罪時還是應當謹慎。
同時,“黑公關”也變得更加狡猾。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懷勝指出,黑公關脫胎於網絡水軍,在互聯網公司的商業競爭中,幫助一方通過網絡輿情攻擊另一方,後來這類公關多以信息服務公司的形態出現,“反噬其主”,由受僱一方變爲敲詐勒索。“過去是收錢幫着罵人,現在是不給錢就罵你。”
李懷勝指出,一些企業在IPO上市前期,會格外注重負面信息,就給了這類黑公關以可乘之機,而由於其“爆料”存在部分真實性,並且敲詐手法隱祕多樣,司法機關對這些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爲較難規制。
“兩年前掃黑除惡期間,曾經提出過‘網絡黑社會’的說法,其實針對的就是這類情況。”李懷勝說,和現實中的黑社會一樣,這些“信息諮詢公司”表面上看起來都是正規公司,實際上他們積攢了大量的互聯網資源,控制大量批量註冊的“殭屍號”和高質量的“真人號”,這類賬號在市場中流通,涵蓋市面上幾乎所有平臺,“是全平臺矩陣,”爲了躲避平臺監管,這些賬號未必是非實名,其背後就是個人信息流通市場。
“個人信息泄露是網絡黑灰產業的源頭。”李懷勝說,在黑灰產業中,不法分子搭建違法平臺,利用個人信息進行網絡詐騙和註冊黑灰賬號,從事網絡水軍活動,賺到錢後還有專門洗錢的網絡,“從上游到下游,利用個人信息,整個產業鏈就做活了。”
(文中李琳、彭成、王三、芒果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