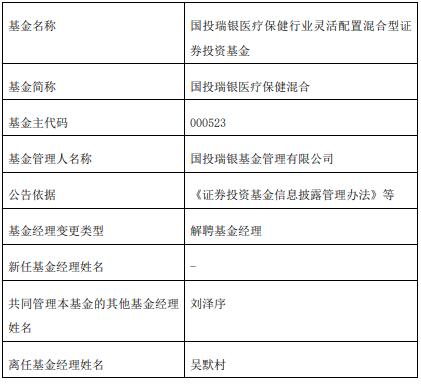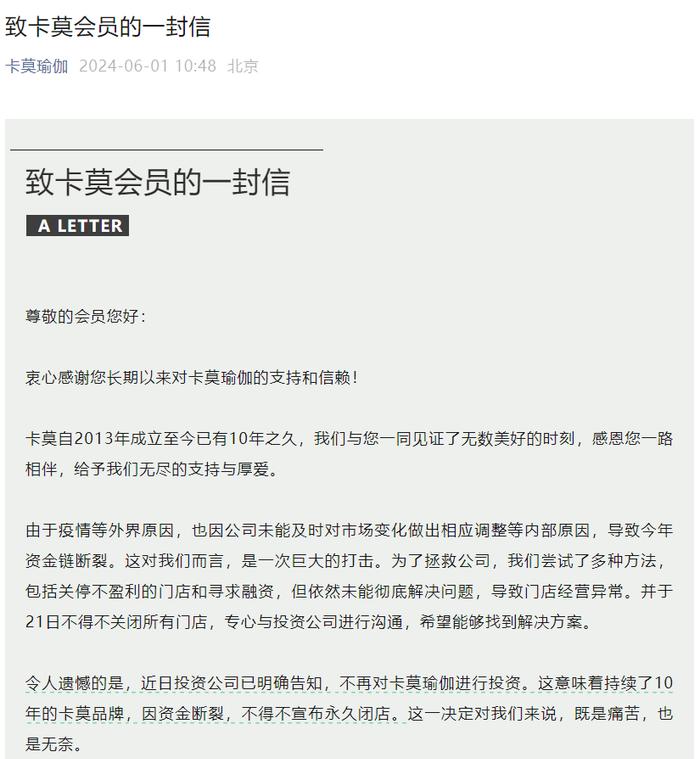與沙塵暴“交手”還是“共存”?
4月19日晚,北京遭遇今年第十次沙塵天氣。中央氣象臺4月19日18時繼續發佈沙塵暴藍色預警,預計4月19日20時至20日20時,內蒙古中西部、新疆南部和東部、甘肅大部、寧夏、山西、河北西部、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區有揚沙或浮塵天氣,其中,新疆南部、甘肅東部、寧夏中部、陝西北部等地局部有沙塵暴。
從今年一月起,北京經歷的數次沙塵天氣中,至“沙塵暴”等級的有兩次。4月12日那起沙塵天氣,風沙甚至一路向南,浙江杭州、上海等多地的城市上空出現了被一層黃色籠罩的景象。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以下簡稱: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長盧琦指出,與過去十年的同期比,今年沙塵暴天氣確實較爲嚴重。但他同時也表示,通過二十餘年的治沙手段,北京的沙塵現象總體有明顯緩解。
黃沙多次過境,社交媒體上開始流行兵馬俑滿身塵土歸家的表情包。有網友提出質疑,“我們種的那麼多樹,都沒用了?”
“進入近代後,人們逐漸認識到沙塵暴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破壞作用,認爲這是一種突發性的氣象災害和生態災難。”盧琦說,實際上,只要氣象上具備了起風條件,有沙子的地方就會有沙塵暴出現的可能。這和生態好壞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邏輯關係。因此,他認爲,沙塵暴是無法被根治的。
那麼我們爲什麼還要治沙?盧琦說,治沙治的是人類活動影響所帶來的人造沙漠,治的是“荒漠化”,“是把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和破壞儘量恢復到原位,而非原生沙漠本身。”

敦煌冬日高大沙山與防護林、綠洲。受訪者供圖
有風,有沙,就會有沙塵
盧琦比喻沙塵暴形成的過程,類似於一場從烏蘭巴托到北京的汽車拉力賽:車子的出發點在蒙古烏蘭巴托,中間經歷無數個加油站,油箱減後又加滿。“凡是風經過的地方,對沙塵都有交換和貢獻,沙塵有落也有升。”
“風起源於蒙古高原,而吹起沙塵的沙源地則包括了蒙古國和我國境內的沙漠、沙地、裸地。”他認爲,網上關於“沙塵暴來源於蒙古國”的說法並不完全準確。
他解釋,沙源、風力條件、熱力條件是沙塵暴形成的三大要素。今年的沙塵天氣是由蒙古氣旋引起大風、捲起沙塵,在途經我國北方乾旱半乾旱地區時補充了沙塵,長距離輸送至長江以北區域,氣旋、大風使沙塵天氣的形成具備了動力條件。“今年回暖早,氣溫忽高忽低,忽冷忽熱的空氣相遇後形成強風,從而形成沙塵暴。”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崔桂鵬描繪我國沙塵暴的三條路徑:東路、中路和西路。東路的風從蒙古東中部南下,主要影響我國東北、內蒙古東中部和山西、河北及以南地區。西路的風從蒙古西部和哈薩克斯坦東北部東南移,影響新疆西北部、華北及以南地區。而京津地區的沙塵主要來自於中路,風從蒙古中西部南下,因中路與京津地區的距離最短,所以對京津地區影響也最大。
崔桂鵬介紹,在萬年時間尺度上,沙塵暴的形成是以東亞特殊的大氣環流爲背景,並與季風的強弱緊密聯繫在一起,其演化主要受地球軌道因素的控制。“近千年來,我國沙塵暴的頻發期就有5個,對應的是同期乾冷的氣候背景。”
而在百年時間尺度上,我國沙塵暴的發生頻率與區域性的氣候變化有關。“沙塵暴的發生原因有些是由局地天氣條件所致,而更多的是由大尺度天氣系統造成。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除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區外,年沙塵暴日數總體上呈遞減趨勢。”崔桂鵬說。
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監測數據顯示,近20年,我國春季(3-5月)沙塵天氣由上世紀60年代年均20.9次減少到近10年年均8.4次,沙塵日數平均每10年減少1.63天。
盧琦說,如果在五十年的統計維度上評估我國沙塵天氣的變化,能發現近二十年沙塵天氣的明顯減少。據中國天氣網數據統計,上個世紀60年代,僅特大沙塵暴在我國就發生過8次,70年代發生過13次,而80年代則發生過14次。
對此,專家們都表示,得益於我國大面積的治沙、固沙措施,地表生態得到一定恢復,近年的沙塵天氣纔有明顯緩解,“荒漠化防治是減少沙塵暴頻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盧琦說。
在盧琦看來,三北防護林建設的主要目的並非用來防治沙塵暴。樹木的防風原理主要在於通過摩擦力減小風的速度,同時具備一定的固沙功能,以間接的方式來削弱風的力度,減少風帶起的沙塵。“但樹木的高度有限,冷空氣和大風影響範圍垂直方向主要是在千米以上高空,20~30米高的防護林可阻擋住部分地表的較粗的顆粒物,但遠不能擋住被大風帶上高空的較細的顆粒物。”
“三北防護林的作用就如同100米跑步和100米跨欄之間的區別。”盧琦說,“所有的工作都是圍繞着把風速給降下來,風遇到比較平的地表面就會加速。”

庫姆塔格沙漠野外科學考察時,考察隊伍遭遇沙塵暴。受訪者供圖
治沙
1984年,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資源研究院原院長王濤第一次走進沙漠。
那是新疆塔里木河下游一個名叫阿拉乾的地方,清理流沙似乎是永恆的主題。由於對當地大規模開發,塔里木河的水流在下游位置出現了斷流,土地逐漸荒漠化。冬春兩季,風一起,當地重要的公路幹線便會被流沙覆蓋。河牀變得乾旱,地下水水位不斷下降,大片大片的胡楊林枯萎後褪下綠來,滿目皆是灰褐色的景象。“對比過去30年的衛星照片,原先一大片綠色走廊不再存在了。”
春天沙塵最多時,負責清理公路的人一天就要剷起幾噸的沙子。“每天做同樣的事,但沙子又會不停地來。”
當時像這樣荒漠化的現象比比皆是。
王濤覺得,治沙的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治沙的同時,荒漠化土地仍在不斷蔓延。當時大部分的土地荒漠化都來自於人類活動,包括過度開墾草原,過度放牧和過度樵採等。“在內蒙古、山西、陝西北部、甘肅、寧夏等地,由於煤價昂貴,當地的農牧民主要以砍樹取火,造成了樹木被過渡砍伐。牧民承包了土地,追求最大的利益,過度放牧就在所難免。”
王濤的工作是做不同區域的基礎研究,用他的話說是“打頭陣”。每片區域的情況不同,整個荒漠化區域從降水到溫度等自然條件不一樣,若是要治理,便要因地制宜。“從呼倫貝爾沙地到科爾沁沙地、到渾善達克沙地、毛烏素沙地、庫布齊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所有這些地區不管是沙漠的利用,或者是沙漠化的防治,都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來進行技術模式的研發。”
治沙工作從新中國成立起便開始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便成立了林墾部,組建了冀西沙荒造林局,開啓了治沙之路。1959年我國成立了中國科學院治沙隊,第一次全方位、大範圍地對我國的沙漠、戈壁和沙地進行綜合的考察,“這就是摸清家底。”王濤說。
1978 年,國務院正式批覆“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成爲生態建設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從這時起,我國治沙的任務重點放到了沙漠化的防治問題上。
早年,王濤在沙漠裏做研究,每天騎着駱駝帶着帳篷,睡在沙漠腹地裏,簡單扎一個小帳篷過夜。條件變好了,就住進當地人的車馬店裏。在野外做風沙觀測時,即便戴上防護的眼鏡,一天下來,滿眼都是沙子。
王濤所在的團隊每年都要進行一次大範圍的野外考察。最長時,他一年中有三個多月都在沙漠中跑。今年,他便和團隊從蘭州出發往西走,穿過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然後從新疆的天山北邊、巴里坤一直到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又到南疆塔里木盆地,再從且末、若羌穿回來一路到青海,最後回到甘肅。“這一趟下來要花至少一個多月時間,行走15,000公里左右。”
做基礎研究的團隊需要以研究沙漠的形成演變、沙漠化的成因過程、時空分佈等等爲基礎,探討適合當地的治沙技術。比如,在固沙植物上便有很大的講究。“考慮植物的各種特性和生態條件,優選出成活率高、生活力強且生存趨於穩定的植物。”王濤說,例如,在沙坡頭站,花棒、黃柳和沙拐棗,可以認爲是優良的固沙植物,籽蒿、油蒿、檸條、檉柳等在成活率和穩定方面表現不如前幾種,但生活力尚好,也可以認爲是較好的固沙植物,能在類似的地區推廣。“如果研究確定荒漠化主要的成因是由於人類的活動,通過調整人類利用土地的方式和程度,沙漠化土地是可以逆轉的。”

巴丹吉林沙漠與騰格裏沙漠交匯處的治沙工程草方格。受訪者供圖
“1998年開始,國家推行退耕還林還草的政策以後,對沙漠化的防治是非常有效的。從2000年開始,根據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林草局兩家每五年更新一次的調研數據,我國的荒漠化土地面積都在逐漸縮小。”王濤說。
2017年,王濤再次來到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當地的土地荒漠化已基本得到改善,地表上又見流淌的河流,生命力頑強的胡楊林又重新冒出綠來。
沙塵暴能否根除?
治沙四十餘年,王濤仍然感慨,“人類在沙塵暴面前還是很弱小的。”在他看來,沙塵暴是人類無法杜絕的自然現象。“如果說人類能做點什麼的話,就是從沙塵暴的起因入手,通過減少荒漠化土地,減少給沙塵暴提供沙物質的沙塵源區範圍,來減少沙塵暴的程度和頻率。”
“進入近代後,人們逐漸認識到沙塵暴對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破壞作用,認爲這是一種突發性的氣象災害和生態災難。”盧琦說,“實際上,只要氣象上具備了起風條件,有沙子的地方就會有沙塵暴出現的可能。這和生態好壞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邏輯關係。”
今年以來,黃沙多次過境,許多人發出疑問:投入人力、物力治沙多年,爲什麼還是有沙塵暴?三北防護林到底對沙塵暴有沒有作用?
沙塵暴作爲一種災害性天氣,影響大氣環境質量,以大風的形式破壞建築物、樹木等,以風沙流的形式破壞農田、鐵路、草場等,造成財產損失。“我國每年因荒漠化問題造成了巨大的生態和經濟損失,每年由此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 640 億元人民幣,將近 4 億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荒漠化問題的困擾。”盧琦說。
但他同時表示,治沙治的是人類活動影響所帶來的人造沙漠,治的是“荒漠化”,“是把人類對自然的影響和破壞儘量恢復到原位。”而非原生沙漠本身。
“我們一方面要了解沙塵暴的形成機理和控制因素,接受沙塵暴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法則,人人蔘與荒漠化防治。例如,在適合造林、需要造林(如農田防護林、防風固沙林)的地方造林,適合種草的地方種草,天然存在荒漠的地方就繼續存在荒漠。”
盧琦說,判斷一片沙漠是否需要治理,一要看其形成年代和類型,如果是原生沙漠,則儘量不進行人爲干預,能保盡保;二要看是否有重大治沙需求,諸如國家重大工程、交通運輸、國防和城鎮建設等,要因害設防、綜合治理。“我國約170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中,可以治理的約50多萬平方公里,其餘120多萬平方公里則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沙漠,應儘量避免人爲干預。”
另一方面,在盧琦看來,沙也有其生態價值,不能一概而論。自然形成的沙漠本身是一種資源,應該被保護起來,減少人爲干預。“亞洲沙塵可以影響到赤道太平洋和亞極地太平洋的海區,而作爲南半球沙塵的主要源區,澳洲沙塵是南大洋海區鐵供應的重要來源。”
他解釋,沙塵是海洋初級生產力限制性營養元素(如氮、磷、硅、鐵)的重要來源。沙塵暴將沙漠中大量礦物質帶入海洋,讓賴以爲生的真菌、藻類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整個海洋的生物圈才得以運轉。“簡單來說,如果沒有從沙漠被吹進海洋中的沙塵,大魚喫小魚、小魚喫蝦米、蝦米喫浮游生物這條生物鏈就無法運轉,就沒有所謂的海鮮。”
沙塵暴也能起到促進土壤形成的作用。沙塵暴把表層土壤從一個地方搬運到另一地方,當沙塵落到陸地上經過發育即形成了可以滿足植物生長的肥沃土壤。

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科研團隊考察世界最高海拔沙漠庫木庫裏沙漠。受訪者供圖
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總體規劃綱要》,會議強調要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將“沙”首次納入到“七位一體”的生態治理總綱。在盧琦看來,這不僅肯定了“沙”的生態價值,也標誌着荒漠化防治工作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對沙的認識更加全面、立體、系統。
盧琦說,過去按照“先易後難、先急後緩”的原則,一些條件較好、治理容易的沙化土地已得到初步遏制。未來需要治理的荒漠化土地,總體環境條件更差,難度更大,單位面積所需投資更高。
這不是一日之計。“生態跟教育一樣需要長線投資,不一定能馬上見到成效。”盧琦認爲,人類需要與沙塵暴共存,“科學認識沙塵暴,推動沙源地跨境全域治理,人人蔘與荒漠化防治,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法則,纔是長久之道。”
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