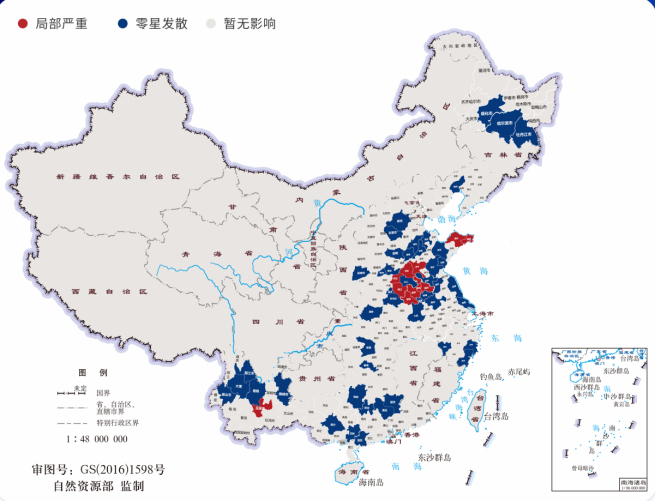我,大理人,被網紅“擠”出古城
離開大理前,最後的午餐,阿溪找了一家餌絲店。
“這應該是下關最早的餌絲店,沒有擺調料臺,老闆調出什麼味道,你就接受什麼味道,而且你發現沒有,只要告訴收錢的那個人你要什麼,結完賬你坐下來就行,服務員絕對能在一屋子的喧鬧聲裏找到是誰點的這碗餌絲,她們就是這麼厲害。”
餌絲店的正對面,就是龍尾關,古時候大理真正的關隘。

這道斜坡的盡頭,就是龍尾關 時代週報 黎廣/攝
“過了那個關,就是大理了,所以龍尾關也是大理和下關的分界線,從那過來,就是下關。”
唐朝的天寶年間,也就是1270年前,大將軍李宓帶着10萬的部隊,也到過這個地方。
阿溪說李宓想要從龍尾關過去,打下南詔國的都城大理,結果在下關全軍覆沒,但白族人民還是把戰死的遺骸收集了起來,蓋了一座萬人冢,就在現在的天寶公園裏面。
“後來大理人也給李宓在蒼山山脈的最後一座山——斜陽峯上,供養了一座神廟,叫將軍洞,那裏可以看到龍尾關,這就是我很不理解的地方,李宓在歷史上是個侵略者呀。”
阿溪已經連湯帶餌絲都喫完了,碗底的“平安”二字依稀可見。

龍尾關附近的天寶公園 時代週報 黎廣/攝
這個傢伙,是土生土長的大理古城人,十幾年前,他不堪大理的喧鬧,離開古城,搬到了下關。
後來他發現,身邊不少的兒時玩伴,大多也因爲大理的出名,而紛紛離開。
風花雪夜
“風花雪月”是大理的四個標識,對應的地理位置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
這種充滿詩情畫意的敘事,在幾十年前,把大理塑造成了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旅遊目的地。
那時的大理與喧鬧無關。
改變發生在2014年的電影,《心花路放》播出以後,黃渤在電話裏大喊“去大理,去大理”。在電影梗的推波助瀾下,大理從風花雪月的宣傳方式,進化到了2.0版的網紅古城。

2008年大理古城的一家街頭小店 受訪者供圖
在今年春節,那個曾經被視爲中國西南地區的理想國、嬉皮士天堂的大理,變得人滿爲患。
一位來自上海的遊客,在大年初四的時候,在朋友圈說“煩死劉亦菲和李現了”:好端端的爲什麼要拍個大理的戲,弄得全國網紅都到大理了,喫個麪包都要排隊,而且20分鐘不挪步。
那種感覺就像大理已經被人和車塞滿,連一滴水都落不到地面。
當時代週報記者在假期的尾巴趕到大理的時候,原本以爲人潮已經回到工作崗位,卻還是耗時近60分鐘才從下關趕到古城。“其實以前,不過就是20分鐘”,阿溪在車裏感嘆,“現在也知足了,20多公里的路,終於不需要再開兩個小時了。
作爲大理古城裏土生土長的人,他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你覺得大理,還是你當初認識的那個大理嗎?
這個提問十分巧妙,它不是尋求一個答案,而是爲了思考。
他說小時候,古城洱海門外是一片塵土,下雨的時候車軲轆一定會打滑,那個樣子的大理,是他心裏的大理。

十幾年前,當地的小孩爬在樹上看城樓 受訪者供圖
“當時全球範圍流行嬉皮士,中國的香格里拉因爲《消失的地平線》而全球走紅,書裏把香格里拉說得很神祕,是長生不老的世外桃源,所以變成了城市人迴避現實生活的天堂。”
“但那時候香格里拉很遠,很多人走到大理的時候,發現這個地方也不錯,就在古城裏租個院子住了下來,抽菸喝酒看書,也寫書作畫,每天和當地人一起去菜市場買菜,也到三月街去趕集,他們真正懂得旅行的目的。”
就像東方這個詞彙最早在西方傳播一樣,福樓拜甚至認爲,幸福和東方是可以互換的兩個詞。
阿溪今年40多歲,在大理完成了9年義務教育,小時候,他放學沒事的話,也會和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玩遊戲。

大理的孩子和異鄉的遊客,很容易變成好朋友 受訪者供圖
在他眼裏,那個時代的陌生人是懂生活的,甚至會思考人生意義,那些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也開始慢慢塑造阿溪,比如他不愛去人多的地方扎堆,不喜歡紙醉金迷,吸引他的是山澗裏的一條瀑布,或者和朋友坐在一起發呆。
等他到了三四十歲的時候,他發現大理古城已經開始變得浮躁起來了。
阿溪在古城裏有個老宅子,他奶奶生前就住在那兒,他既不想把房子租出去,也不想住在古城,他覺得對於大理人來說,古城越來越不像古城。
於是他選擇離開大理,搬到下關,那棟老宅子,錨住了他心底的那座大理。

2008年,一位老者在洱海邊散步 受訪者供圖
“新”古城
第一次去大理是2008年。
那年衚衕參加了5.12汶川地震的災後救援和報道,半個多月的時間,他在四川看到了太多的生死。
回到廣州後,他開始反覆做同一個夢:坍塌石板下的縫隙裏,看到幾個孩子,他們說叔叔別擔心,我們還能再堅持一下,你去喊其他人來救我們吧。
接下來的畫面是他自己變成了廢墟下的孩子,從縫隙裏往外看,天邊正徐徐升起一輪紅日……
於是衚衕決定暫別工作,按照阿蘭·德波頓的說法,旅行能表達出緊張工作和辛苦謀生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意義。
那年8月,他去了大理,他說那一整個月,都在不停地閒逛和發呆,從喜洲到雙廊,從風情島到雞足山。
那時候大理在他面前,就像白族婦女手裏那隻掉了色的塑料油漆桶一樣真實,他看到洱海邊駝運苞谷的騾子,一聲不吭只顧前行;看到不知名的小廟裏煙火,升騰起許願人觸不可及的夢想。

2008年,雙廊鎮上的一頭騾子 受訪者供圖
有一天,他甚至在古城裏最繁華的街道、人民路上參加了半場婚禮,“新郎被新娘團‘脅迫’着,在去見新娘的路上,要到每個路過的酒吧裏討要一杯喜酒,酒吧的人會很開心,新郎也會很開心,只有本地人在人少的時候才這麼玩。”衚衕說。
最後他看到在雙廊田間出殯的隊伍,那場葬禮,像安葬了他夢裏的那些孩子。
從此以後,困擾他的夢境消失了。
那年之後,衚衕總是隔一兩年就去一趟大理,他覺得大理的靈魂,是當地人即便被世俗社會包圍而仍舊保持的恬淡、慢條斯理,他們似乎知道自己要什麼。

2008年 當地人在小廟裏祈福聊天 受訪者供圖
他說正是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讓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種打發方式,這種方式或許不如朝九晚五那麼光鮮,但卻充滿生命力。
但最近這些年,在大理紅得發紫以後,他發現大理已經被民宿老闆,餐飲投資人,點心師和咖啡職人所佔領,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希望讓大理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打造成流量密碼。
那個在上世紀被嬉皮士發現的大理,那個因爲白族的原生態而聞名的旅遊目的地,如今正在消失。就像艾略特在研究喜愛旅行的波特萊爾時說,他發現交通工具的美感,進而創造了一種新型的浪漫鄉愁——那些駝運苞谷的騾子,如今已經變成了喝92號汽油的鐵皮機器。
到了今年,衚衕說那些美感在急劇衰退,尤其是守在古城店鋪裏的那些掌櫃,口音已經開始非本地,雲南人獨有的尾音“噶”,聽到得越來越少。

2008年,在洱海邊玩耍的孩子 受訪者供圖
伴隨而來的,是在任何大城市或者旅遊景點看到的精品咖啡、天空之鏡、外賣小哥、與扎髒辮的小攤,這些表現形式,蓋住了大理真正的樣子。
唯獨剩下當地的就是餌絲餌塊、雞絲米線、乳扇、生皮這些獨有的美食,但對阿溪和衚衕來說,這些也已經不是以前的味道了。
“因爲很有特色,所以很多外來人開始學着做,這當然也沒問題,但最後他們打起了價格戰,本地人覺得沒什麼意思,就退出了。唯一的好處是古城裏喫的東西貴不起來,就是味道不大對。”
但這對於第一次去大理的人來說,似乎並不重要,畢竟大理還有山海。

早期雙廊鎮上的農貿市場 受訪者供圖
離開的,留下的
大年初八的那個夜裏,阿溪開車上青光山,大理殯儀館就在山腰上。
他說這幾個月以來,已經是第四次上山了。“以前大理人都在自己家裏設靈堂,後來大家搬到了小區,就要看小區裏有沒有共識,設置一個公共區域悼念先人,如果沒有的話就會看看車庫能不能辦,實在還不行的話,就只能來殯儀館了。”
過世的是阿溪發小的家人,那天晚上來了很多人,但他們的言行舉止,像極了影視劇中的場景。並沒有撕心裂肺的痛哭,而是大家圍在火盆前,一邊烤火,一邊喫酒擼串,追憶逝者生前的點點滴滴。
第二天,當他們再次聚在一起的時候,也說起關於大理古城的變化,共同的價值觀是認爲這些變化是發展的必然。

洱海邊新建的生態廊道 時代週報 黎廣/攝
“交通不便,出行困難,千遍一律的網紅餐館和打卡點,沒有好喫的,也沒有就業,這些年,我們自己都很少去古城了,甚至有朋友來玩,我們都不建議住在古城裏面,沒意思了。”餐桌上,阿溪的朋友們這麼說。
在大多的縣域一級的小城市,人際關係、或者說臉熟是重要的資源,在這個晚宴中的七八桌人裏,都是大理本地人,彼此也都認識,他們如今大部分,都選擇了離開古城。
潘西的祖籍是網紅小鎮喜洲,特產是喜洲粑粑,“我們一家都是最本地的喜洲人,現在一家子在下關租了個100多平方的房子,租金只有1000多塊錢,反正喜洲是回不去了,只剩下有時候帶孩子去看老人家的時候走一趟,在老房子附近喝一杯咖啡。”
作爲本地人,潘西在喜洲小有名氣,外地人盤了個鋪面在他老宅子附近賣咖啡,總是會給他打個折,他說這是在喜洲唯一的特權。

2008年 在才村碼頭附近洗衣服的人 受訪者供圖
潘西說自己朋友在古城裏有幾座房子,地理位置不好,幾乎是無人的小巷,後來周圍的房主把屋子租給別人蓋民宿,人氣開始旺起來。“朋友想着也挺好,有客人出現,就自己做點兒喫的,可以掙點錢,但過了一陣子發現不對,人多了以後,物價就貴了,掙的錢實際上只是抵消了物價的上漲。”
潘西很無奈的笑了起來,反正覺得原來的恬靜生活,怕是回不去了。
甚至在古城裏做餐飲的老一輩,也都離開了那裏,“因爲盤下門面的大多是外地人,他們這個羣體之間沒有感情,所以互相壓價,然後再壓成本,導致地方美食幾乎消失了,那些老餐館,反倒只能去下關開館子,維持住了出品。”
這就像整座城市,除了建築以外,平移到了下關。

好在大理還有豐富的自然景觀 時代週報 黎廣/攝
但下關的高樓大廈也與日俱增,與今天的一線城市越來越像,終有一天大理也會和其他城市一樣。除了山水。
三毛如何能將撒哈拉沙漠描繪爲“最美麗的家”?人類學的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是好奇那些住在沙漠或者懸崖邊的羣體,身體如何與周遭環境廝磨,從而產生一個有異於城市的精神特質,要搞清楚這些問題,就是去過那樣的生活。
但如果在異地生活也希望享受和城市一樣便利,就無法理解當地人的生活態度和文化根基。
那麼無論到那裏,旅行者都會以城市化的邏輯來審視其他人。對於旅遊來說,這多少有些狹隘。
不如說這是一種羣體無意識,但它所導致的,是這樣的一羣人,將城市的生活邏輯帶到其他地方,長此以往,不同區域之間的人文差異將逐漸消失。
“大理做的那個洱海生態廊道,是大理這麼多年以來做得最好最好的事,把整個海西都盤活了,而且走在上面確實舒服,但我就搞不懂這樣的地方,爲什麼要做個網紅的心型打卡點,簡直庸俗。”潘西甚至能接受不準在廊道上溜他的愛犬,也無法接受那個粉紅色的異類。

生態廊道的網紅打卡地
對於大理人來說,暮色屬於所有人,但暮色之後不想回家的那段時光,只屬於大理本地人。
(本文人名爲化名)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