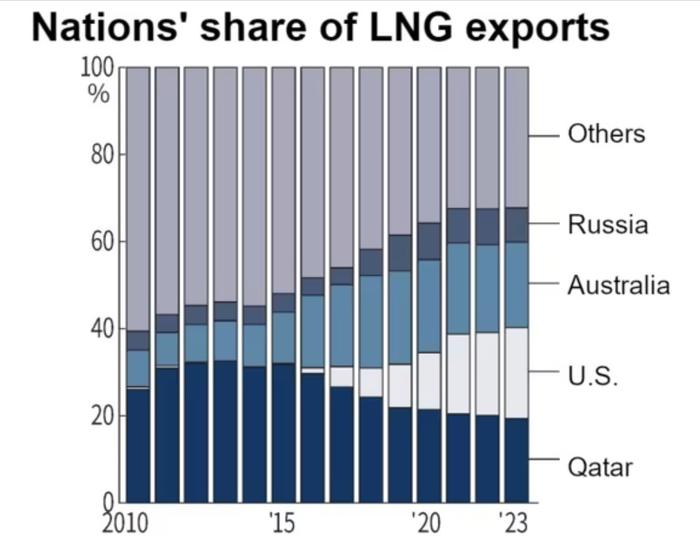最權威解讀?伯南克剖析:美聯儲爲何誤判本輪美國大通脹
伯南克最新研究指出,美聯儲因爲未關注到職位空缺與失業比例而低估了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程度,更重要的是在過於關注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低估了商品市場推高通脹(即價格衝擊)的潛力。
在6月“跳過”加息後,7月美聯儲是否再度重啓加息,成爲市場關注的焦點。
從2022年3月至今,美聯儲在一年多的時間已加息10次,共500個基點,將利率從0附近推升至5%-5.25%區間。這是近40年裏美聯儲最爲激進的一輪加息週期。當前通脹雖有所放緩,但仍高於目標2倍,抗通脹的任務遠未結束。
6月30日,在2023年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亞洲-中國年會(AMES China 2023)上,美聯儲前主席、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魯金斯學會哈欽斯財政與貨幣政策中心傑出高級研究員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分享了其與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奧利弗·布蘭查德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什麼導致了美國大流行時期的通貨膨脹?”,分析了2021年開始美國通脹飆升的原因及其演變過程。活動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主持。
伯南克首先介紹了疫情以來美國推出的空前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和隨後的通脹。2020年3月-2021年3月期間,美國出臺了3項財政刺激計劃:2020年3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簽署通過了2.2萬億美元《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2020年12月,出臺了9000億美元的新冠救助計劃;2021年3月,拜登政府推出了1.9萬億美元的救援計劃。這三項財政刺激規模總和達到了金融危機後一攬子計劃的4.5倍。
據伯南克回憶,2021年早些時候,以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等爲代表的一些學者提出了對這些刺激政策將導致嚴重通脹後果的擔憂,美國學界掀起討論熱潮。
彼時有兩種觀點,主要分歧集中在勞動力市場對通脹的回饋作用機制上,樂觀主義者認爲,即使財政支出增加會讓失業率超預期下降,但考慮到過去三十年的低通脹,考慮到菲利普斯曲線很平坦(也就是通脹對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程度相對不敏感)以及美聯儲的可信性,嚴重的通脹不會出現;批評者則擔心空前的財政刺激可能導致總需求增加,疊加寬鬆貨幣政策的累積效應,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過熱,使得菲利普斯曲線變陡峭,通脹預期脫錨。
然而事實表明,兩種觀點都不完全正確。“通脹水平比悲觀者所預期的還要高,但通脹最初的主要來源並非預期中的勞動力市場,而是給定工資下的商品價格衝擊。”伯南克說。
伯南克和布蘭查德通過構建包含價格、工資和長短期通脹預期的動態估算模型,分析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衝擊對價格和名義工資的直接與間接影響,並量化了美國新冠疫情時期通貨膨脹與工資增長的來源。
該模型的創新之處在於區分了短期和長期通脹預期,允許兩者擁有不同的產生機制,並且引入了工資增長對於物價水平的追趕效應——當人們發現通脹超過預期時,會要求僱主提高工資用於補償購買力的損失,從而推動工資水平的上漲。
通過這些假設,模型捕獲了上述觀點中關於通脹預期通過改變勞動力市場工資,從而進一步回饋影響通脹的作用機制。這一機制的重要性,在模型中由兩組參數所刻畫,其一是通脹適應預期的調整幅度,其二是刻畫追趕效應的工資-通脹調整係數。當前者更大時,預期被更好地錨定,短期的成本和勞動力市場衝擊產生的通脹作用將更爲溫和而短暫;而當後者更大時,工資對於通脹的反饋作用更爲顯著,通脹將反應更爲強烈和持續。
隨後,該研究使用1990-2019年的季度數據,採用結構向量自迴歸的方法對模型的關鍵參數進行估計。估計發現追趕效應的幅度很小,而通脹預期的錨定程度很高,這說明供給衝擊對通脹的作用是比較溫和而短暫的。
基於向量自迴歸模型的樣本內分解顯示,疫情期間美國通脹主要來源於商品市場,由大宗商品價格和供給受限商品價格的大幅上漲導致,而勞動力市場摩擦上升的影響有限。
上述研究意味着,政策制定者最初的判斷可能是正確多於錯誤的,也就是至少在短期內,勞動力市場緊張不會帶來高通脹。價格衝擊對通脹的影響短暫,特別是通脹預期仍然保持較好的錨定。在沒有強烈的間接影響或新衝擊的情況下,即使沒有政策行動,這些衝擊帶來的通脹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大部分消散。
但他們確實因爲未關注到職位空缺與失業比例而低估了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程度,更重要的是在過於關注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低估了商品市場推高通脹(即價格衝擊)的潛力。疫情期間大宗商品價格和一些關鍵產品價格的上漲幅度和持續時間都超出預期。強勁的總需求和消費支出結構的變化,加之一些部門的供應限制,使得供需之間的錯配比預期的更棘手也更持久。通過提高通脹預期,並在較小程度上產生追趕效應,這些衝擊最終影響了工資和價格。
這一分析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爲什麼美聯儲和很多經濟學家未能預測到通脹的突然爆發。對於這一問題,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此前也有過詳細分析。他指出,當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認爲增長和就業是主要問題。對於通脹原因,美聯儲歸之於供給衝擊,並認爲通脹會隨供應鏈的自我修復而下降,而美聯儲也並無政策工具解決供給端的問題。基於這一認識,2022年3月前,美聯儲拒絕緊縮貨幣、提高利率。(詳見:餘永定:美聯儲的通脹教訓)
回顧美國通脹的走勢可以發現,在第一輪刺激兩個月後,即2020年5月,美國通脹率在達到0.1%的低點後便開始緩慢回升。通脹真正“顯性化”的時間節點在2021年3月,也就是1.9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開始實施時,當時美國的通脹率(2.6%)剛開始突破2%的目標值,此後便一路走高。到2021年年底時,美國的CPI已經到了7%。2022年3月,在美聯儲開始加息時,通脹達到8%。
伯南克和布蘭查德的研究指出,直到2023年初,價格衝擊對通脹的影響都大於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大宗商品價格企穩,供應鏈恢復正常,價格衝擊逐漸消退,勞動力市場緊張開始對名義工資增長和通脹上行施加更大的影響,這一影響在未來會逐步擴大,也不會自行消退。
這意味着,要使通脹下降到更加合理的水平,就需調整勞動力市場的緊張程度。伯南克建議,爲保持物價穩定,勞動力市場平衡最終應該成爲中央銀行試圖採取措施的主要關注點。
伯南克認爲,美聯儲將很難在避免經濟放緩的前提下使通脹迴歸目標水平,而經濟放緩的程度將取決於勞動力市場某些結構性特徵的演變,特別是勞動力與工作崗位匹配的效率。在回答現場提問時,他強調,接下來經濟增長會放緩,失業率會同時上升,“它(美國經濟)將是一場溫和的衰退,而絕不是更差的情況。”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5月新增非農就業33.9萬人,大幅超預期,遠高於疫情前2019年的平均水平;失業率爲3.7%,環比上升0.3個百分點,勞動參與率爲62.6%。此外,5月整體平均時薪同比增長4.3%,較上月下降0.1個百分點。
儘管就業市場仍較緊張,但失業率有所上漲、薪資上漲壓力有所緩解,再考慮到加息對美國銀行業及經濟的影響,美聯儲在6月選擇“按兵不動”。但市場普遍認爲,7月美聯儲很可能會再次加息。
伯南克指出,美聯儲目前是世界上最激進的央行之一,如果美聯儲成功降低了通脹率,人們就將很快看到更低的利率表現。
在他看來,美聯儲有決心將通貨膨脹率降至2%,但可能需要花上幾年時間。美聯儲在過去30年使通脹率維持在低水平,人們有信心它能使通脹率再度回到2%。“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就會失去信譽。”伯南克說。
伯南克還回答了關於美元走勢的問題,他認爲,當前在美聯儲採取激進政策的情況下,美元會依然保持堅挺。“不過,隨着通脹迴歸正常,推動利率下行,預計美元將正常化。”
鮑威爾在6月28日召開的“中央銀行論壇”上給出了通脹迴歸的時間表,他指出,核心通脹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迴歸至目標水平,並預計採取進一步緊縮措施。
本文作者:CF40研究部,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原文標題:《伯南克深剖通脹成因,勞動力市場平衡應是央行政策關注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