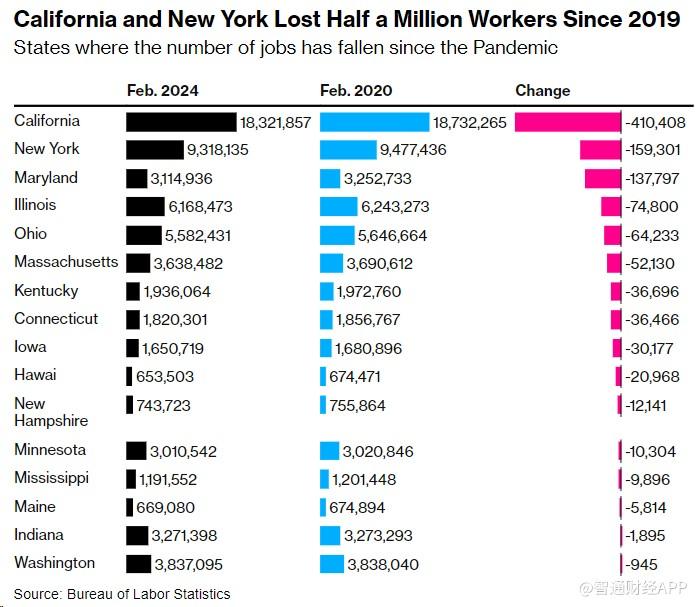就業突圍:回農村的畢業生
返鄉究竟是不是好選擇
要取決於每個人的專業興趣
“這就是我們甘肅定西的寬粉,喫起來很筋道,是用純洋芋做的,沒有添加別的粉。”27歲的張明霞扎一個丸子頭,袖子擼得老高,端一盤用辣椒拌好的定西土豆寬粉站在鏡頭前。
她在四川工作過半年,但定西口音沒變,爲了讓視頻看起來更真實,說幾句話,她就得埋頭扒拉一口寬粉。身後的曬架上,半身長的寬粉雪白如練,襯得皮膚黝黑的圓臉盤姑娘愈加粗糙。
說張明霞“胖、醜”的人就沒斷過,她不在乎。土豆粉3斤一包,售價34.9元,煮之前還得泡上6到8個小時。就這麼一袋地方土特產,返鄉創業的第三年,張明霞用“甘肅胖娃娃在助農”的抖音賬號,帶出了超過1000萬元的銷售額。
上過四年大學,又回到泥地裏“刨食”的畢業生,越來越多。“我有10萬畝有機基地,1000多畝的菌菇基地,這是包括種植業和農業服務在內的‘一產’。我還有核桃油加工生產線、火腿加工生產線、菌菇加工生產線以及機械設備生產,這些屬於二產。我的電商產業園裏還有旅行社、廣告設計公司、電商服務運營公司,這些是三產。”雲南漾濞的郭祁琦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15年,從中南民族大學金融學系畢業後,郭祁琦回到家鄉,從賣家鄉土特產漾濞核桃幹起,一寸一寸地扎進農業。如今,他剛滿30歲,與表哥一起經營着六家公司,對各類農業政策、科技項目、操作細節如數家珍。
“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跟農業有關,新農業是大勢所趨,從事三農行業也會有很多新的政策(扶持)。”選擇返鄉的“00後”揚州大學畢業生陳樂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連續幾年政策引導的影響逐漸顯現。“大學生返鄉創業”“當代大學生返鄉現狀”“回農村的年輕人”,抖音、嗶哩嗶哩等平臺上,有越來越多年輕人用視頻記錄分享自己的返鄉日常。
主動或被動地返鄉究竟意味着什麼?青年失業率上升的背景下,這是不是一條值得鼓勵和探索的“就業路徑”?對於這些問題,那些更早返鄉的年輕人嘗試給出答案。

2022年8月9日,福建福安市賽岐鎮象環村的葡萄種植園,返鄉創業大學生林恩輝(右二)、陳莉瑾(右一)在推銷剛採摘的葡萄。圖/新華
來自鄉村的隱痛與機會
定西,古絲綢之路重鎮,甘肅省會蘭州市的“東大門”,因地處青藏高原、蒙新荒漠和東南季風區匯合之處,有獨特的土壤和氣候條件,成爲全國最適宜馬鈴薯種植的三大區域之一,被稱爲“中國馬鈴薯之鄉”。被當地人稱作“洋芋”的定西馬鈴薯,形整、質優、儲存期長、澱粉含量高,享譽世界。
但在張明霞的記憶裏,定西洋芋帶來的不是驕傲,而是隱痛。她所在的隴西縣,農民在高原上開出旱作梯田。沒有大路,交通不便,每到土豆成熟,外來的收購商總要壓價。“爸媽覺得收購商給的價格低,想多要兩分錢,收購商就說,爛在地裏去吧。”
“爲什麼大學畢業不去大城市工作,卻待在農村,是不是想啃老?”爲了回答這個問題,張明霞端着一碗土豆粉,特意錄了一條視頻:“我知道爸爸媽媽凌晨五六點鐘就揹着乾糧去地裏幹活了,他們過得很辛苦,但是一直都沒有放棄過,所以畢業以後我選擇了農村電商,想要和他們一起並肩奮鬥,也可以讓農產品有一個更好的銷路。”
楊小強決定做農村電商,則是因爲天水當地的特產花牛蘋果。大專畢業後,他留在天水做電工,有一次,一位外地來的主播到天水直播賣花牛蘋果,熟悉農戶的楊小強幫着聯絡。直播結束後,農戶問楊小強:“人家外地人都能賣這麼好,你們這些本地娃娃,就不能試試嗎?”和張明霞的父母爲洋芋愁銷路一樣,因爲果子滯銷,每年都有農戶被迫放棄,挖掉田裏的蘋果樹。
郭祁琦則總是想起大二的那個暑假,他跟着從職業高中畢業的表哥“進社會歷練”,因爲曾向長春的歐亞超市賣過漾濞核桃,採購經理又找到他們,希望由他們幫忙,到漾濞隔壁盛產柑橘的賓川縣採購一批柑橘。
爲了找到口感最好的貨源,找了一下午柑橘的郭祁琦試喫到鼻血直流,“舌頭都要麻木了。”好不容易盯完一天,要付款時,才發現自己揣來的2萬元遠遠不夠。沒有拿到足額貨款,農戶不肯放他走,郭祁琦解釋也沒用,只能反覆協調,由採購方匯來全款,收到款子的農戶再三確認,這筆訂單才終於完成。
“爲什麼家鄉會這麼落後?我無法理解。”專業的金融知識與農村的現實在他身上斷裂開來,從那時起,他思考自己未來的出路:“我讀的不是頂尖的學校,畢業後可以去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或者考個公務員。但北上廣不缺人才,而家鄉這麼落後,我回來,機會應該更多。”
但這是郭祁琦的“官方說法”。事實上,大三那一年,微商剛剛興起,郭祁琦就利用微店賣漾濞核桃。銷售最好的時候,一個月的利潤就有兩萬元。此後,他的學費、路費都靠自己賣核桃來掙。“我們整個家族都是很普通的家庭。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還留在大山裏。“用經商來改變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這是最快的。”郭祁琦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不僅是雲南這種西南邊陲,出身江蘇淮陰農村的大學生陳樂也被自己看到的鄉村現實所困擾。“80後不願種地,90後很多人都去了大城市,我們00後很多人會把小麥當成韭菜。現在從事農業的,大多都是五六十歲的老農人,甚至還有七八十歲的老人,農村根本看不見年輕人,更別提田裏了。大部分老農人種地根本掙不到錢,有時候辛苦一年,連本都回不了。”
在揚州大學,陳樂學習的是畜牧專業。在他看來,處境最好的同學,是到專業對口的養殖場工作,能獲得較高的收入。還有不少同學在準備考研,也有相當比例的人回到家鄉縣城準備考事業編,餘下的則在讀書的城市“隨便找個工作幹一幹”。
近兩年,應屆畢業生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教育部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158萬人。國家統計局7月1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6月,16~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爲21.3%,相較5月增加0.5個百分點,連續三個月創2018年有統計以來的新高。
如何在就業市場中突圍?是1158萬畢業生面臨的“社會第一課”。
“秒變小學生”
“我是個00後,今年剛畢業,我選擇了一條與衆不同的道路,回家種地了。”3月7日,決心成爲一名“新農人”的揚州大學畢業生陳樂,用一條抖音短視頻公佈了自己的決定。
以陳樂爲代表的“00後”畢業生,選擇成爲新農人,離不開政策的助推。早在2019年12月10日,人社部、財政部、農業農村部發布《關於進一步推動返鄉入鄉創業工作的意見》。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支持年輕人返鄉創業,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持續出臺。
“大學生怎麼了?只要你幹了農業,秒變小學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陳樂的視頻都是記錄自己作爲“農業小學生”是如何在瓜棚裏學習。
要給西瓜打藥,陳樂才知道,他在視頻裏看到的那種全自動化大棚,投資額動輒就要上百萬元。而表哥的大棚裏,農藥裝在一隻固定位置的大水箱裏,要打完整個大棚,需要人拿着水管來回走動噴灑。打藥意味着在大棚裏站一整天,忙完一天,腰痠背痛,呼吸道也會不舒服。
要給西瓜授粉,陳樂才第一次知道,花朵還分爲公花和母花。操作時,要把公花摘下來,把公花上的花粉一點一點塗在母花上。“母花的花蕊上都必須得塗到,這是非常精細的工作,必須得靠人力一朵一朵地塗過去。”陳樂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授粉直接關係到西瓜的收成,爲此,表哥不敢將工作交給僱來幫工的工人,也不肯讓初來乍到的陳樂直接上手。
陳樂觀察學習了兩天,才被允許操作。60畝大棚西瓜的授粉,全靠表哥、陳樂和阿姨三人一起完成。陳樂自詡是不怕喫苦的農村娃,可授粉結束,他得休整一整天才能緩過勁來。
但陳樂覺得,這還只是最初級的挑戰。他的最終目的,是通過短視頻,爲家裏低附加值的農產品搭建一個可以獲取更高利潤的零售渠道。這意味着他需要輸出更吸引人的內容,獲得更大流量。僅有流量還不夠,“你的賬號應該更加人格化,成爲粉絲的朋友,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信任,才能把你的東西賣給他們。”
陳樂的嘗試並不順利。因爲他太年輕,又缺少經驗,要輸出西瓜種植技巧等內容,沒有足夠的說服力,比不上抖音裏四五十歲的老農人面孔。他本希望能在今年5月西瓜上市的季節積累足以支撐零售的粉絲數量,但效果不及預期,他感到挫敗。
陳樂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要成功打通從種植、內容生產到銷售的鏈路,僅僅親力親爲地參與種植,展現勞作過程是不夠的。在他看來,要成功做起一個“新農人”賬號,就不能只作爲一個邊緣角色,自己必須得是一片農田的主人,爲農田和產出全權負責,只有這樣,做出的內容才足夠真實,纔有說服力和生命力。
但問題在於,要獨立成爲一片農田的主人,就意味着土地承包、農資購置,這都需要資金。陳樂剛畢業,沒有足夠的積蓄,需要靠兼職工作來支撐他做短視頻的支出,獨立經營農田則顯得有些遙不可及。
靠網貸啓動
決定做電商後,楊小強給四個散落各地的好朋友打了電話,張明霞是其中之一。
五個出身農村的大學生,在天水的校園裏結下深厚的友誼。“進了本科院校,你可能會發現大家都在學習。但進了我們這樣的專科學校,同學都在談戀愛,都在玩。”楊小強發現,在這樣的環境裏,同學會迅速分化成兩個羣體,一羣人沉溺在玩樂裏,另一羣人則四處尋找出路。
“只能做小生意。”達成一致的五個人,送過外賣,收發過快遞,還賣過花牛蘋果。最終,他們發現,能穩賺不賠的,還是收廢品。有人畢業了,他們就去收那些被丟棄的書本,再從裏面分揀出小說,一部分賣廢品,另一部分賣二手書。在那樣拮据和青澀的生活裏,理性、沉穩的楊小強成了小團體的“主心骨”。因此,畢業兩年後,雖然五個人各自有了工作,但楊小強的一個電話,就能叫回所有人。
只有投入,沒有回報,在擁有足夠的粉絲和流量以前,他們需要熬過漫長的啓動期。2020年,孤注一擲的五個人,只能靠打零工來維持運轉。卸一噸貨,價錢最好的時候,也只有47塊錢。最險的一次,幾個人一起從車上跌落,摔得好幾天都走不了路。“我們幹日結,純苦力。”楊小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五個口袋空空的年輕人別無選擇。對張明霞來說,那是一段極度黑暗的日子。四個男孩做苦力來支持她拍視頻,她不知道自己要拍點兒什麼才能獲得關注,着急的時候,她就一起去打零工,“分揀一晚上快遞,回來得睡三天才能緩過來。”爲了省錢,他們只喫饅頭榨菜。
堅持了幾個月後,張明霞站在騰格裏沙漠與綠洲交界的邊緣,黝黑黝黑。她戴一頂草帽,捧一隻金燦燦的小蜜瓜,就像她給自己取的暱稱“胖娃娃”。“這次大家相信這是沙漠邊緣產的瓜了吧?”也許是因爲畫面足夠有說服力,有一天晚上,四個男孩子打完工回家,發現直播間居然有了五萬元的銷售。
但興奮沒有持續太久,銷量起得猝不及防,他們備貨不多,只能臨時四處尋找貨源,沒有足夠的貨款,也得想辦法硬湊。
找同學朋友幾百、幾千地借,錢湊不夠,楊小強只能網貸。“上學的時候,我看同學用網貸買球鞋,我就想,爲啥要借錢來花?沒想到,爲了創業,我也得貸那麼多款。”楊小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雖然能還上,但借得太多了,“十幾個平臺,徵信是花的,以至於現在想走正規渠道貸款都貸不了。”
一年下來,賬號的粉絲數量和店鋪的銷售都有了起色,可一算賬,五個人還是賠了20多萬,直接導致另外三個成員退出。
他們栽在熟悉的蘋果上。讀書時就賣過的花牛蘋果,直播間的銷售足夠好,可由於蘋果搶手,頭一天的成本價格還是一斤六七毛錢,第二天就漲到了一塊五一斤。農產品利潤本就微薄,“一斤漲個幾毛錢,就賠完了。”楊小強回憶。
等到銷售靜寧縣特產紅富士,他們吸取花牛蘋果的教訓,決定先囤貨。花牛蘋果和靜寧富士在當地都非常有名,雖然靜寧富士的價格要比花牛蘋果高,但楊小強想,既然能把花牛蘋果賣出去,靜寧富士應該也沒問題。他們每天都去收貨,到手就存放進倉庫。
“有時候會覺得做電商就像在撞大運,有的產品運氣好了,一下就賣爆了,有的產品再怎麼努力,就是賣不動。”楊小強告訴記者。事實上,他們豪賭一把的靜寧富士,恰好就缺少了那點運氣。無論張明霞怎麼努力,靜寧富士的銷量就是上不去。教訓太慘痛,賠得不堪回首,“多少錢已經不記得了,反正一倉庫蘋果先轉進冷庫,第二年實在沒辦法,一毛錢一斤的價格賣出去做果汁了。”

左圖:郭祁琦。 中上圖:介紹農產品的張明霞。 中下圖:2020年6月,張明霞及其他4名返鄉的大學生。 右圖:陳樂
接受現實的前提下把控風險
深入農業和農村,年輕人會陷入一些來自政策和市場的困境。迄今仍讓朱波不平的,是幾年前與當地政府的一次合作。
當時朱波的工廠已經運營兩年,勢頭不錯。當地政府希望朱波的工廠向1076戶農戶出售售價爲6500元一臺的機器。當地政府允諾,農戶向朱波支付2500元,剩餘的4000元,先由朱波的工廠墊資,待農業局和林業局發給農戶共計4000元的補貼到賬後,再由農戶支付給朱波。此後,朱波得到通知,稱相關資金由省一級主管部門統籌整合,“這筆資金就一直欠着,欠了我們500多萬,快六年了,杳無音訊。”
郭祁琦運氣好一些。資金喫緊,他們一邊擴大銷售區域,一邊依靠研發新設備,申請專利。“農機方向的科技創新比較少,我們申報一些省級、國家級的項目會相對容易。”最困難的時候,他們依靠科技部的項目獲得200萬元的補貼才渡過難關。
在郭祁琦的經驗裏,要獲得最新的產業信息,爭取更多的資源,必須要與當地政府保持緊密的聯繫。但問題在於,一旦政府出現變化,企業前景就會遭遇不確定性。在他看來,這就是在農村創業的複雜之處。
“以申請中央和省一級的項目爲例,要申請,你就必須要有跟農戶合作的經歷,要有利益鏈接機制。我們跟農戶一起做事情,所以在申報的資料準備上,我們非常強,做起來也很簡單。但政策風險也特別大,有可能一直拿不到錢。”郭祁琦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張明霞和楊小強遇到的,是另一種困境。農產品上市本就有窗口期,窗口期內,價格又會隨行情波動。做微利的農村電商,如何在庫存滯銷風險和斷貨風險間找到平衡,對年輕的電商人來說,是極大的挑戰。
“做水果,不可控因素太多了。一批貨拿回來,不一定全用得上,殘次率也參差不齊。昨天的殘次率只有5%,今天可能會達到10%。到了10%,今天收的貨可能就不夠發。”楊小強說。
要以嚴格的收購規則要求農戶控制殘次率,這樣的規則屢屢失靈。“並不是因爲我們規模小,而是因爲一個水果的成熟期只有那麼短的時間,如果農戶天天忙着挑選,可能就會導致一些果實直接爛在地裏。以櫻桃爲例,產品本身就很脆弱,挑出來的次果,要麼倒掉,要麼就以一兩塊錢的價格賤賣。相比農戶,我們更有能力承擔風險,因爲我們可以挑選出殘次品走低價的電商平臺。”楊小強說。
“並不是說我們多麼(高尚),其實定規矩的時候,我們的界限也是很明確的,但是在工作中……”電話裏,楊小強和張明霞笑起來。“看着他們那麼辛苦那麼累,要堅持這個界限真的挺難的。前兩天,我們收民勤蜜瓜,一開始就說,就要這麼多,多的一點兒都不能要。”張明霞回憶,當天,供貨大叔送完定好的瓜後,晚上又多拉來一車瓜。
“我們努努力,是能賣掉的。實在不行,我們還可以找其他做電商的朋友一起消化,警告他們,瓜賣不掉就不給飯喫。”張明霞爽朗大笑。
另一個難題來自物流。定西偏遠,物流成本高,再加上西部電商發展整體滯後,導致分撥中心等基礎設施容量和效率都受到限制。“西安、鄭州的分撥中心比較大,一天幾百個掛車都能中轉過來,但西北這邊,哪怕只有幾十個掛車,人手設備也跟不上,貨總得在那裏壓個四五天。”楊小強坦言。
此外,合作的快遞公司價格亦時常波動。“我們發貨的網點,要是完不成他們的任務,運費就好商量,你說啥就是啥,他們一旦完成了任務,價格就高了。”張明霞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說實話,在農村,合同很多時候就是一張‘紙’。”電話裏,楊小強笑着說。這是農村的現實,他不抱怨,只是想方設法在接受現實的前提下把控風險。2022年初,楊小強和張明霞還清了債務,如今,他們始終能留着幾十萬元的現金保底,再也不用靠打零工維持生活。
返鄉是從就業市場突圍的一條好路麼?
今年4月,農業農村部農村研究中心發佈了一項關於“新農人”的報告。這份名爲《數字農人:新媒體賦能下的鄉村發展新動力》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抖音平臺上有超過4萬名三農創作者。其中,城市白領返鄉創業佔比最高,爲21%;農民工和大學生佔比分別爲17%和13%。在所有創作者中,31~40歲的返鄉青年佔比54%。
該報告主持人、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璟告訴記者,抖音的“數字農人”中,有62.96%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33.33%擁有本科及碩士以上學歷,有12.35%成爲農村電商致富帶頭人。
“經課題組調查測算,2021年抖音三農創作者直接間接帶動的就業崗位合計達54.8萬個;帶動二次創業並建立10372個農林牧漁、住宿餐飲、旅遊等行業的中小型企業,保守估計,直接整合帶動130萬周邊農戶。”前述報告稱。
隨着鄉村振興的不斷推進和就業形勢的不斷變化,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開始認真考慮將農村和農業當作自己未來的出路。
在抖音等短視頻平臺檢索“大學生返鄉”“大學生助農創業”“大學生新農人”,有越來越多站在農田裏的年輕面孔,養豬、賣核桃、種菌子、賣茶葉、賣水果、放牛、種藕,他們或是講述自己的返鄉故事,或是展示耕種、收穫的過程。對於這樣的內容,評論區裏總是湧動着善意和鼓勵:“三觀正”“未來可期”“靠自己勞動創造財富不丟人”“只要不啃老,什麼工作都不丟人”。
然而,經過半年的歷練,陳樂認爲,回鄉創業並不適合自己這種既缺乏資金,又缺乏種植知識和技術的“小白”。這與前述研究的調查結論相吻合,報告指出,“新農人”較一般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面臨更突出的土地、融資、僱工、物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困難,還要面對家庭不理解、社會不認可、對農業不熟悉等自身問題。
對於年輕人來說,返鄉真的是一條好出路嗎?
郭祁琦認爲“年輕人要來農村創業,一定要明白‘先穩定、後發展’。你來到這麼窮、基礎設施這麼落後的地方,手裏的錢會非常少,心理落差會非常大,還會遭受家人的質疑、朋友的否定、社會各界的不理解。來了以後,會發現很多事情都不會做,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啥。而且會因爲政府不支持、基礎設施不到位等原因備受挫折。但你要知道自己的野心,而且得能做到韜光養晦,真正藏下來,磨練自己,提升自己。否則這條路你根本走不下去。”返鄉潮流下,郭祁琦提醒。
“我們的教育,整體上還是比較封閉、標準化,不論是高中生還是大學生,思想觀念都還比較封閉,多樣性和創新性不足,被一種標準答案式的思維束縛。這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共性問題,這樣的問題也會表現在他們的職業生涯和生活中。”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回農村創業,真的很累、很累。要回來,主要就是得不怕苦、不怕累,不要怕曬黑了。”張明霞笑着說。
“現在確實有很多人辭職回家創業,拍視頻、記錄生活,但我發現他們壓根就不像一個新農人。”楊小強說着大笑起來,“我看他們打着傘出去拍視頻,就覺得(滑稽)。”楊小強認爲,現在的受衆都足夠聰明,渴望看到真實的生活,如果決心成爲一名新農人,就要做好將自己融入自然的準備。
“既不能說青年人下鄉就沒有好選擇,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爲青年人在城市裏找不到好工作,就該讓他們下鄉。”儲朝暉認爲,當前,對於青年人返鄉的現象不能做一概而論的判斷,返鄉究竟是不是好選擇,要取決於每個人的專業興趣,家庭和學校可以提供參考意見,而政府則應該創造一個城鄉平等發展的機會和局面。
“城鄉一體化,不應該是區分中心和邊緣的一體化,而是平等的一體化。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僅靠一個個個體去解決這些問題,就會非常困難。要解決鄉村的問題,包括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都需要建立這樣平等一體化的社會機制。”儲朝暉提醒。
張璟在調研時發現,目前參與“鄉村振興”的農業經營者、社會組織、MCN機構等主體間的利益連接機制仍不健全。“地方政府該做什麼,經營主體該做什麼,社會組織該做什麼,鄉村培育出的‘新農人’又能做什麼,還不清楚,還沒有磨合好。”張璟告訴記者。
(應受訪者要求,朱波爲化名)
發於2023.7.24總第1101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返鄉突圍就業市場的大學畢業生
記者:王宇([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