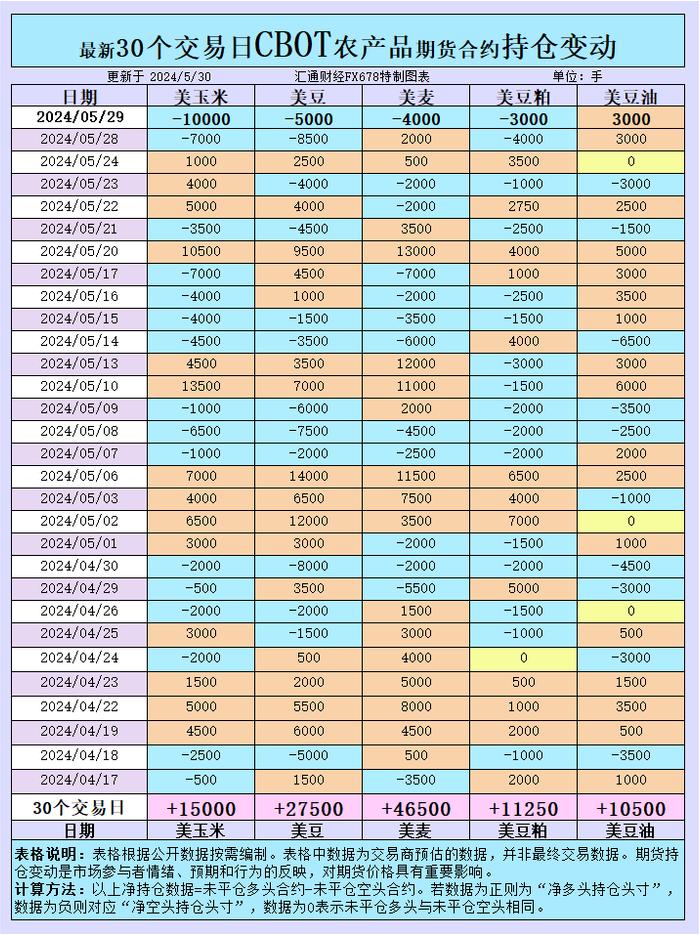WeWork被傳申請破產,市值已蒸發99.3% WeWork中國澄清:已分離,全面本土化
來源:華夏時報

本報記者 李貝貝 上海報道
10月31日,市場消息稱,聯合辦公鼻祖WeWork正考慮在美國新澤西州根據《破產法》第十一章申請破產,時間最早爲下週(11月6日—12日),而WeWork中國市場是否會因此受到衝擊備受業界關注。
11月3日,Wework中國相關人士向《華夏時報》記者澄清, WeWork中國目前是一家獨立運營的公司,早在2020年末即與WeWork分離,獨立爲一家專注在中國市場提供高品質的靈活辦公空間和綜合性辦公服務的企業。
“我們在中國擁有獨立經營和管理能力,而非WeWork的分公司或子公司。”Wework中國相關人士稱,WeWork中國於2016年進入上海,過去7年覆蓋了12個城市、接近100個社區,每天爲7萬多的社區會員提供辦公及空間服務。
WeWork的落幕無疑是共享辦公企業的縮影。從2015年因創業浪潮興起及之後爆發式增長,再到經歷多輪洗牌、知名品牌經營難言樂觀,共享辦公賽道的衰落令人唏噓。不過,儘管行業出現波動,但可以確定的是,“共享辦公”這種商業模式並不會輕易消亡。“對於共享辦公的未來,我認爲它將會更加普及、併成爲一種趨勢。”IPG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肯定地表示。
WeWork市值已蒸發99.3%
據外媒報道,WeWork計劃最早於下週進入破產程序。截至11月3日,WeWork市值僅剩5911萬美元,相比上市初期的90億美元市值已蒸發99.3%。
破產傳言爆出之前,今年8月,WeWork在第二季度業績報告中即已發出破產預警,稱公司面臨持續虧損和辦公空間會員不斷取消租約,嚴重懷疑公司能否持續經營。WeWork在8月份曾對監管部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表示,擔憂其無法繼續進行運營。由於今年上半年的宏觀經濟形勢不利,共享辦公空間需求下滑,公司虧損高達數十億美元。今年,包括首席執行官在內的多位高管均已離職。
公開資料顯示,WeWork成立於2010年,截至2020年底在全球擁有超過150個城市有850多家門店,工位數超過100萬個,會員數量超45萬,營收超過32億美元。2021年10月21日,WeWork以SPAC的方式在紐交所掛牌,發行價爲10.38美元每股,開盤價爲11.28美元每股,較發行價上漲8.7%。
WeWork曾是全球估值最高的“獨角獸”之一,受到過多家風投機構追捧。其中,孫正義的軟銀集團是其最大的投資者,投資總額超過106.5億美元。
但Wework的發展卻是“叫好不叫座”,長期虧損運營。今年二季度,WeWork的收入爲8.44億美元,雖同比小幅增長4%,但淨虧損仍達到3.97億美元,同比增長60%;截至今年6月底,WeWork的長期債務高達29億美元。2022年,WeWork的收入約6.6億美元,淨虧損達到5.07億美元。此外,從2023年下半年到2027年底,WeWork估計有100億美元的租賃義務(支付租金等)到期,從2028年開始還有150億美元的租賃義務到期。
需要注意的是,WeWork破產的消息對其中國市場並未有明顯衝擊。
11月2日,WeWork大中華區副總裁全斌在2023觀點地產年會上透露,受地域文化影響,新冠疫情消散後,WeWork中國整體辦公室需求量迅速回升,但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很多人依然處於居家辦公的狀態,“美國紐約在上半年還是較低的入駐率”。
全斌同時強調,WeWork中國目前是一家獨立運營的公司,其於2016年進入上海,過去7年覆蓋了12個城市、接近100個社區,每天爲7萬多的社區會員提供辦公及空間服務,互聯網公司、新消費公司、專業服務類公司在過去都是其主力會員。
11月3日下午,Wework中國相關人士亦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相關消息對WeWork中國的運營沒有影響,“WeWork中國早在2020年末就與WeWork分離,我們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WeWork中國強調,對中國市場充滿信心。
共享辦公空間行業大洗牌
WeWork的落寞無疑是共享辦公企業的縮影。
公開信息顯示,2015年,“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掀起創業浪潮,共享辦公順勢進入爆發期。2015年,國內共享辦公企業達到2500家,到2018年9月,國內共享辦公平臺超過300家。2019年前,共享辦公的市場規模呈現翻倍式增長,SOHO3Q、優客工場、WE+和裸心社等知名品牌都爭相入場,有些甚至可以和行業巨頭WeWork相競爭。
但隨着競爭的加劇、“雙創”政策紅利的消退,近年共享辦公行業迎來了多輪洗牌,空置率過高,無法擺脫虧損、遲遲難以盈利“上岸”等,也成爲行業的普遍狀況。尤其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大爆發,相繼而來的是大批公司裁員、倒閉,加上居家辦公興起,共享辦公需求不斷被稀釋,“玩家”們愈發窘迫。
以有着“中國版WeWork”稱號的優客工場爲例。財報數據顯示,2021年,優客工場營收10.58億元(人民幣,下同),淨虧損達19.96億元;2022年,優客工場營收6.61億元,同比減少37.52%,淨虧損3.22億元,同比收窄85.09%。
2023年7月開始,優客工場(北京)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多次成爲失信被執行人,涉案金額多達數百萬元,創始人毛大慶也一度被“限高”;同年同時期,另一家共享辦公品牌“辦伴”也曝出經營危機。彼時的報道顯示,辦伴位於北京的辦公室已經關閉,其他城市的業務部門也存在拖欠工資、佣金、物業租金等情況。
受訪人士普遍認爲,截至目前,共享辦公企業仍在生態、圈層、孵化等方面缺乏成熟的成長體系。如何順應時代變遷、迎合市場需求,是“玩家”能夠生存、行業繼續發展的關鍵。
IPG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分析指出,共享辦公的商業模式主要依賴賺取空間的單位面積,“一旦競爭激烈,就很難維持盈利”;在日前舉辦的2023觀點商業年會上,“靈活辦公行業中的領導者”IWG集團中國區總裁胡懋也坦言,共享辦公行業粗看起來好像門檻並不高,“但實踐後發現,並不是那麼簡單”。
共享辦公模式未來或更加普及
儘管行業出現波動,但可以確定的是,“共享辦公”這種商業模式並不會輕易消亡。
“對於共享辦公的未來,我認爲它將會更加普及、併成爲一種趨勢。”柏文喜表示,隨着自由職業者和遠程工作的興起,共享辦公提供了一種靈活、高效的工作方式,可以滿足這些人的需求。同時,共享辦公也可促進社區的形成和交流,爲人們提供更加開放和互動的工作環境。
那麼,如何提高行業從業者的差異化程度、打造更多盈利點?
胡懋認爲,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關鍵是怎麼樣把靈活辦公的需求變成流量,把流量變成“留量”。對此,很重要的一點是,在運營過程中,要運營非常龐大的網絡辦公空間,必須要有可靠的運營系統作爲底層支撐,以及高標準、統一的服務品質把控,專業團隊和健康的業務狀況支持。
對於繼續處於共享辦公賽道的從業者,柏文喜建議他們可以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建立良好的社區、注重空間設計和舒適度、提供專業培訓和講座以及持續創新等。以“多樣化的服務”爲例,除了傳統的辦公空間租賃外,還可以提供其他如會議、打印、茶水等服務,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求等。
對於共享辦公而言,企業的靈活性顯得尤爲重要。WeWork中國方面向記者強調,完全本土化後,積極拓展和創新,滿足新經濟趨勢下企業客戶的各類辦公需求、以及“爲客戶提供靈活的辦公空間和高品質的專業服務”是WeWork中國持續發展的關鍵。
WeWork中國方面介紹說,WeWork中國不斷挖掘用戶需求,持續進行產品升級。在產品矩陣上,針對不同需求、不同企業規模,WeWork中國擁有豐富、全面的產品線,不論是自由職業者、初創企業、快速成長型企業還是成熟型企業,都可以按需靈活搭配產品和服務組合。例如,在今年5月開業的武漢WeWork企業天地1號社區,WeWork中國打造了一款高端商務空間產品“勵帷”,爲注重獨立品牌形象的中大型企業提供專屬空間與一站式服務。
除此之外,WeWork中國還爲入駐企業提供包括法務、人力等方面的增值服務,企業可以按需定製,追求更個性化的工作體驗,搭建了獨有的“中國式共享辦公生態圈”。
責任編輯:張蓓 主編:張豫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