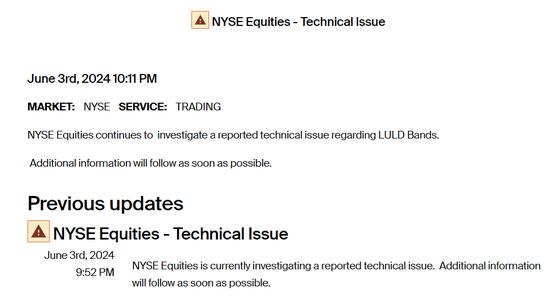張維迎:阿里巴巴的大數據代替不了馬雲
來源:辛莊課堂

計劃經濟的本質
否定企業家精神
經濟發展靠政府還是靠企業家?這個問題學術界爭論了近200年。
歷史經驗證明,靠企業家比靠政府要好。自工業革命以來,企業家主導的經濟體都得到了比較好的經濟發展,政府主導的經濟則表現不佳。
政府主導經濟的完美標本是計劃經濟體制。世界範圍的計劃經濟雖然失敗了,但計劃經濟的理論基礎並沒有得到徹底清理。結果,計劃經濟的幽靈不時穿着各種式樣的馬甲粉墨登場,這些馬甲包括產業政策、發展規劃、宏觀調控、國家創新工程等等。
特別是近幾年來,隨着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出現,計劃經濟的可行性又一次成爲熱門話題。馬雲在一次演講中的如下一段話,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馬雲說:
“昨天在一場交流裏,(討論到)馬克思主義講到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到底哪個好?我認爲我們過去的一百多年來一直覺得市場經濟非常之好,我個人的看法是,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爲什麼?因爲數據的獲取,市場這隻無形的手有可能被我們發現。中醫的醫生在沒有發現X光和CT機之前,是沒辦法把肚子打開來看一看,所以中醫的號脈,望、聞、問、切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診斷系統。但是X光和CT機出來以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相信數據時代,我們對國家和世界的經濟數據明確的掌握,就像我們將會有一個X光機和CT機,所以30年以後將會有新的理論出來。”[i]
馬雲的觀點可以簡單概括爲“大數據計劃經濟論”(big data-based planned economy)。馬雲本人作爲一位傑出的企業家,而不是經濟理論家,是否嚴肅思考過他講話的後果並不重要,但他提出的問題需要我們嚴肅對待。這不僅是因爲他的觀點得到一些人的附和,可能產生一些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甚至也不希望的後果。更重要的是,自計算機誕生以來,時不時有人說,計算機儲存信息能力和計算速度的突飛猛進,使得計劃經濟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具有可行性。
大數據能否復活計劃經濟?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大數據能否替代企業家精神?
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徵是,用系統的、制度性的強制力量否定企業家精神,剝奪個人選擇的自由,特別是創業和創新的自由。計劃經濟下,投機倒把都是犯罪,不可能有企業家活動。
企業家如何做決策?
按照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觀點,發現、創造、以價格或非價格的方式傳遞信息,是人類企業家精神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企業家。但鑑於企業家的重要性,有必要從通常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的角度論證一下大數據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
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裏,個人決策的目標和手段都是給定的,所謂決策就是在給定的手段中選擇能夠最大化給定目標的手段。但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指出的,這與真正的企業家決策想去甚遠!現實中,企業家決策不是給定手段——目標下的決策,而是尋找、識別和選擇目標和手段本身!一個人企業家精神的高低,很大程度取決於感知和尋找目標和獲得手段能力的高低。如果手段和目標是給定的,並且是相同的,在同樣的數據下,所有理性人都會做出相同的選擇。但現實中,即使基於同樣的數據、同樣的硬知識,不同的企業家也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爲什麼?因爲企業家決策不僅取決於數據、硬知識,更依賴於默性知識。對企業家而言,個人對市場前景、技術前景和資源可獲得性的想象力、感知、判斷力,纔是最爲關鍵的。
當然,大數據對企業家是有用的,因爲企業家在決策時需要數據。但真正的企業家決策一定是超越數據的,當然也是超越大數據的。僅僅基於大數據的決策充其量只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僅僅基於大數據做決策的企業家,不是真正的企業家,只是管理者。企業家必須想象和看到大數據不能告訴他的東西。
大數據只是一種生意。在沒有大數據的時候,發現和使用大數據是企業家的功能。但一旦大數據普及開來,大數據就成爲“哥倫布的雞蛋”,不再是企業家的功能,正如當所有人都在使用電的時候,電就不再是任何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一樣。真正的企業家必須超越大數據。
熊彼特將企業家精神等於創新。數據不能告訴企業家創新什麼。比如,有關郵政馬車運輸業的數據不能告訴卡爾·奔茨和戴姆勒發明汽車;否則,發明汽車的就應該是馬車伕,而不是卡爾·奔茨和戴姆勒。有關計算機市場的數據也不可能告訴比爾·蓋茨創辦軟件產業;否則,創造軟件產業的就是IBM而不是比爾·蓋茨。同樣,數據也不可能告訴馬化騰應該創造微信;否則,發明微信的就應該是中國移動公司而不是騰訊公司!
讓我再以電影業爲例說明這一點。
設想一個電影製片公司可以獲得過去幾十年所有影片的大數據,包括每個影片的觀衆人數,觀衆的年齡結構、地域分佈、時段分佈,票房收入,所有媒體上發表的影評,甚至觀衆在觀看時的表情(如笑了多少次、哭了多長時間),等等。這樣的大數據能告訴我們下一個最賣座的電影是什麼嗎?不可能!
每一部新電影都是一項新發明,我們無法預料哪部電影會受到公衆歡迎。如同好萊塢資深編劇威廉·戈德曼指出的:“環球影業公司這個最大的電影公司當初爲什麼拒絕出品《星球大戰》?因爲沒有人,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有人知道哪部電影會大賣,哪部電影會票房慘淡。”[ii]
同樣,圖書市場也如此。亞馬遜公司無疑擁有圖書市場的大數據,它可以根據客戶過去查看和購書的記錄,向你推薦書。但亞馬遜公司的大數據並不能告訴我們,未來哪一本書會暢銷,更不可能告訴每個作者應該寫什麼樣的書!如果一個作者想根據大數據制定自己的寫作計劃,那他(她)十有八九會失敗!如果計劃機關根據亞馬遜或噹噹網的大數據制定圖書出版計劃,那一定是圖書市場的災難!
我不是否定大數據的意義,而是說大數據不能替代企業家的想象力和判斷。讓我用運輸業的集裝箱聯運革命說明這一點。[iii]
以集裝箱革命爲例
集裝箱聯運(intermodal shipping containerization)是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對國際貿易、經濟全球化、特別是供應鏈的全球分佈貢獻巨大。在1950年代之前,無論海運,還是鐵路運輸、汽車運輸,貨物都是散裝的,同一貨物從生產商到零售商,中間需要經過多次重複裝卸,費時、費力,成本高,失竊多,也不可靠。碼頭上,貨物堆積如山,讓人印象深刻。

早在1937年,美國北卡州的卡車司機馬爾科姆·珀塞爾·麥克萊恩(Malcolm Purcell McLean)就有了集裝箱運輸的想法。1955年,他開始行動了。他賣掉了他在家族運輸企業中的股份,貸款買了7艘舊油輪,將其改造成上面可以堆放集裝箱的平臺船;接下來又把卡車貨廂加固成可以裝載集裝箱的拖車。他在油輪的甲板上方安裝了鋼架,裝上可以快速安放集裝箱的插板。他還改造了碼頭。1956年4月26日,一艘經過改造的二戰時期的舊油輪從新澤西紐瓦克碼頭出發,駛向波士頓,船上裝載着58個集裝箱。他成功了!接下來,麥克萊恩對其他幾艘舊船也做了相同的改造,開通了紐約-德克薩斯集裝箱運輸航線。在他的示範下,其他船運公司紛紛跟進。到1960年代末,集裝箱運輸時代到來了。鐵路運輸也迅速集裝箱化。到1990年代晚期,國際貿易貨物總價值的60%是通過集裝箱運輸的。與散裝運輸相比,從生產者發貨到買家收貨,運輸時間降低了95%,單位運輸成本下架幅度更大!可以說,沒有集裝箱運輸革命,就不可能有1970年代之後出現的產業鏈的全球化分工。
爲什麼是麥克萊恩,而不是原來的輪船運輸公司或其他什麼人“發明”了集裝箱運輸?這無法用數據解釋。就數據而言,麥克萊恩最初只是個卡車運輸個體戶,他掌握的數據與傳統的船運公司相比,根本不是一個量級;就技術含量而言,集裝箱也算不上真正的“發明”。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就有了不同尺寸的小集裝箱的使用,只是沒有標準化的商業化集裝箱運營。
根本的原因是靈感,麥克萊恩比別人領先一步有了這種靈感。他後來在一次接受採訪時回憶說,在1937年的一天,他正煩惱地等待傳統的貨物裝卸時,突然就冒充了這個想法:
“我不得不耗費一天的大部分時光等待卸貨,我坐在駕駛室裏無所事事,看着碼頭工人裝載其他貨物。眼睜睜看着大量時間和金錢被浪費了,我很震驚…當我在熬時間的時候,一個想法湧現出來:把我的貨廂吊起,不觸動裏面的任何東西,然後直接放在船上,那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啊!”
總之,我要強調的是,任何數據——無論它多大,都不可能代替企業家的警覺和判斷。阿里巴巴的大數據代替不了馬雲,全社會的大數據代替不了企業家羣體。如果政府想在大數據基礎上建立計劃經濟(包括產業政策),不僅會消滅大數據本身,也會消滅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和技術進步。
本文選自作者《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第3章,海南出版社/理想國公司2022年版。
[i] 馬雲是在2016年11月19日 “2016世界浙商上海論壇暨上海市浙江商會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講這番話的,這次論壇由浙商總會和上海浙江商會聯合舉辦。馬雲的講話很口語化,爲了閱讀的方便,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我做了適當的文字通順。原文見http://tech.sina.com.cn/i/2016-11-20/doc-ifxxwrwk1500894.shtml
[ii] 轉引自威廉·伊斯特利《威權政治》第322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iii] 詳細討論見Vaclav Smil. 2006. Transform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P.220-22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