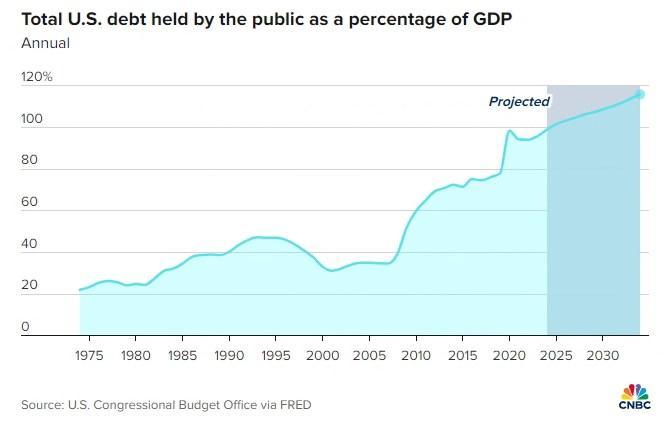20年後重啓 中央爲何又開始大幅審批縣改市?
原標題:20年後重啓!中央爲何又開始大幅審批通過縣改市?
時隔20年,縣改市重新啓動,明確了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的路徑選擇。但若想真正推動中小城市發展,關鍵不在於提升城市行政級別,而是需要打破現行等級化的城市管理體制。
![《財經》記者 熊平平 實習生 許向陽/文 朱弢/編輯]() 《財經》記者 熊平平 實習生 許向陽/文 朱弢/編輯
“我是平泉市人。”李淳在向朋友介紹自己家鄉時,逐漸將“承德市”改爲“平泉市”。“以前說平泉縣,沒多少人知道,還會給陌生人一種自己是小地方來的感覺。”
平泉原屬承德市下轄縣,2017年4月9日,經國務院批准、民政部批覆,平泉正式升級爲縣級市,由河北省直轄,承德市代管。
“市”與“縣”雖只一字之差,但在現行的行政區劃體制中,平泉已經比周邊的寬城縣、灤平縣高了半個層級,成爲全國366個縣級市陣營中一員。與平泉類似,近五年先後有16個縣升級爲市。
距1997年國務院暫停縣改市至今已20年,正在重啓的新一輪縣改市,能否推動中國城市發展路徑轉軌?
升級帶來機會?
駕車從北京向北出發,途經京承高速、大廣高速、長深高速,行駛300公里後到達河北省平泉市。在接近平泉的高速公路兩側,“慶祝平泉撤縣設市”的大幅廣告顯眼,進入市區,市委市政府大樓也都掛上嶄新的門牌。
平泉市發改局副局長李慧東介紹,平泉在1997年就踏在了撤縣設市的門檻上,因國務院凍結審批後被擱置,但他們並沒有放棄,近年來持續向國務院提交改市申請材料,2017年4月9日終於如願以償。
儘管升格了,但平泉本身並非經濟強縣及人口大縣。民政部網站數據顯示,平泉人口在全國1726個縣、縣級市中排698位。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166.8億元、全部財政收入10.8億元,與之臨近的寬城縣同期GDP爲208.1億元,財政收入爲14.5億元。
在北京工作的平泉人李淳說,平泉能夠被國務院批准升級,出乎他的意料,“僅與承德其他縣比較,平泉經濟發展就不及寬城,放到全國比更爲普通。”
爲何在經濟數據上表現一般的平泉,能夠成功升級?
《財經》記者 熊平平 實習生 許向陽/文 朱弢/編輯
“我是平泉市人。”李淳在向朋友介紹自己家鄉時,逐漸將“承德市”改爲“平泉市”。“以前說平泉縣,沒多少人知道,還會給陌生人一種自己是小地方來的感覺。”
平泉原屬承德市下轄縣,2017年4月9日,經國務院批准、民政部批覆,平泉正式升級爲縣級市,由河北省直轄,承德市代管。
“市”與“縣”雖只一字之差,但在現行的行政區劃體制中,平泉已經比周邊的寬城縣、灤平縣高了半個層級,成爲全國366個縣級市陣營中一員。與平泉類似,近五年先後有16個縣升級爲市。
距1997年國務院暫停縣改市至今已20年,正在重啓的新一輪縣改市,能否推動中國城市發展路徑轉軌?
升級帶來機會?
駕車從北京向北出發,途經京承高速、大廣高速、長深高速,行駛300公里後到達河北省平泉市。在接近平泉的高速公路兩側,“慶祝平泉撤縣設市”的大幅廣告顯眼,進入市區,市委市政府大樓也都掛上嶄新的門牌。
平泉市發改局副局長李慧東介紹,平泉在1997年就踏在了撤縣設市的門檻上,因國務院凍結審批後被擱置,但他們並沒有放棄,近年來持續向國務院提交改市申請材料,2017年4月9日終於如願以償。
儘管升格了,但平泉本身並非經濟強縣及人口大縣。民政部網站數據顯示,平泉人口在全國1726個縣、縣級市中排698位。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166.8億元、全部財政收入10.8億元,與之臨近的寬城縣同期GDP爲208.1億元,財政收入爲14.5億元。
在北京工作的平泉人李淳說,平泉能夠被國務院批准升級,出乎他的意料,“僅與承德其他縣比較,平泉經濟發展就不及寬城,放到全國比更爲普通。”
爲何在經濟數據上表現一般的平泉,能夠成功升級?
![]() 李慧東對此解釋,一是形勢,承德是河北少有的無縣級市地區;二是空間區位,平泉位於河北東北部,系遼寧、內蒙古、河北三省份交界地,東接遼寧凌源市,北臨內蒙古赤峯寧城縣;三是經濟結構,整個承德都是偏資源型結構,礦產資源佔到其經濟規模的40%-50%,而平泉對礦產資源依賴較小,高附加值農產品加工、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逐漸成形;四是交通區位,錦承鐵路設有平泉站,在修的京沈高鐵在平泉也有站點,以短途運輸爲主的平泉機場在2016年底正式運營。
“將平泉打造成三省交界處一個比較大的中心城鎮,從而拉動周邊地區發展,形成集聚效應。”李慧東說,這是平泉升級後的設想。
剛升級爲市僅四個月時間,平泉發改、財政、規劃、國土等核心職能部門已有相應藍圖。
從縣改爲市,基本邏輯是未來優先發展城市經濟,擴大工業與服務業比例。發改局已引入多項基金,推動工業發展。
平泉市規劃城管局副局長王守乾表示,未來平泉會擴大城市空間,重點圍繞中心城區規劃發展,包括對位於北城的高鐵新區、臥龍新區的開發建設。
市財政局副局長史景儒稱,改市後,平泉的財政收入與支出受影響較大。在收入上,城建稅徵收標準由原來5%升至7%,城建部門正在向上級政府申請專項資金支持,土地出讓金也相應會增加;在支出上,會由原來對農業爲主轉向以工業、城市建設爲主。
但對於平泉市出租車司機鄒琪和在北京工作的平泉人張武威而言,改市並沒有對他們的生活帶來直接影響。張武威說,家鄉平泉沒有好的工作機會,自己回平泉發展可能性極小。
縣改市後,倒是對鄒琪帶來困擾,由於縣改市等“利好”刺激,平泉房價大幅上漲,鄒琪離買房又遠了一步。
據李慧東介紹,今年上半年,平泉房價漲幅爲每平方米1500元,這是當地樓市第一次有這麼大漲幅。5月22日,平泉市住建局發文要求“商品房每平方米不超6000元”,但實際情況是,開發商用推遲公佈價格、收取裝修費等方式漲價,位於平泉市政府附近小區房價已近每平方米1萬元。
地方政府爲何熱衷縣改市
對於平泉50歲以上公職人員而言,撤縣設市對於他們並不陌生。1981年起便有過一輪全國範圍的撤縣設市,自1997年被國務院叫停,縣改市沉寂近20年。
198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以大中城市爲依託,形成各類經濟中心”,隨後有31個縣撤縣設市。1993年5月,國務院同意民政部《關於調整設市標準的報告》,明確撤縣設市適用範圍、人口總數、經濟指標等。此後縣改市進入井噴期,截至1998年底,全國縣級市數量達437個,其中近350個爲縣改市。
1997年,國務院發文凍結縣改市審批,撤縣設市進入了嚴格管控階段。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表示,之所以叫停,是由於當時許多縣並沒有達到撤縣設市標準就獲得審批,出現縣改市“大躍進”,很多縣級市以農村爲主,造成“假性城市化”,形成耕地佔用、權力尋租等衆多問題。
1993年版撤縣設市標準爲:在人口密度爲350人/平方公里的縣,政府駐地所在鎮總人口不低於12萬人,其中非農人口不低於10萬人;全縣GDP不低於60億元,財政收入不少於3億元;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達75%以上;城區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設施較爲完善。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爲100人-350 人的縣,設市的標準更低一些。
李慧東對此解釋,一是形勢,承德是河北少有的無縣級市地區;二是空間區位,平泉位於河北東北部,系遼寧、內蒙古、河北三省份交界地,東接遼寧凌源市,北臨內蒙古赤峯寧城縣;三是經濟結構,整個承德都是偏資源型結構,礦產資源佔到其經濟規模的40%-50%,而平泉對礦產資源依賴較小,高附加值農產品加工、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逐漸成形;四是交通區位,錦承鐵路設有平泉站,在修的京沈高鐵在平泉也有站點,以短途運輸爲主的平泉機場在2016年底正式運營。
“將平泉打造成三省交界處一個比較大的中心城鎮,從而拉動周邊地區發展,形成集聚效應。”李慧東說,這是平泉升級後的設想。
剛升級爲市僅四個月時間,平泉發改、財政、規劃、國土等核心職能部門已有相應藍圖。
從縣改爲市,基本邏輯是未來優先發展城市經濟,擴大工業與服務業比例。發改局已引入多項基金,推動工業發展。
平泉市規劃城管局副局長王守乾表示,未來平泉會擴大城市空間,重點圍繞中心城區規劃發展,包括對位於北城的高鐵新區、臥龍新區的開發建設。
市財政局副局長史景儒稱,改市後,平泉的財政收入與支出受影響較大。在收入上,城建稅徵收標準由原來5%升至7%,城建部門正在向上級政府申請專項資金支持,土地出讓金也相應會增加;在支出上,會由原來對農業爲主轉向以工業、城市建設爲主。
但對於平泉市出租車司機鄒琪和在北京工作的平泉人張武威而言,改市並沒有對他們的生活帶來直接影響。張武威說,家鄉平泉沒有好的工作機會,自己回平泉發展可能性極小。
縣改市後,倒是對鄒琪帶來困擾,由於縣改市等“利好”刺激,平泉房價大幅上漲,鄒琪離買房又遠了一步。
據李慧東介紹,今年上半年,平泉房價漲幅爲每平方米1500元,這是當地樓市第一次有這麼大漲幅。5月22日,平泉市住建局發文要求“商品房每平方米不超6000元”,但實際情況是,開發商用推遲公佈價格、收取裝修費等方式漲價,位於平泉市政府附近小區房價已近每平方米1萬元。
地方政府爲何熱衷縣改市
對於平泉50歲以上公職人員而言,撤縣設市對於他們並不陌生。1981年起便有過一輪全國範圍的撤縣設市,自1997年被國務院叫停,縣改市沉寂近20年。
198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以大中城市爲依託,形成各類經濟中心”,隨後有31個縣撤縣設市。1993年5月,國務院同意民政部《關於調整設市標準的報告》,明確撤縣設市適用範圍、人口總數、經濟指標等。此後縣改市進入井噴期,截至1998年底,全國縣級市數量達437個,其中近350個爲縣改市。
1997年,國務院發文凍結縣改市審批,撤縣設市進入了嚴格管控階段。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表示,之所以叫停,是由於當時許多縣並沒有達到撤縣設市標準就獲得審批,出現縣改市“大躍進”,很多縣級市以農村爲主,造成“假性城市化”,形成耕地佔用、權力尋租等衆多問題。
1993年版撤縣設市標準爲:在人口密度爲350人/平方公里的縣,政府駐地所在鎮總人口不低於12萬人,其中非農人口不低於10萬人;全縣GDP不低於60億元,財政收入不少於3億元;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達75%以上;城區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設施較爲完善。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爲100人-350 人的縣,設市的標準更低一些。
![]()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在研究中發現,1994年-1997年間共有99個縣改市案例,但如果嚴格按照1993年的民政部標準,僅有6個案例符合所有指標,另有24個縣三項大類指標一項都不滿足,但也被批准。
即使是在國務院凍結縣改市期間,對縣改市的追逐熱潮從未停止。民政部數據顯示,2007年至2008年,全國各地曾掀起過一輪申請熱潮,江西南昌縣、豐城縣,山東單縣等多地開展撤縣設市籌備工作,但民政部並未審批放行。
《南方週末》報道,自1997年開始,全國至少有138個縣(地區、盟)明確提出改頭換面的設市設想。
地方政府爲何熱衷縣改市?據李力行等人的統計,相比於普通的縣,縣級市在稅費收入、審批權限、土地指標、財政供養人口、官員級別等多方面均有更大吸引力。
新型城鎮化或更倚仗小城鎮
與平泉同期實現升級的,還有另外5個縣,分別是湖南寧鄉、陝西神木、浙江玉環、四川隆昌、貴州盤縣。
新一輪縣改市於2013年正式放閘,截至當前已有吉林扶余,雲南彌勒、香格里拉等16個縣成功升級。(見圖1)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在研究中發現,1994年-1997年間共有99個縣改市案例,但如果嚴格按照1993年的民政部標準,僅有6個案例符合所有指標,另有24個縣三項大類指標一項都不滿足,但也被批准。
即使是在國務院凍結縣改市期間,對縣改市的追逐熱潮從未停止。民政部數據顯示,2007年至2008年,全國各地曾掀起過一輪申請熱潮,江西南昌縣、豐城縣,山東單縣等多地開展撤縣設市籌備工作,但民政部並未審批放行。
《南方週末》報道,自1997年開始,全國至少有138個縣(地區、盟)明確提出改頭換面的設市設想。
地方政府爲何熱衷縣改市?據李力行等人的統計,相比於普通的縣,縣級市在稅費收入、審批權限、土地指標、財政供養人口、官員級別等多方面均有更大吸引力。
新型城鎮化或更倚仗小城鎮
與平泉同期實現升級的,還有另外5個縣,分別是湖南寧鄉、陝西神木、浙江玉環、四川隆昌、貴州盤縣。
新一輪縣改市於2013年正式放閘,截至當前已有吉林扶余,雲南彌勒、香格里拉等16個縣成功升級。(見圖1)
![]()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肖金成表示,2013年國家發改委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通知,其中“改市”字眼再現。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對具備行政區劃調整條件的縣可有序改市。”
“全國1000多個縣,每一個都有撤縣設市的衝動。”肖金成表示,因縣改市涉及政府部門自身利益,爭取獲批升級爲市,成爲許多縣政府的首要任務。
肖金成介紹,審批時,民政部並非採用單一經濟指標考量,還結合了空間位置因素。如2017年獲批的6市中,陝西神木、湖南寧鄉、浙江玉環三地均屬全國百強縣,2016年寧鄉GDP達1098億元,而河北平泉、四川隆昌、貴州盤縣經濟實力偏弱,2016年平泉GDP僅166.8億元,但三地均位於跨省交界處。
2016年12月19日,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陳亞軍曾向媒體透露,“新的縣級市設立標準和程序制定完成。”但該份標準並未向社會公佈。
2017年4月19日,《第一財經日報》援引一內部人士的話稱,新標準應屬於民政部內部掌握,不會對外公佈。一旦發佈標準,所有符合條件的縣都想改爲市,民政部將難以審批。
爲何選擇在2017年大幅度審批通過縣改市?
民政部在5月27日作出回應稱,全國城鎮化水平已達57.35%,但縣級市數量持續減少了80餘個。“縣級市數量的持續減少,導致中小城市發展滯後,帶來大中小城市發展失衡、城鎮化佈局形態不合理、人口城鎮化滯後、大城市病凸顯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
肖金成對《財經》記者介紹,此時重啓縣改市,最根本的原因是當前中國的城市數量太少,只有600多座行政區劃意義上的城市,難以滿足人口城鎮化需要。(見圖2)
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肖金成表示,2013年國家發改委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通知,其中“改市”字眼再現。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對具備行政區劃調整條件的縣可有序改市。”
“全國1000多個縣,每一個都有撤縣設市的衝動。”肖金成表示,因縣改市涉及政府部門自身利益,爭取獲批升級爲市,成爲許多縣政府的首要任務。
肖金成介紹,審批時,民政部並非採用單一經濟指標考量,還結合了空間位置因素。如2017年獲批的6市中,陝西神木、湖南寧鄉、浙江玉環三地均屬全國百強縣,2016年寧鄉GDP達1098億元,而河北平泉、四川隆昌、貴州盤縣經濟實力偏弱,2016年平泉GDP僅166.8億元,但三地均位於跨省交界處。
2016年12月19日,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陳亞軍曾向媒體透露,“新的縣級市設立標準和程序制定完成。”但該份標準並未向社會公佈。
2017年4月19日,《第一財經日報》援引一內部人士的話稱,新標準應屬於民政部內部掌握,不會對外公佈。一旦發佈標準,所有符合條件的縣都想改爲市,民政部將難以審批。
爲何選擇在2017年大幅度審批通過縣改市?
民政部在5月27日作出回應稱,全國城鎮化水平已達57.35%,但縣級市數量持續減少了80餘個。“縣級市數量的持續減少,導致中小城市發展滯後,帶來大中小城市發展失衡、城鎮化佈局形態不合理、人口城鎮化滯後、大城市病凸顯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
肖金成對《財經》記者介紹,此時重啓縣改市,最根本的原因是當前中國的城市數量太少,只有600多座行政區劃意義上的城市,難以滿足人口城鎮化需要。(見圖2)
![]() 依據民政部公開數據推算,當前包括直轄市、地級市、自治州、縣級市在內的城市數量爲693座,國家統計局公佈2016年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爲7.93億人,粗略計算,每座城市平均有114萬人口,而許多城市還需消化自身大量農村戶籍人口,城市總體壓力較大。
馮俏彬在其調研中發現,縣改市停滯20年間,許多縣的經濟、人口、社會並沒有停滯,許多發達縣域經濟的行政區劃與經濟社會發展嚴重脫節,如仍按照縣的標準規劃城市,會帶來諸多隱患。
追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城市發展軌跡,中央政府思路經歷過多次轉向。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量農村勞動力得以解放,各類城鎮迅速發展,優先發展中小城鎮成爲當時政策主導思想,上一輪縣改市正是在這一時期快速發展。由於對全國縣改市“大躍進”風險及佔用大量耕地、戶籍等問題的擔心,1997年縣改市暫停,城市發展轉向大中型城市,縣(市)改區成爲大中型城市擴張發展空間、獲取資源的最好辦法。
李力行對《財經》記者表示,縣改市沉寂近二十年後重啓,背後體現了城市化發展思路再次轉向,多份政策文件出現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爲重點的提法,新型城鎮化未來或更加倚重中小城鎮的發展。
改市後,能否真正推動發展?
平泉市各部門對縣改市後的發展充滿期待,但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最核心問題是:在獲得更大行政權限及更多社會資源後,平泉經濟能否發展得更好,能否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能否吸引更多人口前來擇業、定居?
37歲的平泉人劉煥逸已在北京工作14年,他告訴《財經》記者,“回平泉並不是年輕人好的選擇,養老是好去處。”劉煥逸解釋,最核心問題是平泉產業太少,能提供的機會匱乏。
平泉市城市規劃部門、發改局官員也意識到,要吸引人口,核心是發展產業。因此在平泉發展中,城市規劃上部署航空產業、裝備製造、光伏等產業的聚集,發改局爲企業提供投融資便利,都在爲發展產業創造條件。
在撤縣設市後,城市除了可獲得更多的行政權限外,對該城市的招商引資、爭取項目落地等方面都有積極影響,進而逐漸形成集聚效應。馮俏彬認爲,平泉等地纔剛獲批改市,須等一段時間才能看到政策的效果。
但劉煥逸表示,平泉的集聚效應有限,一方面是平泉人更願意去往京津等大城市發展,其次是承德。未來平泉更像是一個交通樞紐點,周圍縣城居民會來平泉坐高鐵。
按照既有經驗來看,平泉改市後挑戰重重。李力行在其研究中,將上一輪縣改市未能促進當地發展的原因之一歸結爲:縣級市的規模過小,難以發揮城市的集聚效應。
從上世紀90年代的90多個縣改市經驗來看,改市對於當地經濟增長、公共服務提升的助推並不明顯。李力行等人將1994年-1997年間90多個縣改市數據與1537個普通縣對比,發現縣改市後的經濟增長率並未優於普通縣,且經濟快速增長通常發生在申請縣改市期間,一旦獲批後,經濟回落迅速(見圖3)。其次,在創造就業、提供教育和衛生等公共服務等方面,也沒有明顯優於普通縣。
依據民政部公開數據推算,當前包括直轄市、地級市、自治州、縣級市在內的城市數量爲693座,國家統計局公佈2016年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爲7.93億人,粗略計算,每座城市平均有114萬人口,而許多城市還需消化自身大量農村戶籍人口,城市總體壓力較大。
馮俏彬在其調研中發現,縣改市停滯20年間,許多縣的經濟、人口、社會並沒有停滯,許多發達縣域經濟的行政區劃與經濟社會發展嚴重脫節,如仍按照縣的標準規劃城市,會帶來諸多隱患。
追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城市發展軌跡,中央政府思路經歷過多次轉向。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量農村勞動力得以解放,各類城鎮迅速發展,優先發展中小城鎮成爲當時政策主導思想,上一輪縣改市正是在這一時期快速發展。由於對全國縣改市“大躍進”風險及佔用大量耕地、戶籍等問題的擔心,1997年縣改市暫停,城市發展轉向大中型城市,縣(市)改區成爲大中型城市擴張發展空間、獲取資源的最好辦法。
李力行對《財經》記者表示,縣改市沉寂近二十年後重啓,背後體現了城市化發展思路再次轉向,多份政策文件出現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爲重點的提法,新型城鎮化未來或更加倚重中小城鎮的發展。
改市後,能否真正推動發展?
平泉市各部門對縣改市後的發展充滿期待,但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最核心問題是:在獲得更大行政權限及更多社會資源後,平泉經濟能否發展得更好,能否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能否吸引更多人口前來擇業、定居?
37歲的平泉人劉煥逸已在北京工作14年,他告訴《財經》記者,“回平泉並不是年輕人好的選擇,養老是好去處。”劉煥逸解釋,最核心問題是平泉產業太少,能提供的機會匱乏。
平泉市城市規劃部門、發改局官員也意識到,要吸引人口,核心是發展產業。因此在平泉發展中,城市規劃上部署航空產業、裝備製造、光伏等產業的聚集,發改局爲企業提供投融資便利,都在爲發展產業創造條件。
在撤縣設市後,城市除了可獲得更多的行政權限外,對該城市的招商引資、爭取項目落地等方面都有積極影響,進而逐漸形成集聚效應。馮俏彬認爲,平泉等地纔剛獲批改市,須等一段時間才能看到政策的效果。
但劉煥逸表示,平泉的集聚效應有限,一方面是平泉人更願意去往京津等大城市發展,其次是承德。未來平泉更像是一個交通樞紐點,周圍縣城居民會來平泉坐高鐵。
按照既有經驗來看,平泉改市後挑戰重重。李力行在其研究中,將上一輪縣改市未能促進當地發展的原因之一歸結爲:縣級市的規模過小,難以發揮城市的集聚效應。
從上世紀90年代的90多個縣改市經驗來看,改市對於當地經濟增長、公共服務提升的助推並不明顯。李力行等人將1994年-1997年間90多個縣改市數據與1537個普通縣對比,發現縣改市後的經濟增長率並未優於普通縣,且經濟快速增長通常發生在申請縣改市期間,一旦獲批後,經濟回落迅速(見圖3)。其次,在創造就業、提供教育和衛生等公共服務等方面,也沒有明顯優於普通縣。
![]() 研究還發現,縣級市在財政收入、公務編制人員數量、政府機構規模方面有更快擴張,而後者的擴張會侵蝕公共財政,對提升公共服務產生負面效果。
平泉市一位官員向記者透露,平泉縣改市後,爲鼓舞公職人員士氣,在經過上級政府批准後,財政局向黨政機關公職人員增加了物業費、通訊費等補助。
此外,平泉市另一官員稱,縣改市後,政府部門的編制人數、機構數量、三公經費,都不會增加,但平泉市正在積極爭取擴大編制限額。
李力行認爲,未能促進縣級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另一原因,是行政主導的設市機制,僵化的行政區劃管理應該加以改變。
僅從行政區劃上做文章,對解決當前的城鎮化難題並無實質意義。肖金成表示,城市的自然形成,與行政區劃的調整關係並不大。縣屬於農村行政區,只有中心城區和下屬鄉鎮駐所地屬於城鎮概念,更多區域屬於農村,僅通過行政手段將其改爲城市行政區,但大部分地區爲農村的自然狀態並未改變。
肖金成還指出,擺在縣改市道路上的土地產權問題就存在體制性障礙。縣城土地和城市土地性質不同,縣城某種程度屬集體土地,產權不明晰,在未來進行商業開發、園區設置時,都將會有障礙。另外,在縣改市後,原來城鎮區域是否應該按照城市標準設置,目前很難講清楚,比如一部分城鎮居民的住房仍然屬於農民宅基地。
值得推敲的是,爲什麼所有的縣都想改市、改區,不願意停留在目前的狀態,而國外很多國家是沒有縣與市的區別,這就是中國城市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重啓縣改市,突破城鎮化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這遠遠不夠,並沒有做出實質性改變。”肖金成指出。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曾多次指出,中國城市的行政等級決定資源的流向。不對這一金字塔結構的行政區劃體制進行改革,中小城市難有大的發展。
研究還發現,縣級市在財政收入、公務編制人員數量、政府機構規模方面有更快擴張,而後者的擴張會侵蝕公共財政,對提升公共服務產生負面效果。
平泉市一位官員向記者透露,平泉縣改市後,爲鼓舞公職人員士氣,在經過上級政府批准後,財政局向黨政機關公職人員增加了物業費、通訊費等補助。
此外,平泉市另一官員稱,縣改市後,政府部門的編制人數、機構數量、三公經費,都不會增加,但平泉市正在積極爭取擴大編制限額。
李力行認爲,未能促進縣級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另一原因,是行政主導的設市機制,僵化的行政區劃管理應該加以改變。
僅從行政區劃上做文章,對解決當前的城鎮化難題並無實質意義。肖金成表示,城市的自然形成,與行政區劃的調整關係並不大。縣屬於農村行政區,只有中心城區和下屬鄉鎮駐所地屬於城鎮概念,更多區域屬於農村,僅通過行政手段將其改爲城市行政區,但大部分地區爲農村的自然狀態並未改變。
肖金成還指出,擺在縣改市道路上的土地產權問題就存在體制性障礙。縣城土地和城市土地性質不同,縣城某種程度屬集體土地,產權不明晰,在未來進行商業開發、園區設置時,都將會有障礙。另外,在縣改市後,原來城鎮區域是否應該按照城市標準設置,目前很難講清楚,比如一部分城鎮居民的住房仍然屬於農民宅基地。
值得推敲的是,爲什麼所有的縣都想改市、改區,不願意停留在目前的狀態,而國外很多國家是沒有縣與市的區別,這就是中國城市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重啓縣改市,突破城鎮化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這遠遠不夠,並沒有做出實質性改變。”肖金成指出。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曾多次指出,中國城市的行政等級決定資源的流向。不對這一金字塔結構的行政區劃體制進行改革,中小城市難有大的發展。
 《財經》記者 熊平平 實習生 許向陽/文 朱弢/編輯
《財經》記者 熊平平 實習生 許向陽/文 朱弢/編輯




責任編輯:張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