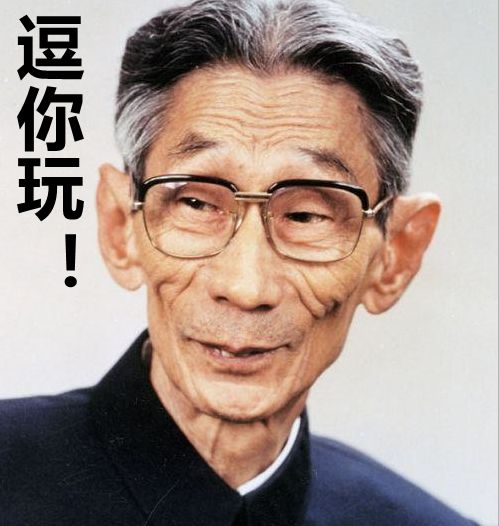天津人未解之謎:馬三立的《逗你玩》中,是誰偷了小虎家的被臥面子?
摘要:這段透露出幾個重要信息,小虎他爸他媽都是賣魚的,而兩年前他家東西被偷時,小虎李文林他爸,老李,應該是正在市上賣魚,也許是因爲生意剛起步,李大嫂那會還是全職主婦,兩年之後,買賣越做越大,小虎也到了上學的年紀,不用家大人在家看着了,老李兩口子這纔開始一起幹買賣。小虎的嬰兒時期,有一天他家鄰居張二伯在菜市場買了4斤魚,非得冒充是釣來的,被小虎賣魚的爸爸當場揭穿,給二伯來了個大窩脖兒,雖然李嬸盡力打圓場,但因爲張二伯這人太渾,仍舊與李家結下了樑子。
《逗你玩》是馬三立先生的一段單口小段,全長不過6分鐘,臺詞不過900個字,但效果極佳,至今“逗你玩”這個梗仍被天津的老少爺們們津津樂道。
平心而論,《逗你玩》這種作品,絕非是一般人能拿的動的,它是馬三立先生表演功底及超好觀衆緣的體現,段子雖小,卻充分地展現了馬氏相聲的風格與魅力。
但一直以來,就如同馬志明《糾紛》中“王德成在哪壓了丁文元的腳”這個問題一樣,許多觀衆也被《逗你玩》中的一個問題困擾着:
小虎家的褲子、褂子和被臥面子
到底是被哪個王八蛋偷走的?
這個問題,遠比《糾紛》之謎複雜的多,今兒個咱就撥開重重迷霧,在重溫馬三立先生一系列經典作品的同時,爭取解開這個謎團…
首先在“小虎本傳”《逗你玩》裏,馬三立先生就已經交待了很多信息:
1.
小偷過來了,奧,這好地方!
“幾歲了?”
小孩一瞧:“5歲…”
“叫嘛?”
“小虎兒!”
2.
街坊這老大娘
雖說老大娘
歲數不大三十多歲吧
三十多歲
大嫂子
咱們稱之大嫂子
從現有信息可以看出,小虎一家是馬三立的街坊,當時小虎他媽30多歲,就一個5歲的孩子小虎,那她結婚的年紀應該在二十大幾,大概其是屬於晚婚晚育,小虎很有可能是個獨生子。作爲家庭主婦的她,任勞任怨,帶孩子做飯洗衣服,樣樣拿得起來放得下。
那大嫂子爲嘛不讓爺們兒幫着看衣服呢?
爲嘛非要讓小虎這不懂事的孩子守在外邊,以至於讓小偷得逞呢?
OK,這就要搬出馬三立的第二段作品了:《考試》。
小虎兒這個名字,大夥一看就知道是個小名,那小虎的大名是什麼呢?這個答案在馬三立先生晚年的作品《考試》中有說明,小虎在去學校考試之前,他媽媽囑咐他:
“別害怕啊,老師問叫什麼名字,別說叫小虎啊!學名李文林,記着!”
等到老師問問題時,問小虎:
“幾歲?”
“七歲。”
好的,我們知道了,小虎姓李,大名叫李文林,而且這會已經七歲了,距離他家被臥面子被偷已經過去了2年。
再往後看,老師又接着問小虎:
“幾歲?”
“七歲。”
“去年幾歲?”
“……去年六歲。”
“上三年級幾歲?”
“九歲。”
“行啊!你爸爸是會計?”
(搖頭)“賣魚的…”
“哦,買賣人。你媽媽是學校老師?”
“也是賣魚的…”
“哦,個體戶。”
這段透露出幾個重要信息,小虎他爸他媽都是賣魚的,而兩年前他家東西被偷時,小虎李文林他爸,老李,應該是正在市上賣魚,也許是因爲生意剛起步,李大嫂那會還是全職主婦,兩年之後,買賣越做越大,小虎也到了上學的年紀,不用家大人在家看着了,老李兩口子這纔開始一起幹買賣。
而個體戶這個名詞,是80年代初改革開放後出現的,計劃生育政策,是1982年9月被定爲我國基本國策的。
這也正好再次印證了,小虎是個獨生子。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根據年代,大致判斷出李家丟失的被臥面子是什麼款式的,大概就是下面這樣的:
言歸正傳,老師一聽小虎家賣魚的,繼續問小虎:
“100斤魚,賣99斤,還剩多少?”
“還剩10斤。”
“聽明白了嗎?100斤魚,賣99斤,還剩多少?”
“還剩10斤。”
“剩的了那麼多嗎?”
“剩的了。要是我爸爸看攤兒,剩的還能多。”
這段話聽着可笑,可卻反映出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小虎他爹媽都是奸商,賣個魚還要玩兒稱。可李大嫂兩年前可是個賢妻良母,到底這兩年間這老孃們經歷了什麼,才讓她逐漸黑化呢?
OK,這又要搬出馬三爺的第三段相聲,《釣魚》了。
提到《釣魚》這個故事,多數人第一反應絕對是高英培、範振鈺二位的作品,其中“二他爸爸”的形象深入人心,但這個段子,應該是根據馬三立先生的“親身經歷”改編的。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馬三立、張慶森就曾講過這個故事,雖然沒有錄像,但卻有珍貴的錄音留存了下來。
在這段作品中,又是馬三立的一位街坊,滿嘴胡了天,七個不行乎,八個不在乎,非得吹牛說大話,說自己會釣魚。可他自己心裏知道自己幾斤幾兩,最後跑到魚市買了4斤魚,才鬧出一堆笑話。
鬧出了什麼笑話呢?相聲中也有交待:
釣魚大哥回到院裏,讓媳婦拿來大盆,把魚都倒進去了,誰知他的幾位街坊(也是馬三立的街坊)也過來了,頭一位立刻就發現了一個問題,說道:
“(這魚)都一邊大啊!”
按正常邏輯來講,對魚的質量這麼敏感的人,很有可能長期與魚打交道,我們完全可以推斷,這個人提出質疑的人,極有可能就是小虎李文林他爹!因爲他就是賣魚的!天天跟魚熬鰾!
如果說這樣還不足以證明,那麼後面的故事,則100%肯定了這種推測:
街坊那個大嬸,抱着孩子過來看看,也許是怕釣魚者面子掛不住,爲了防止發生衝突,打圓場道:
“(這魚)不少,合二斤多!”
這裏有兩個問題,大嬸懷裏抱着個孩子,而且還幫着剛纔提出質疑的大哥打圓場,那這個人,應該就是小虎他媽,而懷裏的孩子,就是小虎!而且這個人“打圓場”時賢惠的樣子也很符合小虎小時候,李嬸的性格特徵。
那麼釣魚的大哥是誰呢?
咱們還得打開馬三立的第四段作品——《練氣功》,再找找線索。
在《練氣功》,馬三立再一次提到了他的街坊,小虎。
這一次,小虎與張二伯狹路相逢:
打外邊來個小孩兒,這小孩兒手裏拿一根冰棍兒,剛要進衚衕,這張二伯過去:“小虎,拿的嘛?”
都怕他呀!
“二…二伯?”
“問你拿的嘛?拿的嘛?”
“冰…冰棍兒。”
“冰棍兒?嘛的?”
“奶油的。”
“倒黴孩子買奶油的幹嗎?小豆的呀,這倒黴孩子,這…好喫嗎?我嚐嚐?我嚐嚐?”
“你讓我嚐嚐!你讓我嘗不讓我嘗?你讓我嘗不讓我嘗?你不讓我嘗你別進衚衕兒,你進衚衕兒我把你踹出去啊!”
張二伯其人,大家都很瞭解,用馬三立的話說:
成天不上班,淨喫勞保,不知道他幹嘛地。這人混、糊里糊塗。
這個性格描述與釣魚大哥的形象特徵完全吻合!
那麼他的作案動機是什麼呢?
咱們好好捋一捋時間線:
話說在80年代初期,李嬸剛剛結婚,他爺們老李賣魚養家,成爲了第一批個體戶。之後又趕上國家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不久後生下了他的獨子,也就是小虎李文林。
小虎的嬰兒時期,有一天他家鄰居張二伯在菜市場買了4斤魚,非得冒充是釣來的,被小虎賣魚的爸爸當場揭穿,給二伯來了個大窩脖兒,雖然李嬸盡力打圓場,但因爲張二伯這人太渾,仍舊與李家結下了樑子。
正因如此,很有可能兩家從當時開始就不再互相走動了,而且當時小虎還是懷抱的娃娃,尚未懂事,也就導致了他對二伯不熟悉。
張二伯平時淨玩蔫壞損,時不時的找茬,使絆子。
小虎5歲那年,說機靈不機靈,說傻也不傻,因爲長期的疏遠,仍舊不太熟悉張二伯,二伯也正是利用小虎的這個弱點,哄騙他喊自己“逗你玩”,這才讓老李家損失了大褂一件,褲子一條,被臥面子一個。
還有一棵奶油冰棍……
作案動機找到了,就是因爲日常發生的口角,張二伯記仇,並且讓李嬸寒了心,心說自己好心好意的打圓盤,你還這樣,由此開始逐漸黑化 。
所以,真相大白!
偷小虎家被臥面子的犯罪分子就是張二伯!
參考資料:《馬三立街坊考》、頭條@津沽一頁書
天津人未解之謎:王德成究竟在哪壓了丁文元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