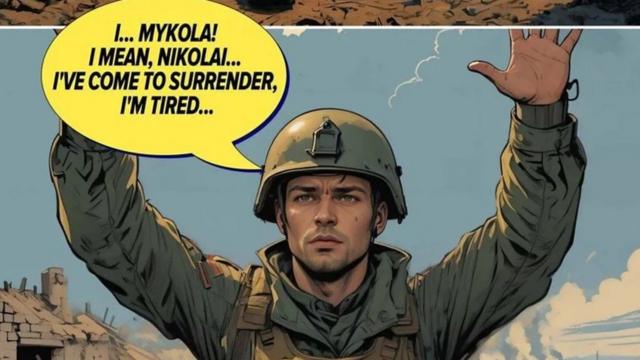苗懷明:父親——我研究古代小說的引路人
原標題:苗懷明:父親——我研究古代小說的引路人
最近幾年,不斷有記者或學生採訪,其中一個被反覆提及的問題就是:你是怎樣走上古代小說研究之路的?我的回答很簡單:從小就感興趣,如果沒有濃厚的興趣,自己是不可能堅持這麼多年的。
至於爲何感興趣,如果放在一年前,我會很樂意細說一番。但自從父親去世之後,這個話題一下變得非常沉重。因爲談及這個話題,就不能不談到他老人家。
2017年1月31日,父親病魔纏身,行動已很不便,一個月後就去世了。
一年前的今天,父親離開了我們。面對冷酷無情的病魔,我們兄妹幾個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父親在痛苦中無助地離去。
小時候生活在河南一個貧窮的小鄉村裏,相比村裏別的孩子,自己算是幸運的,因爲父親在外面讀過書。雖然從現在來看,那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專,但當時在村裏他已經是文憑最高的人了。
父親畢業後分配在湖北工作,在那裏待了將近二十年,一般情況下每年只回來兩次:一次是春節,一次是農忙的時候。每到臨近春節,幾乎全村的人都拿着紅紙到我家找父親寫春聯,這往往也是我感到最自豪的時候。村裏沒幾個人讀過書,更不用說寫毛筆字了。
此外,我還有一個村裏別的孩子無法享受的福利,那就是聽父親講故事,我對古代小說的最初印象,那就從父親那裏聽來的。
父親的文憑
父親雖然學的是測繪,但對古代文史一直有着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古代小說,爲此買了不少這方面的書籍。父親回家,我們兄妹幾個最爲開心的事情就是臨睡前聽他講故事。在父親所講的故事中,印象最爲深刻的是《西遊記》。
父親口述版的《西遊記》與原書有較大的出入,用他後來的話來說就是,書裏有些情節記不清了,就憑印象加上自己的虛構,要不就是把其他小說裏的情節搬過來,結果我們還是聽得津津有味的。除了《西遊記》,父親還講過其他小說,但印象都已經相當模糊了。
後來上學識字,父親就買書給我看,每次從外地回來,總要帶個一兩本,或者是連環畫,或者是書本。這對愛讀書的我來說,比過節日都高興。日積月累,竟然也攢了一箱子。其中不少書比如《西遊記》,我都看了好多遍,裏面的一些詩詞都能背出來。
父親爲《三國演義》所包書皮
再後來,到讀中學的時候,父親逐漸把他的一些藏書給了我,其中有《三國演義》、《西遊記》,還有《紅樓夢》、《說唐》等,這是我的第一批古代小說藏書。這些書都用廢紙包上書皮,這是父親愛護書籍的習慣。受父親的影響,我也養成了這個習慣。只是後來書買的太多了,包不勝包,就不再包了。
現在想來,如果當初不是父親給我講《西遊記》之類的古代小說故事,如果不是父親送給我這些古代小說作品,我對古代小說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大興趣,也許後來就不會走上研究之路。
筆者上大學期間與父親在八達嶺長城合影。
到北京上大學之後,我開始買書,數量很快就超過父親。其間,父親有兩次出差,趁便到學校看我。大學將要畢業那個學期,他到北京出差,當時正好有閒時間,看我的書放得比較亂,就幫我整理。於是我們一起動手,我收拾書籍,讀書名,念價格,他負責登記書目,很快就編出了一本藏書目錄。
父親爲筆者整理的藏書目錄。
這是我的第一本藏書目錄。後來我養成了買書後登記造冊的習慣,直到現在仍是如此,已經編有好幾本了。
我博士畢業後到南京工作,父親每次來,都住在我書房裏,有時間就看書。他最後一次來,是和母親一起,那是2014年,他們在南京住了半個月。我工作忙,經常早出晚歸,沒時間陪他們,都是讓他們自己打車出去逛,午飯也順便在外面喫。那時候父親身體還好,天天和母親出去逛,好在南京的名勝古蹟多的是,總是有地方可去。
父親1987年11月22日寫給筆者的書信。
每次從單位回來,推開院子的小門,就看到他們老兩口在燈光下各自捧着一本書,靜靜地坐在那裏認真閱讀。然後就問他們白天出去的情況,聊聊家常。當時感覺心裏很踏實,也很溫馨。
父親愛讀文學、歷史方面的書,我回家時常給他帶一些,當然都是那些比較通俗、學術性不太強的。
自然,父親最愛看的還是我寫的書。我每出新書,必定給父親帶回去一本。他是我最忠實的讀者,不管是學術性較強的戲曲、小說文獻學方面的書,還是較爲通俗的《夢斷靈山》、《風起紅樓》之類,他統統認真讀過一遍。有時還打電話過來,給我說說他的讀後感,或者告訴我發現了錯別字。
父親1981年買的《現代漢語小詞典》,筆者至今仍在使用。
有段時間,我研究民間說唱,不時向父母瞭解老家過去說書的情況。他們小時候都是聽說書長大的,所講的情況很有參考價值。後來我想在老家找一些民間藝人採訪,父親就忙着找親戚打聽。可惜這門技藝在農村已基本失傳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七八十歲的老藝人,人家身體不好,加上我也很忙,一直沒有采訪成,如今不知那位老藝人還在人世否。
我一直有個心願,那就是請父親爲我的書題寫書名,他也答應了,但一直沒有動筆。他是學測繪的,經常繪製地圖,寫圖名、地名,是認真練過字的,雖然參加過一些書法比賽,沒得過太好的名次,但在單位及親友間還是小有名氣的。他的身體一直很健康,總覺得再拖拖也沒問題,誰想到走得那麼突然。
父親喜歡在藏書的扉頁上題寫姓名、日期及購買地點,以表紀念。
早知道的話,就催着他寫了。他寫了一輩子毛筆字,如今家裏竟然沒有一幅他的字,這個遺憾是永遠無法彌補了。
好在他喜歡在自己的藏書上題寫姓名及購買時間、地點,以示紀念,有幾本書是用毛筆寫的,還算是可以看到他的字。
父親爲筆者整理的藏書目錄內頁。
與天下千千萬萬的父親相比,也許再普通不過,但在我的心裏,他是唯一的。父親不僅養育了我,還培養了我的讀書興趣,尤其是對古代小說的興趣,引我走上研究之路,這大概是他沒有想到的。他早年購買的那些古代小說作品如今都已成爲我的藏書,就由我來延續他的文學夢吧。
父親去世後,一直想寫篇文字紀念他老人家,但心緒煩亂,不知從何寫起,遲遲沒有動筆。轉眼已是他去世一週年的日子,老家的風俗很重視逝者的週年,母親幾次說希望我回去,但今天正好有三節課,沒法回去了,就將這篇不像樣子的小文獻給父親吧。
2016年國慶節期間,筆者回家,陪父親散步,此時他已患上絕症,但大家都還不知道。
父親生前經常給我說,你工作忙的話,就不用回來了,甚至春節的時候也這麼說。我知道他是心疼我,不讓我兩地奔波太勞累。週年的時候不能到墓前去,想必他能諒解自己的兒子。
父親生前最喜歡讀我寫的書,在他去世後的一年裏,我又出了兩本,應該都是他比較喜歡的,後面我還會再出不少書,但那個最忠實的讀者再也無法看到,更不用說題寫書名了。
如今我已成爲一名古代小說研究的專業人員,但那個給了我生命、引我走上古代小說研究之路的人卻永遠離開了。
父親收藏的《說唐》
人世間的遺憾註定是永遠無法彌補的,無論你如何後悔,寫到此處,悲從中來,詞不達意,就此打住。
2018年4月4日於簡樂齋,父親去世一週年之際
本文經作者授權獨家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