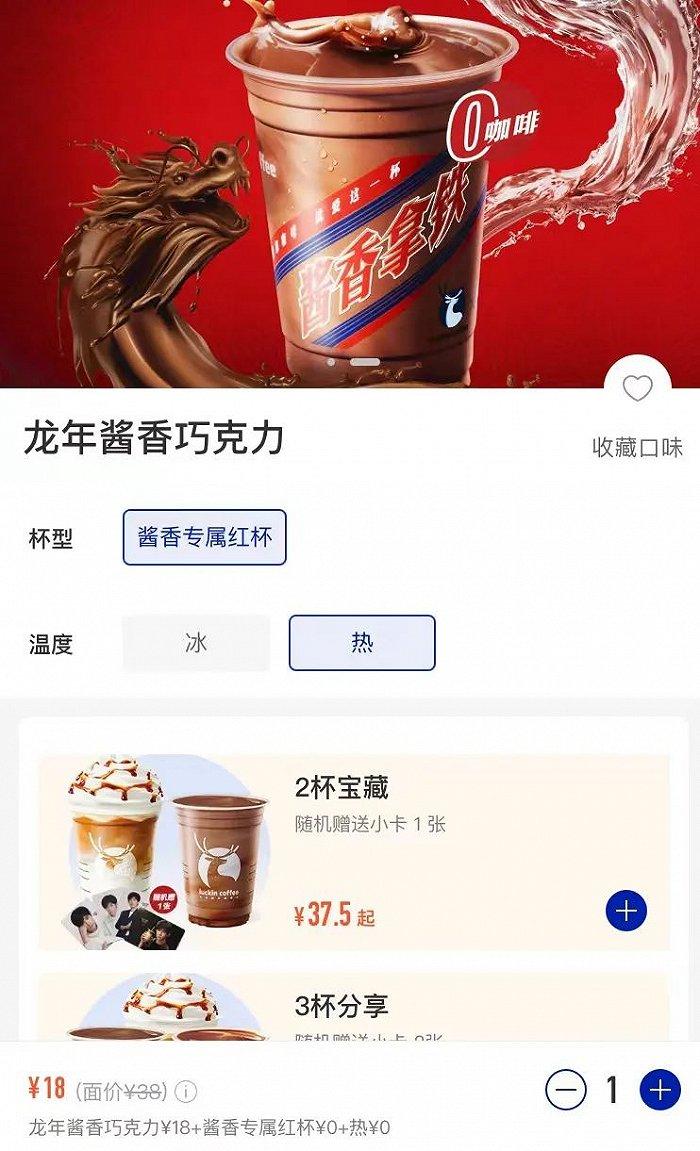爲什麼瑞幸可以適用於軟件範式
摘要:所以,瑞幸投入數以億計的資本做App、搭技術平臺,燒十數億做品牌、吸引用戶,與其說是在咖啡業務裏獲取規模優勢、完成數據驅動,不如說是在賭這些“一次性投入”所購買的數字基礎設施,可以持續地、大規模地、零邊際成本地使用。瑞幸憑藉融資在咖啡市場提供低價的價值主張,以此換取更大的消費規模及用戶數據。

歡迎關注“創事記”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文/Yancy B
來源:格竹集(ID:Mind7Hand)
“燒錢換流量”是過去10年最好的商業策略。Uber一共融資$150億,上市市值連續縮水後,依然還有$600億。
不過,當策略用於無法滿足以下條件的公司時,很可能導致一場災難。
1)指數增長。
2)邊際成本趨近於零,主營業務現金流爲正。
3)網絡效應。
ofo的問題就在於車輛需要重複購買,現金流頻頻告急。美團外賣儘管沒盈利,但餐廳抽傭可以覆蓋補貼和送餐成本,不需要融資補血。
在我們的傳統認知裏,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理想商業範式是軟件。前期技術研發成本高,需要風投資金啓動,不過這些基礎設施可視作固定成本,軟件的邊際使用成本趨近於零,一旦快速增長,投資者將獲取超額收益。
瑞幸也採用了“燒錢換流量”的策略,並於上週在納斯達克上市。作爲一家咖啡店,它能適用軟件這種商業範式,滿足以上三個條件嗎?如果適用,何以可能的原因是什麼,挑戰又是什麼?
讓我們先從瑞幸想要做的是一件什麼事開始:
瑞幸正在做什麼
虧本銷售實體產品是一件不可理解之事,瑞幸正在做的就是用低於成本的價格賣咖啡。顯然,它的初級目標不是利潤。
瑞幸憑藉融資在咖啡市場提供低價的價值主張,以此換取更大的消費規模及用戶數據。然後,用數據驅動營銷。比如,基於LBS投放的線上線下廣告。再如,動態定價。
瑞幸寫在菜單上的咖啡價格和傳統咖啡店不一樣。它不是需要實現的實在價碼,而是一個給消費者用於錨定的東西。動態定價的實質時,基於數據給出一個不固定(換言之有驚喜)的折扣,讓用戶認爲所購買的咖啡低於錨定價格。
更有效的營銷,更多消費者分攤店鋪租金、機器等固定成本,會讓咖啡的平均成本更低,進一步實現低價主張。

在另一圈的循環上升裏,數據驅動更有效率的運營。比如,通過開設低成本的外賣店獲取消費數據,完成pick-up店鋪的選址工作。再如,監控庫存數據,佔用更少的經營現金。
充沛的現金流可用於增加銷售品類,從垂直的咖啡業務轉爲橫向拓展。咖啡業務的已有用戶以及包括商店在內的基礎設施,將爲新品類的銷售獲取某種結構上的成本優勢。
這或許就是瑞幸寫在招股書裏的願景:Ourmissionistobepartofeveryone’severydaylife,startingwithcoffee。
不過,“tobe”不一定能成爲“be”,跨越鴻溝前,至少還需要搞定兩個向量:
增長空間與挑戰
第一個是指數級增長。
大陸的咖啡市場存在兩個事實:
1)好喝的咖啡是水攝入總量的重要來源。
人的身體成分主要是水,每天至少要喝2L才能補充消耗,也就是6杯飲品。去年,我們留給咖啡的份額是0.01杯,還不到一口。
這和地球其他地區不同,歐洲的日均飲用量大概是2杯,美國是1杯,日本是0.8杯,中國香港、臺灣分別是0.7杯,0.6杯。
一連串的數據都證明了咖啡作爲世界三大飲品的地位。大陸喝得少,已經不能用文化差異來解釋。剩下的唯一合理理由是:咖啡好喝,但我們的不好喝。
2)“好喝的咖啡”供應不足。
大陸商業化程度並不低,爲什麼會出現供應不足?
對此,我這個身在南方的重度麪食愛好者深有體會。如果說我在北方的消費選擇是“好喫的面”與“不好喫的面”,那麼南方的選擇就變成“好喫的米粉”與“不好喫的面”。最後,我放棄了麪食消費,轉投米粉。
市場調研一般只能看到米粉店的繁榮,忽略隱性需求“好喫的面”。於是,市場出現更多米粉店。即使城市商業化程度高,南北流動頻繁,市場的供需慣性也無法一朝改變。
大陸咖啡市場與南方面食本質一樣。
咖啡店爲降低材料成本,會一次批發大量烘培好的咖啡豆。烘培豆最佳衝制期是3-15天,最遲不能超過一個月。交易量少,烘培豆積壓,無法爲消費者提供“好喝的咖啡”這個基礎價值,只好轉向開發其他價值,比如“第三空間”。你要是去星巴克買咖啡豆,甚至還能買到半年前的。
當市場供應集中在“第三空間”時,消費認知停留在咖啡不好喝,購買咖啡的理由自然就變成買座位。我在知識星球分享過,星巴克這種我們所熟知的商業模式只是最近四十年的創新,更爲古老的模式是意大利街頭那種提供“好喝的咖啡”喝完即走的咖啡店。

所以,瑞幸想在大陸的咖啡市場獲取指數級增長是可能的,符合軟件範式的第一條件。
它的競爭對手不是星巴克,而是包括茶、奶茶、可可在內所有好喝的飲品。指數級增長的機會是:在我們每日的水攝入總量中,提高咖啡的佔比,從0.01杯咖啡剛沾溼嘴脣的狀態,到0.1杯喝一兩口,甚至再到完整的1杯,市場規模將從500億提升十倍百倍至萬億市場。
不過,“好喝的咖啡”供應不足這件事並不好解決。
現在瑞幸沒有自己的烘培廠,只有一個合作在建,大部分咖啡豆要從臺灣的友源進貨。如何經濟地、少量多次地購進咖啡豆,如何壓縮從倉庫到店鋪的分發時間,如何增加顧客數量快速消費庫存。從它現在的產品口味來看,還沒有一個明確答案。
瑞幸獲取指數級增長的真正挑戰是:在15天內把烘培豆衝製成一杯咖啡,和時間做一場運營賽跑。
扭轉融資補血
第二個向量是咖啡業務的經營現金流持續爲正。
一家咖啡店的營業成本有兩種:

一種是邊際成本,隨營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最理想的邊際成本是零,即軟件範式。一杯咖啡的邊際成本雖然不是零,但也足夠低。質量中等的烘培豆大概是80元/kg,衝制一杯咖啡需要15g,也就是1.2元,再添加點牛奶、糖,邊際成本差不多是3元,相比一杯動輒三十多的咖啡,並不算高。
所以,我們可以在瑞幸財報裏看到,儘管售價低,但收入完全可以覆蓋材料成本。這是瑞幸有機會適用軟件範式的基礎。
不過,當審視真實的經營環境時,總邊際成本不只是材料成本,還包括店鋪員工工資。瑞幸的運營效率顯然還不夠好,要麼補貼力度過高,要麼員工人效比太低,以至收入不足以覆蓋總邊際成本。
另一種是投資於基礎設施的固定成本。
對大多數公司而言,一旦開始經營,當期財務報表一定是虧損。在資產表裏,公司會用債務或股權融到的資本去購買某種經營所需的資產。在利潤表裏,只要資產收益低於資產成本,就會顯示虧損。
不過,不論服務1個人還是1000個人,固定成本是不變的,是某種“一次性投入”。只要收入高於邊際成本,在下期的現金流量表裏,經營現金流就會爲正,不需要融資補血。
所以,公司能否在將來某個時間點扭虧爲盈的問題實質是:主營業務的經營現金流能否持續爲正。這不僅與邊際成本有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固定成本的價格以及有效期。
不同類型的成本結構會有不同的商業模式。瑞幸區別於傳統咖啡店的是,它的固定成本有兩種:
一是實體基礎設施,即開店所支付的店鋪裝修費,機器購置費,以及租金。
這部分“一次性投入”資產的有效期並不長,最多五年就需要重新購買。瑞幸2018年租金總支出是1.4億,假設以全年1000家有效店鋪計,一家店鋪租金是14萬/年,五年70萬。2018年新開一家店所支付的裝修、機器的平均成本是30.5萬。
換言之,每五年需要重新投入100萬現金,即使每年賺20萬,算上貼現率都是一筆賠本生意,更何況瑞幸現在的收入還無法覆蓋邊際成本。所以,單看瑞幸這部分固定成本,無論如何不會適用於軟件範式,這也是它採用“燒錢換流量”策略飽受質疑的重要原因。
轉折點在於運營效率。星巴克一家店一年大概能賺100萬,如果瑞幸可以在規模的基礎上大幅提高員工人效比、降低邊際成本,即使只賺50萬,都比星巴克更有利可圖。畢竟瑞幸90%以上的店鋪是pick-up類,需要定期重複投資的固定成本低得多。
二是數字基礎設施,比如品牌,數據運營系統,自有App及其用戶。
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有效期遠比實體要長。所以,對軟件範式類公司而言,前期固定成本再高都沒關係,當使用的邊際成本爲零時,經營現金流持續爲正,扭虧爲盈是遲早的事。比如,谷歌研發搜索引擎的固定成本雖然高,但邊際使用成本卻趨近於零,可以持續地從用戶身上賺取廣告的純收益。
所以,瑞幸投入數以億計的資本做App、搭技術平臺,燒十數億做品牌、吸引用戶,與其說是在咖啡業務裏獲取規模優勢、完成數據驅動,不如說是在賭這些“一次性投入”所購買的數字基礎設施,可以持續地、大規模地、零邊際成本地使用。
這或許纔是它的終極目標:
打造成本領先的平臺
瑞幸將開設店鋪視作建立storenetwork的過程。如果說店鋪是節點,數字基礎設施是連接的網絡,那麼如何理解這套網絡,它所承載的業務是什麼,網絡效應又來自哪裏?
網絡效應分兩種。一種來自需求端,比如社交網絡,越多朋友加入對用戶價值越大。一種來自供應端,比如電商平臺,越多供應商加入對用戶價值越大。
瑞幸選擇的顯然是後一種,它現在有30%的收入來自非咖啡銷售,雖然還談不上bepartofeveryone’severydaylife,但橫向拓展銷售品類甚至業務的方向是清晰的。
從它在深圳的店鋪選址來看,它和星巴克一樣會在商場、寫字樓等地區重點佈局,不同之處在於店鋪更分散,還會在一些年輕人居住集中的公寓進行佈局。換言之,提供平臺的購買便利性。

瑞幸之所以將咖啡業務視作網絡起點,startingwithcoffee。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是,咖啡是一種非差異化的日常用品,配方、種類固定,只要烘培豆新鮮、操作得當,就不會難喝到哪去,有咖啡習慣的用戶需要經常飲用。
作爲非差異化、高頻次、高毛利的日用品,咖啡之於瑞幸storenetwork的意義,就如牙膏之於沃爾瑪超市,是一款可以不斷用低價吸引流量的口碑產品。一開始,牙膏的毛利普遍很高,沃爾瑪卻直接按成本標價,吸引用戶上門光顧,然後在其他預留了30%利潤的產品上賺錢。
瑞幸的“低價主張”幾乎和沃爾瑪的前半段操作如出一轍,不過遺憾的是,在上市前,瑞幸還沒來得及完成高效運營效率這項任務。
瑞幸和售賣差異化產品所需要構建的競爭力不同。比如,喜茶的任務更多是持續研發新品,用體驗提高客戶留存率。所以,在之前爬取喜茶數據的文章裏,我們會發現用戶評論會高頻出現“驚喜感”。
提供非差異化產品的平臺,核心競爭力是成本領先。只有更高的運營效率,才能更好地提供“低價主張”。只有先在垂直業務上完成邊際收入爲正的任務,纔有充沛資源去橫向拓展,在新增品類上獲取結構性的成本優勢。
更何況,在大陸咖啡市場,從賣座位的咖啡到成爲高頻日用品,還有一個“好喝的咖啡”的運營距離,瑞幸招股書裏按月下降的用戶留存率正在清晰地揭示這一事實。
換言之,即使瑞幸在絕大多數人所忽略的咖啡業務裏找到了實現軟件範式的機會,它同樣還是要從解決運營效率開始。
One More Thing
因爲登陸微信公衆號的頻率低,所以看到一些朋友的留言時已過時效,無法回覆了,抱歉。關於今年第二季度發起的DailyUpdate挑戰,我還在繼續執行,目前知識星球已更新至第8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