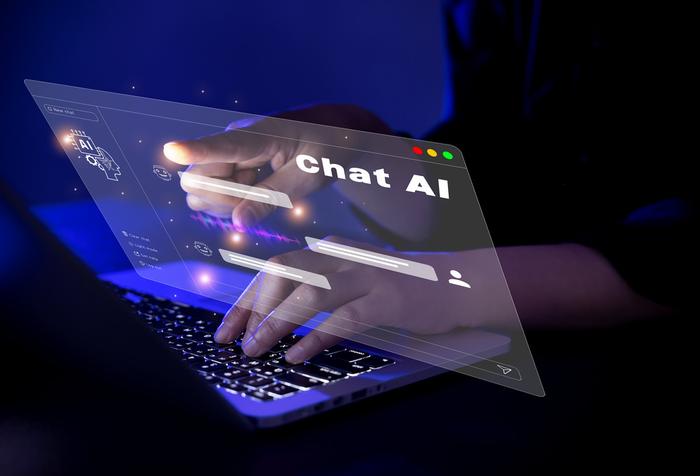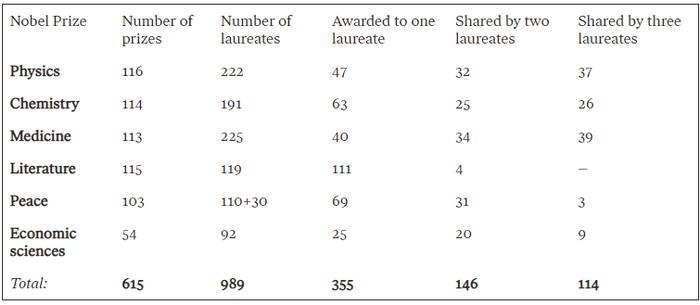詩魂 | 詩歌與教授詩歌 / 謝默斯·希尼 黃燦然 譯
原標題:詩魂 | 詩歌與教授詩歌 / 謝默斯·希尼 黃燦然 譯
一
我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用於教學,在一些非常不同的水平上。最早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在貝爾法斯特巴利墨菲區聖托馬斯中學,這個班的學生都是貧苦而不滿的青春期少年,他們之中很多人將在十年後變成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的現役成員。接着,我到一所教師培訓學院工作,也是在貝爾法斯特,並花時間試圖使學員教師們相信想象性文學作品和其他類型的創意活動的價值在教育過程中發揮的作用;然後到女皇大學講授詩歌,最近幾年來則成爲哈佛大學駐校詩人。在上述每一個地方,聽衆的文學意識,他們對詩歌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這個看法的接受程度,都千差萬別;我既見識過聖托馬斯貧苦學生的詰問,也見識過哈佛樓裏的頷首和老花眼鏡的閃光;在這兩個場合都看得出有種強烈願望,想確認藝術的價值和意義,儘管這種願望在貝爾法斯特是受壓抑的,在坎布里奇則完全是熱烈的。關鍵問題是被稱爲詩歌的這個備受推崇但難以定義的人類成果之可信性。即便是在巴利墨菲,那些因其社會和文化背景而被拒諸接觸韻文之門外,因而傾向視之爲某種不着邊際的愛好的少年們,也都很好奇,儘管有抗拒。有很多影響在起作用,使他們畏縮:同輩人的壓力、男校操場的流氣、工人階級對任何含有中產階級矯飾味道的東西的迴避。但是即便如此,詩歌的神祕還是引發他們的興趣,而在那些英語課期間,時不時總會有某種東西穩定下來併成爲焦點:在某個精神集中的時刻,他們專心領會的詞語竟然含有深意,並且以只有詩歌纔有的力量擊中他們。
英語課期間發生的另一件事,也值得回味。大約每週一次,並且幾乎總是出其不意地,學校校長會突然出現在教室門口。麥克拉弗蒂先生是一位真正傑出的短篇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不能自拔的教師。他原本應該整天待在校長辦公室裏處理各種事務,但是他卻穿着一身花呢西裝和鋥亮的拷花皮鞋巡行於各走廊,找機會打斷哪個人的話,以便參與進去,稍微過一過他如此懷念的教師癮。“說得好,同學們,”他會一邊激動地喊道,一邊匆匆越過教室地板來認領同學們,把他們當成他自己的學生。然後他會說“說得好,希尼先生!”以便解除我對他們的責備,或毋寧說,以便指派我在一次幾乎總是固定不變的雙人表演中充當他的配角。“希尼先生,”他會繼續說,“他們在你課堂上勤奮嗎?”“是的,麥克拉弗蒂先生,”我會回答。“你有教他們欣賞詩歌嗎?”“啊,是的,”我會回答,“我有的。”“你看到他們有任何提高嗎?”對此,正確的答案是:“當然看到。”接着便是高潮,他會把注意力刻意地從同學們身上轉到我身上,問道:“希尼先生,當你在報紙上看到橄欖球隊的照片,你總是能夠一眼就從球員臉上認出誰曾學習過詩歌,對嗎?”而我會盡職地、始終如一地回答:“對,麥克拉弗蒂先生,我確實知道。”於是麥克拉弗蒂會得意地點點頭,然後轉向班上:“你們看到了吧,同學們,好好學習,別到頭落得來跟其他人一樣,在某個街角瞎扯!說得好,希尼先生!”於是他會精力充沛地走開,其感染力和成問題就如同詩歌本身。
當我說“成問題”,無非是講,詩歌是不能像定理那樣證明的。麥克拉弗蒂之所以能夠提出詩歌可以明顯地使一個人變得更好而一走了之不受質疑,是因爲我隨時準備好跟他一唱一和。況且不管怎樣,班上的學生都知道整場演出是一個假面舞會。但恰恰是這個虛構、反諷和有異想天開的腳本的假面舞會,才能夠使我們抽離自身並進一步貼近我們自己。藝術的悖論在於,藝術全是人工的,它們全是編造的,然而它們使我們可以瞭解關於我們是誰、我們是什麼或我們可能是什麼的真相。事實上,麥克拉弗蒂先生關於詩歌人性化力量的誇張說法既誘人又滑稽,因爲這幅漫畫是根據西方兩千五百年美學理論和教育理論繪製的。從柏拉圖到現在,從雅典學院到你當地小學家長與老師見面,都一直存在着一場關於想象性寫作在課程大綱中的地位、意義和選擇的辯論,以及關於這樣的作品對於培養好公民的感受力和行爲到底是否有作用的辯論。事實上,麥克拉弗蒂的表演本身就是對這個人文主義傳統的其中一箇中心理唸的戲仿或誇張,這個理念就是,在善與美之間存在着根本性的聯繫,而研究美即是積極地促進美德。當然,這種對藝術價值的獨特捍衛,在二十世紀受到大屠殺這個歷史事實的災難性削弱:問題在於,如果某個最有教養的民族中的某些最有教養的人可以授權大規模殺人又在同一個晚上去聽一場莫扎特音樂會,那麼獻身於美和欣賞美又有什麼善可言呢?然而,如果說期望詩歌和音樂做太多事情是錯覺和危險的,那麼忽略它們所能做的,則是貶低和減損它們。
謝默斯·希尼詩集書影
它們所能做的,不僅得到麥克拉弗蒂先生的證明,而且得到莎士比亞的凱列班的證明。在《暴風雨》中,凱列班關於愛麗爾的音樂對他產生的作用的描述,可作爲對詩歌本身的作用的讚歌。你記得那些對白:凱列班告訴斯丹法諾和特林鴆羅別擔心那來自他們頭頂上的天空的神祕音樂,並說:
別害怕;這小島充滿喧囂,
聲音和甜蜜的曲調,使人愉悅,沒有害處。
有時候一千件彈撥的樂器
會在我耳邊奏響,有時候歌聲
如果我是在長睡之後醒來聽到
會使我又睡去。
“聲音和甜蜜的曲調,使人愉悅,沒有害處”:作爲對詩歌和整體文學的善的描述,這就夠了。體驗那些聲音,並不需要把凱列班變成另一種生物,也不需要該體驗對他的行爲發生持續的作用。文學或音樂的善,首先存在於它自身,而文學和音樂的首要原則,是威廉·華茲華斯在《抒情謠曲》的“序”中所稱的“那偉大而根本的快樂原則”,也就是語言本身引發我們說出“這對我有益”的那種快樂。
二
詩人從事的必要詩歌教學,常常源自他們生命中的危機時刻;他們就他們所承受或解決的問題提供的說法,首先以個人和迫切的方式表達出來,然後這些有關藝術或生活的特殊表達方式變成了熟悉的參照點,甚至有可能獲得治病救人的力量。
就拿濟慈來說吧,他在給弟弟喬治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把他對自己的詩歌命運的看法,簡化爲一個關於把才智培養成靈魂的寓言:需要一所學校,而那所學校就是痛苦世界。這份神聖文本意想不到地發端於濟慈本人一個迫切需要,就是需要使他那本質上是興高采烈的性情配合他覺得是可怖的環境。或拿奧斯普·曼德爾施塔姆來說吧,他有一個令人精神一爽的信念,認爲詩人是“一個偷空氣的人”,因此絕不是國家官方所要求的意義上的“工人”,他的工作只是飾帶製造者那種意義上的工作,也即製造一種設計,它是“空氣、孔眼和逃學”,或者是甜甜圈烘烤師傅,製造古怪的洞而不是有用的生麪糰。曼德爾施塔姆那不顧後果的卓越性,乃是詩歌的自由的表白,超過任何可能在講臺上說的東西;並且,當然,它要付出相應的高昂代價,那不是一般的學院正統觀念拿得出來的。
儘管如此,如果要在教育系統內實施詩教,那麼這種詩教偶爾由詩人自己來實施,也就講得通了;只要他們承認他們作爲教育家的職能與他們作爲藝術家的職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別,那就沒有害處,甚至可能有很多好的東西從他們的參與中流出。而不管怎樣,如同在教育領域裏任何別的東西一樣,成功與否更多地取決於詩人教授的性格和他或她使學生參與進去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任何先天的才能或後天的知慧。教學既是神祕性的,又是技術性的,教學者的氣質、其才智的出衆或其一般的可信性,既與詩人教授的影響有關,也與其詩歌本身的信譽程度和固有價值有關。
詩人的一大優勢,是這樣一個事實:他或她很可能擁有信得過的個人語言——顯然,我不是指色彩繽紛的“詩意”的語言,而指的是在專業用語與個人用語之間不應該有差距:相當於詩人在酒吧角落對一首剛剛發表於《愛爾蘭時報》上的詩的缺陷或優長評頭品足時的用語,也是他在教室對學生講話的用語。一般來說,既要對作品的技術層面予以專業關注,又要結合一種更務實的承認,承認詩歌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及結合一種期待,期待一位詩人或一首詩應體現一定程度的機鋒和常識。此外,與一般可能有的假設相反,詩人很可能對任性的東西、焦點模糊的“感覺”和誇誇其談的雄辯一點也不買賬;他們知道自大和膨脹和自欺的危險,這是因爲他們的本職很容易有這些傾向,因此,他們已預先做好準備,隨時檢視自己包括別人的作品中的這些缺點。
詩人還較有可能不知不覺地表露詩歌傳統活生生的本質和“正典”的通俗性生命。如今,本科生都被過早地告知,要把詩歌遺產視爲一種壓迫性的強加,以及要懷疑它在性別領域潛存的歧視,懷疑它在階級領域和權力領域的特權化和邊緣化。所有這些懷疑如果是由一個正在接受如此去懷疑的教育的人來行使,那是很有益的,但這種懷疑如果是在沒有任何文化根基的人身上引發,那將對文化記憶造成可悲的破壞。另一方面,當一位詩人憑記憶或出於偏見或出於純粹的欣賞而引用“正典”,則“正典”就會以一種富有教育意義的方式顯露出來。簡單地說,一個出於專業上的愛而引經據典的悶蛋,要比一個出於理論而進行顛覆的“摘下面具”的悶蛋更有利於社會生活。
謝默斯·希尼日記手稿
然而,不混淆藝術性與教育性,乃是對作爲教授的詩人的主要告誡。這種混淆導致的最惡劣後果,乃是詩人在與學生相處時所表現的傲慢而荒唐可笑的行爲:詩人以爲詩藝的卓絕可使其在課室裏不顧禮節和不加準備,這不僅是對人性的冒犯也是對專業必要性的冒犯。我看過不少有才能的男男女女,他們是如此包裹在“我”的閃亮盔甲裏,以致完全無法跟面前的聽衆溝通。這可能只是一個純粹的白癡狀態和浪費機會的個案,但是當詩人教授的地位賦予他們的權威被他們用於壓制那些有潛力者和被用於摧毀新手讀者或新手作者的信心,那就令人痛心了。無論學生是什麼年齡,也無論是什麼環境——小學課室或研究生詩歌研討班——施教者與受教者之間的契約要求施教者身上那個獲授權的人維持某種平等關係和提供某種保護。我們都被正確地警告在這些環境下要小心各種形式的性騷擾,但可能也存在着一種本職騷擾,也即學生的希望和抱負受到難以想象的攻擊。當然,對學生的才能給予公平而誠實的評估——不管是好是壞——是必須傳達出來的,但傳達必須帶着尊敬和必須小心學生的情緒基礎。
(刊於《詩書畫》2014年第2期[總第12期]。註腳見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