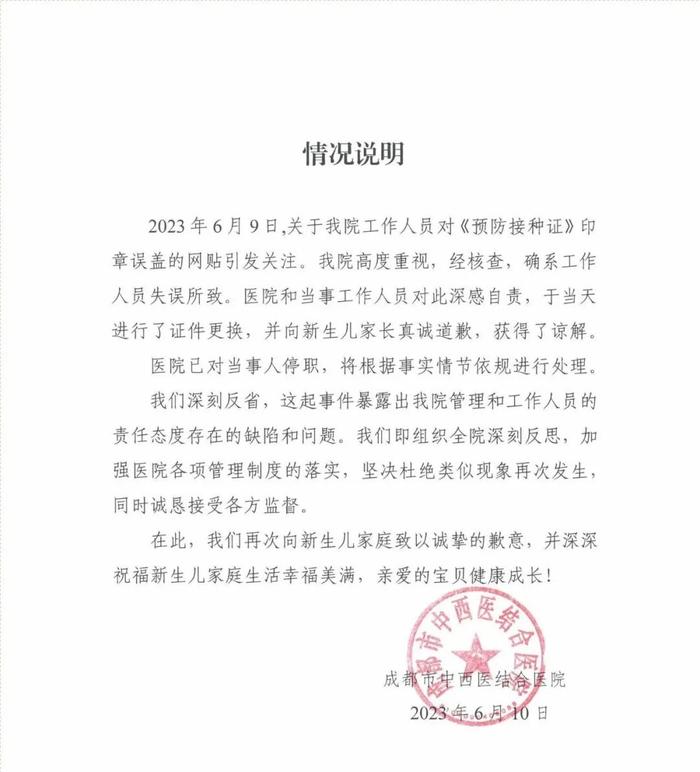揭祕上古奇獸——九尾狐的傳說
摘要:據東漢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記載,大禹來到塗山--據考在今河南嵩縣,遇見一隻九尾白狐,並聽見塗山人唱歌,說“綏綏白狐,龐龐九尾”,如果你在這裏“成家成室”,就會子孫昌盛,於是大禹便娶了塗山氏的女孩子,叫做女嬌。這個人獸婚配神話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意義,乃是塗山氏是一個以九尾狐爲圖騰物的部族,九尾白狐被塗山氏當作自己的祖先。
九尾狐,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奇獸。古典傳說中,九尾狐乃四腳怪獸,通體上下長有火紅色的絨毛。善變化,蠱惑。性喜喫人,常用其嬰兒哭泣聲引人來探也。九尾狐在仙界是極稀罕的種族,很少過羣居生活,喜好隱蔽于山谷,一般分散在仙界各層,許多人終其一生甚至連妖狐的面也未曾見着。
盛傳妖狐具絕世之容姿,蓋世之智能,而妖狐的皮毛更是珍品中的極品,其中享譽最高的又屬九尾狐狸。只出沒於高山嚴寒地帶,一般小妖狐誕下一百年後既可化爲人形,無一不是絕貌傾城。九尾狐的皮毛爲淡若無色的淡白,眼瞳爲血的深紅,銀白色的九尾狐,皮毛如月華般清濯明淨的銀色,皎潔出塵。當狐狸擁有九條尾巴之後,就會有不死之身。
九尾狐出沒時有一個特徵,是會有沙沙聲,像是雞毛撣子擦過紫檀木桌面的聲音。因爲狐狸練成人形,最難修煉的,就是狐狸尾巴!尾巴有九條,既顯示了它狐媚的深厚功底,又暗示了它向人類藉助陽氣時的困難,因爲尾巴的繁複很容易使其露出馬腳。因此,其尾巴的構造恰恰符合古文化的辯證法:能力越高,麻煩就越多。漢時石刻像及磚畫中,常有九尾狐與白兔,蟾蜍、三足烏之屬並刻於西王母座旁,以示禎祥。
在上古有一個夏族大禹娶塗山族女子的神話,此中牽涉一個神祕物象,便是九尾白狐。據東漢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記載,大禹來到塗山--據考在今河南嵩縣,遇見一隻九尾白狐,並聽見塗山人唱歌,說“綏綏白狐,龐龐九尾”,如果你在這裏“成家成室”,就會子孫昌盛,於是大禹便娶了塗山氏的女孩子,叫做女嬌。由於神話記載得很晚,明顯加進後世思想文化觀念,如果恢復其本來面貌,便是大禹在塗山娶了九尾白狐做妻子。這個人獸婚配神話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意義,乃是塗山氏是一個以九尾狐爲圖騰物的部族,九尾白狐被塗山氏當作自己的祖先。由於九尾狐有這麼一件很風光的事情,所以後代的狐狸精們總喜歡驕傲地說自己是塗山後裔,炫耀血統的高貴。
上古神話演義中還有一段: 過了黑齒國,就到青丘國。那些人民食五穀,衣絲帛,大概與中國無異。但發現一種異獸,是九尾之狐。據土人說,這狐出現,是太平之瑞,王者之恩德及於禽獸,則九尾狐現,從前曾經現過,後來有幾十年不現了。現又復出現,想見中國有聖人,天下將太平之兆。文命聽了,想起塗山佳偶,不禁動離家之嘆。然而公事爲重,不能顧私,好在大功之成已在指顧間,心下乃覺稍慰。在此九尾狐的出世被稱爲祥瑞之兆。
漢代盛行符命思想,於是本爲圖騰神的九尾狐也被符命化了,成爲祥瑞的神祕象徵符號。
在中國狐文化史上,狐的一件倒黴事也是發生在漢代,就是被妖精化,在“物老爲怪”的思想作用之下,普普通通隨處可見的狐狸不比龍鳳麒麟,是很難保住它的神聖地位的。儘管在唐代流行狐神、天狐崇拜,但那已經是妖神了,既然是妖神就不像正神那般正經,不免胡作非爲,就像沒成正果之前的孫猴子一樣。不過在唐代人的觀念裏,最厲害的天狐——九尾天狐卻仍保持着正派風範。可惜九尾狐的光榮史終究是要結束的,只不過因爲它神通最大比別的狐結束得晚一些,也正因爲它神通最大,當它被妖精化後也就成爲妖性最大的狐狸精了。
九尾狐最晚在北宋初期已被妖化了。田況《儒林公議》說宋真宗時陳彭年爲人奸猾,善於“媚惑”皇帝,所以“時人目爲九尾狐”,可見九尾狐在人們心目中已經不是什麼瑞狐、神狐,變成壞東西。而也在這個時期,中國遠古史上一個著名女人被說成是九尾狐,而且傳到日本,這便是商紂王的妃子妲己。其實唐代白居易在《古冢狐》中已經把“能喪人家覆人國”的妲己和周幽王的妃子褒姒比作狐妖,當九尾狐變成妖精時,妲己這個用美色把紂王迷惑得亡國喪身的王妃被說成是九尾狐精,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妲己成了九尾狐狸精,真可說是超級狐妖的完美結合。在小說中的描寫,則是由元代講史話本《武王伐紂書》開了頭,再由明代長篇章回小說《封神演義》廣而大之。
在《武王伐紂書》中,吸盡妲己魂魄元氣骨髓而借其空皮囊化形爲妲己的是隻“九尾金毛狐子”。妲己的結局是在武王克殷後被姜太公用降妖鏡逼住現出原形,然後把她裝進袋子用木碓搗死。之所以費了這麼多周折,原來是因爲行刑的劊子手讓她那“千妖百媚妖眼”撩撥得下不了手。
從九尾狐塗山女到九尾狐妲己,九尾狐的神聖和光榮徹底喪失了,九尾狐成爲最淫最媚最壞的女人的象徵。《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大老婆吳月娘罵小老婆潘金蓮是“九條尾的狐狸精”時,就是十分刻毒的咒罵。
九尾狐,最早是出現在《山海經》。“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山海經·南山經》),“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山海經·海外東經》。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是一個亦正亦邪的形象(按照正規說法,狐,狸是兩種動物,只是人們叫習慣了,統稱狐狸,而只有狐有仙氣,狸似乎只是俗物)。
《魏書·志第十八·靈徵八下》當中記載道,在各地現身的異獸裏,狐狸佔據了很大篇幅,這是某種瑞祥的徵象麼?似乎有些讓人不解。在白狐、黑狐、五色狗的交錯身影裏,僅從“肅宗正光二年三月”開始,計有:“南青州獻白狐二;三年六月,平陽郡獻白狐;八月,光州獻九尾狐;四年五月,平陽郡獻白狐;孝靜天平四年四月,西兗州獻白狐;七月,光州獻九尾狐”等等記載。到了元象元年四月以後,九尾狐好似集體行動一樣,突然密集地從人們的視線裏穿行:“光州獻九尾狐;二年二月,光州獻九尾狐;興和三年五月,司州獻九尾狐。”這麼多“獻寶”的案例,動機不外乎是以此來佐證皇恩浩蕩並獲得宮廷的賞賜,九尾狐不幸再一次成爲了體制的晴雨表。
對此,還是北周皇帝睿智一些。 《北史·周本紀下第十》記載道: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州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令焚之。
按照正史的深意,這一個案進一步反映了皇帝的實事求是作風。只是,焚燒之後的九尾狐,屍骨不存,但媚術已然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