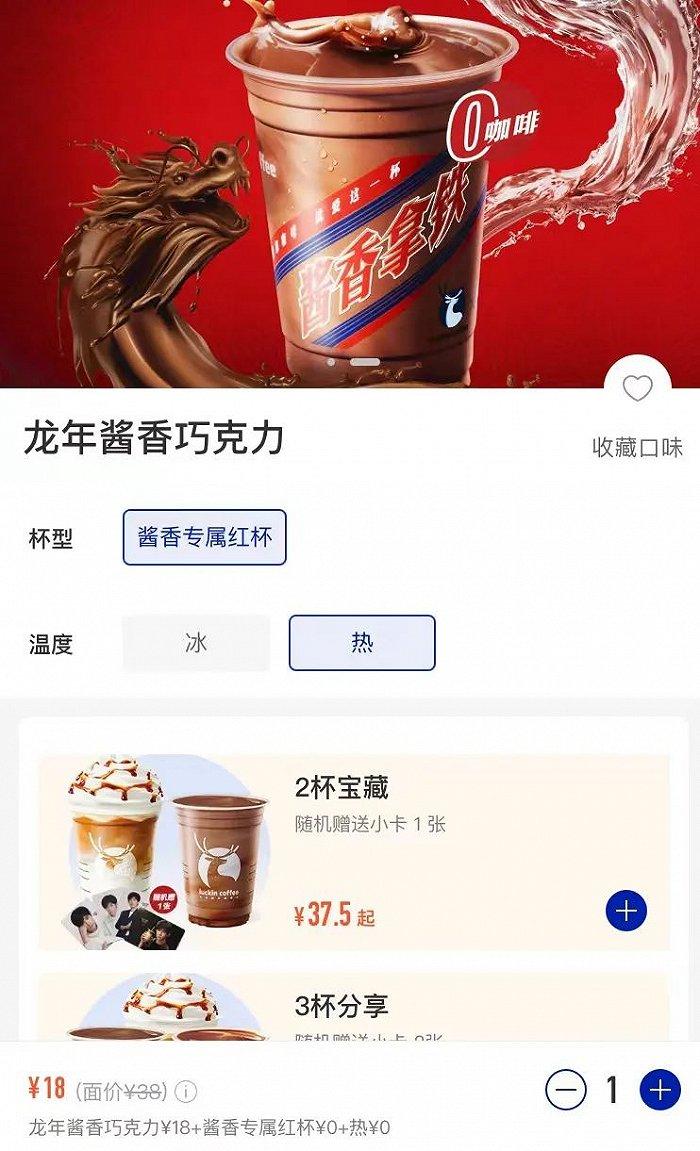其實人生有很多事,是隻開花不結果的
約老友坐。
一見面,居然來了一發哲學式問題:活着特麼的有什麼意思?
這叫我特麼的怎麼回答呢?
尋常人,都不會這麼“矯情”。會這麼“作”的,往往都是出了些“毛病”的人。
於是問:出事了?
還真問着了。這哥們的感情和生意均出了問題,一個已破裂,一個已破財。正處於解救而不得的狀態。於是惴惴然外加惶惶然。出口便曰:活着真沒意思。
我尊重這種情緒,也尊重類似的思考,畢竟,每一個人,都會或早或晚地,遇見這種困惑。
不過,近些年,已經換了態度,對待這種問題。
在伊薩克·迪內森的散文長卷《走出非洲》裏邊,有一個非常動人的細節:
在非洲種植咖啡樹的時候,一不留神,咖啡樹的主根會被折斷。
主根一旦被折斷,主根的截面上會長出很多鬚根。
從此,這顆樹再不會再結咖啡豆,但卻會比其他的咖啡樹,開得多出幾倍的花朵。
作者在後邊跟了一句話:這些鬚根,就是那棵咖啡樹的夢。
如果你是非文青,我想你會更容易接受另外一個譬喻:這些鬚根,讓咖啡更美麗。
人生有許多事情,也是隻開花不結果的。
比如,一些努力會有去無回,一些深情會如竹籃打水。甚至整個人生,都不會有一個確鑿而篤定的結局。
有一個小說,講的是一個作家,一直在寫故事。
文筆極佳,洞察力與想象力卓絕,因而紅極一時。
著作等身的時候,他覺得,人間浮事,俱已成書。若有疏漏,均屬意外。如此自信自滿,卻無人覺得過分囂張。
但忽然有一天,他發現,自己也是一個故事。
他成爲別人口中的故事,江湖流傳的故事,別人筆下的故事,甚至,命運虛構出來的故事。
寫到這裏,幾近神祕主義了。
但有一點,卻是確鑿的。
所有人,都只是一段時間,從塵世路過。
你遇上不同的愛、流言、破壞、榮光、離散與悲傷……繼而,成爲一段叫做“我”的情節。

有一年在旅途,遇見一個多年在路上的行者。
那時候,她剛從戰火紛飛的中東回來,無意中遇上,聊了許多務虛的話題。
她說:
死盯着生命的虛無,並因此放棄進取,其實是幼稚的。
真正的智者,是明知虛無,卻像開荒一樣,在生命的荒野上建設意義。
這與蘇格拉底不謀而合——“在死亡的門前,我們要思量的不是生命的虛空,而是它的重要性。”
“那麼,愛呢?”
“也是一樣的。大多數感情,都註定了挫敗、瑣碎、庸常、一地雞毛。但是,堅信並付出,就是愛的證明。”
忽然就諒解了一些往事。
是的,生命一如斷了主根的咖啡樹,無來無去,無着無落,慌張地向空氣裏,伸出無數鬚根,想建設,想聯結,想起高樓,想宴賓客……
此舉貌似徒然,但是,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即便沒有果實,這種欣然與生機,這種希望與相信,已經告慰了全部的虛空。
昨天,和母親聊天,談到死亡。
她很豁達:都是要死的,所以更應該珍惜,好好活一天是一天。
我聽了又欣慰又佩服,這麼樸素的話語,那麼本真的認知,卻最接近存在主義的內核。
是的,過程。
只剩了過程。
對付荒誕與虛無的辦法只剩它了。史鐵生說。
當你實現着、欣賞着、飽嘗着過程的精彩,你便把虛空送上了虛空。
當夢想使你迷醉,距離就成了歡樂;
當追求使你充實,得與失,成與敗,都是伴奏;
生命從不以成功,證明它的價值。而以美,以抗爭,以驕傲,自證其存在。一如西西弗斯,哪怕置身於荒誕的命運,仍然可以在失敗的戰役中,向自己的尊嚴表示敬意。
因此,加繆說:他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