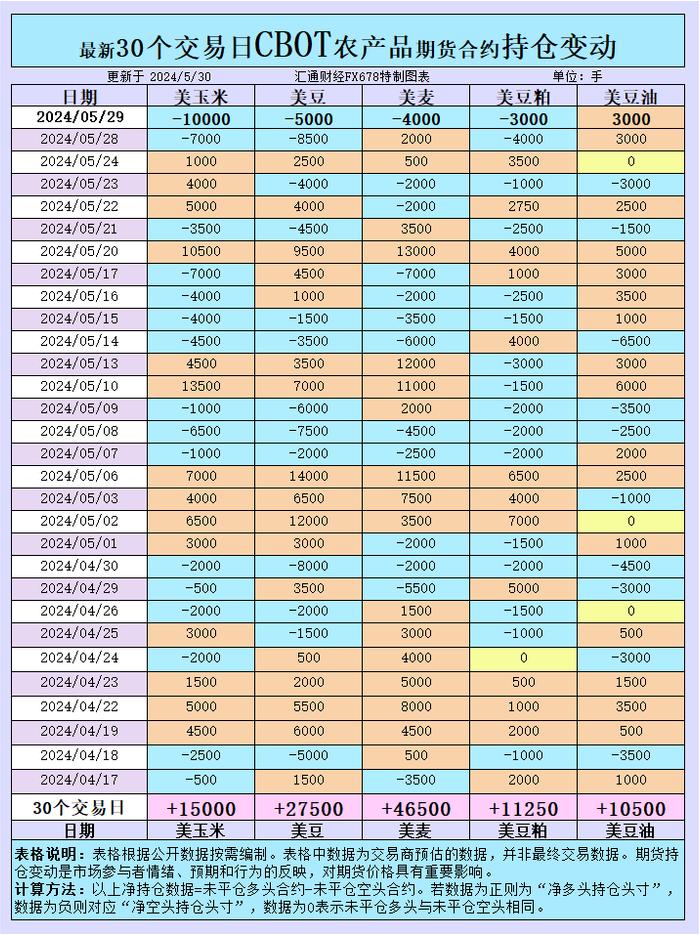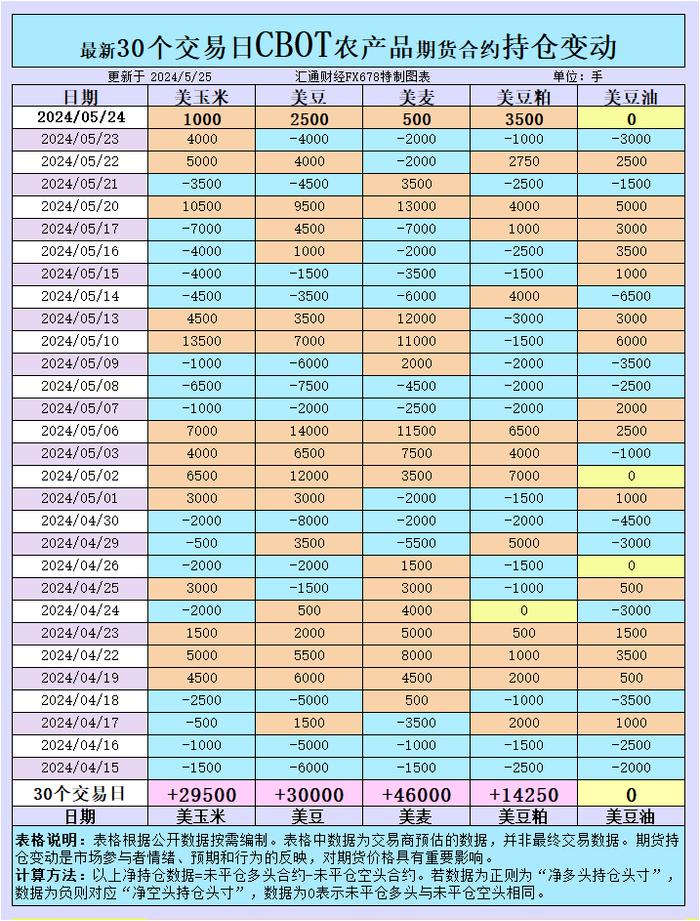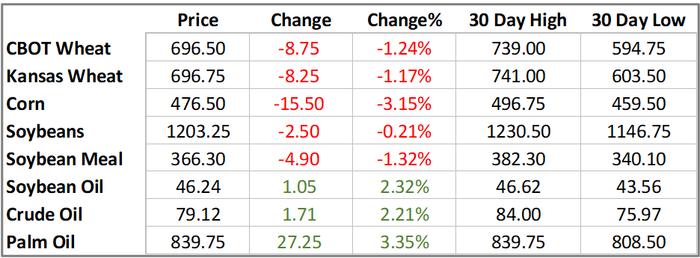一粒小麥,在他眼裏就是整個世界的重量
摘要:靠着“把育種當藝術”的精神,張懷剛把小種子做成了大學問——他發表論文110篇,參與編著6部,授權專利2項,標準4項,作爲主要完成人榮獲省部級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1項、三等獎1項,主持或參與培育的高產優質小麥品種多達12個,並在青海、新疆和甘肅推廣應用,產生了較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該所張懷剛研究員當年深受“高原338”的影響,從選擇農學專業學習,到進入西北高原所從事小麥育種研究,一路走來剛好40年。
文章來源:科學大院
在青海,有一項全國紀錄很少被外地人瞭解。1978年,青海省都蘭縣香日德鎮春小麥種植創下全國畝產1006.65公斤的紀錄。這個紀錄背後有一個享譽全國的小麥品種,叫“高原338”。而培育“高原338”的研究機構,就是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西北高原所”)。
該所張懷剛研究員當年深受“高原338”的影響,從選擇農學專業學習,到進入西北高原所從事小麥育種研究,一路走來剛好40年。張懷剛非常自豪地說,“我在小麥育種行業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征程”。

張懷剛研究員(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從農村來,奔農業去
張懷剛有很多社會身份,但是,他更願意稱呼自己是一個“搞農業的人”。他說:“我過去是農村娃,後來又搞了幾十年的農業研究。”
張懷剛出生於四川省廣安市的一個普通農村家庭,家裏祖祖輩輩都是農民。1978年,正值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年僅16歲的張懷剛不知不覺間站在了歷史和時代的拐點上。
當時,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幾乎不知道高考爲何物。面對專業選擇,張懷剛無從參考,只是因爲長期在農村生活,自認爲對農業很熟悉,加之聽說國家對農業院校考生有不少“優惠政策”,他就選擇了農學專業,並順利考上離老家不遠的西南農學院(現西南大學),在農學系學習作物生產與育種知識。他入校後才知道,當時在育種界已經聲名鵲起、後來被譽爲“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也出自這所學校的農學系。
大學四年一晃而過,在“統包統分”的時代,年僅20歲的張懷剛卻爲畢業去向犯了愁。當時,有三個不錯的選擇擺在他面前:一是留校任教當老師;二是去農技站做技術員;三是去研究所搞育種研究。

張懷剛博士畢業答辯(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張懷剛說,“當時也綜合比較過,但還是覺得育種研究更有社會意義,也符合自己的性格”。儘管主管畢業分配工作的老師再三勸他,搞育種很艱苦,但張懷剛還是毅然決定從事育種工作。他說,自己的想法很簡單,一來自己“從小在農村長大,最不怕喫苦”,二來“和一條新聞有關”,“當時,西北高原所培育的小麥品種‘高原338’突破了畝產1000公斤的大關”。這對經歷過糧食稀缺年代的張懷剛來說,無疑是一條振奮人心的“大新聞”。正是這條新聞,讓張懷剛對小麥育種一直“心懷大志”,也對西北高原所一直“心存好感”。
所以,他很樂意第一次“出遠門”,前往上千公里之外的青海西寧工作。
“來之後發現跟自己想的還是有點兒不一樣”,張懷剛回憶說。剛開始,生活上很不習慣:一是海拔高,冬天冷;二是麪食多,稻米少;三是離家遠,思鄉切。張懷剛還記得,當時按月供應伙食,每人每月三十斤糧食,其中大米供應只有三斤。由於大米緊缺,食堂每天早上只能供應稀飯。“那個稀飯是用頭一天的剩飯加工的,其實就是稀溜溜的白開水泡飯,根本不頂飽”。這對成長於南方的張懷剛來說,確實“有點兒難過”。
不過,張懷剛很快就適應了生活上的那些困難,他從最基礎的考種(一種考察種子品種特性的方法,一般考察項目有株高、芒長、穗長、千粒重等)做起,逐漸開啓自己的育種研究之路。
出一趟差 幹了件大事
1982年9月,進所才一個月的張懷剛被領導安排了一份美差:去福建漳州進行小麥加代繁殖。福建漳州是著名的“魚米花果之鄉”,對張懷剛來說,能去氣候宜人的南方,尤其是能喫上白米飯,“比什麼都開心”。
這也是張懷剛第二次“出遠門”。可是,到了漳州,他傻眼了。儘管過去在農村種過田,在學校也跟着老師瞭解過一些育種知識,但是,真要自己下地種,卻突然沒了主意。
身邊沒有老師,也沒有同事,更沒有現在發達的通信條件能隨時諮詢,而且當時帶了很多不同的小麥育種材料,“眼看國慶節過完了,再不種就錯過了好時辰”,張懷剛只好硬着頭皮播種。
那是他入職之初遇到的“最大挑戰”,“種子都是研究人員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有些種子已經培育了許多年,如果被我‘種壞了’,是多大的損失啊!”張懷剛憂慮的幾天睡不好覺。
沒有老師就自己學,沒有幫手就自己幹。張懷剛將種子全部搬出來,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登記造冊,然後對着記錄本將種子一行行排列整齊,最後來到整好的地裏,根據種子類型逐一點播……就這樣,他幾乎無師自通,把種子全都播種下去了。

1999年在國際小麥玉米研究中心訪問(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然而,種子播下去了,卻遲遲不出苗。這可把張懷剛嚇壞了。下地一看,原來是秋天雨水少,地裏十分缺水。當地又是沙壤土,張懷剛擔心漫灌破壞土壤,會導致串苗,甚至直接破壞地裏的種子,就只好選擇一窩一勺地澆灌。水源地距離試驗田很遠,他就只能一遍遍擔水,一勺勺澆地。不知不覺,泥土沾滿了褲腿,汗水浸溼了衣衫。
就這樣,憑着年輕人的一股子硬勁兒,他讓地裏的麥子長出了苗,種活了。張懷剛開玩笑地說,“看到種子發芽的那一刻,就跟小時候喫到糖果一樣幸福甜蜜。”
次年三、四月,麥子成熟了。此時的漳州雨水很多,直接影響麥子收穫。在當地老鄉的幫助下,張懷剛組織了搶收——和播種時一樣,分類分批收割,然後打麥裝袋,並登記造冊。然而,雨季收割的麥子含水分量高,如果保存不當,就會發芽或黴變。爲了保住這些來之不易的種子,張懷剛突發奇想,發明了一個“種子晾曬機”。他在倉庫里弄了一臺風箱,調好控制溫度,將種子放入其中一顆顆風乾,“風乾後的種子,纔是最安全的種子”,張懷剛開心地說。
無意間,張懷剛這一趟“長差”卻幹了一件大事。
張懷剛說,“我種的這些種子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品種,叫‘高原602’,後來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高原602”是張懷剛的博士生指導老師陳集賢研究員前後歷時十餘年配製的雜交組合和精心選育的品種。張懷剛在漳州繁殖出充足的種子,爲後來擴大試驗示範,加快推廣應用奠定了基礎。據瞭解,該品種1975年開始培育,1982年定型,1987年由青海省審定通過,後被推廣至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黑龍江等地,累計種植2000萬畝,增產糧食5.88億公斤,增產效益8.81億元。1992年,“高原602”榮獲青海省科技進步一等獎;1996年,“高原602”又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這在春小麥育種領域是非常難得的成就!”張懷剛自豪地說。
育種是一門藝術
“育種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粒種子從早期培育到大面積應用推廣,有時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一輩子的時間”,張懷剛說,從事這項工作以後他才逐漸明白“育種是一門藝術”。
一粒種子,除了對產量有要求外,還有很多其它的要求,比如抗倒伏、耐旱抗寒、抗病蟲害、營養價值,以及品種適用性,等等。在張懷剛看來,“育種的藝術性,就是要在這諸多的要求中,精挑細選、分析培育新的品種”。
張懷剛介紹說,小麥株高不僅影響小麥的光合作用,也會影響小麥抗倒伏能力,以及對田間肥力的綜合利用。他們曾在西寧旁邊的平安縣試驗一個品種,基本可以將株高控制在80公分左右,“我們覺得這個品種很好,就拿到別的地方推廣試種,結果一試就倒了”。仔細研究才發現,兩塊地的肥力有很大差別,新推廣地塊的肥力明顯很足,以致麥苗瘋長,“隨便就竄到100多公分了”。

在模擬實驗室指導學生開展科學實驗(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張懷剛嚴肅地說,“這就給我們提了個醒,種子的培育是一個綜合系統,海拔、氣候、土壤、株高、營養及抗病蟲害等,需要綜合觀察、判斷”。爲了開展綜合研究,張懷剛在西寧及其周邊建了很多實驗點,有時還要長途跋涉到很遠的地方進行樣本採集。
張懷剛的學生、同事劉寶龍副研究員記得,每年六、七月份,種子快成熟的時候,張懷剛都會親自去地裏踏勘,“不管白天行政工作有多忙,他都會在下班後來到幾十裏外的試驗田觀察種苗,經常在那裏一待就是一兩個小時”。遇到週末,他會在實驗站住上兩天,把問題搞清楚了才又回到市裏繼續別的工作。就這樣春夏秋冬、寒來暑往,張懷剛“像養孩子一樣精心培育種子”。
有一年九月,張懷剛帶着劉寶龍等人外出採樣。他們從西寧出發,沿着青海湖到柴達木盆地,再繞道祁連、同德等地返回西寧,整個行程3000多公里,歷時十餘天。讓劉寶龍感動的是,張懷剛這一路,既當司機又當老師,還要當“保姆”,每天開車幾百公里,同時還爲學生講授知識、答疑解惑,並且負責學生的安全和喫住用度。“每天早上7點出發,下午6點以後才能回到駐地,晚飯後還要整理材料直到凌晨一兩點”。就這樣連軸轉了十餘天,張懷剛竟然比劉寶龍他們這些小夥子還要“精神、麻利得多”。
靠着“把育種當藝術”的精神,張懷剛把小種子做成了大學問——他發表論文110篇,參與編著6部,授權專利2項,標準4項,作爲主要完成人榮獲省部級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1項、三等獎1項,主持或參與培育的高產優質小麥品種多達12個,並在青海、新疆和甘肅推廣應用,產生了較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育種,創造美好生活
“育種,創造美好生活”,這是張懷剛重要的座右銘。
張懷剛說,“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要首先解決喫飯的問題”,所以老一代育種人始終以“增產”爲目標,“哪裏畝產多少斤,就像一個個大衛星,確實非常鼓舞人心”。他自己心心念的“高原338”之所以影響很大,就是因爲它創下了畝產1000公斤的紀錄。他參與選育和推廣的“高原602”,之所以能被國家科技進步獎承認,也主要是因爲它“增產顯著”。但是,隨着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育種人漸漸發現,產量只是一個方面,品質越發成爲更高的追求目標。
因此,不斷滿足老百姓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實際需要,是育種人責無旁貸的使命。

在小麥試驗地調研(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張懷剛舉例說,北方人愛喫麪,尤其愛喫拉條子,但是,拉條子對面筋的含量要求很高。早期一些小麥品種,儘管產量很高,但用它們加工製作的麪粉不僅粘牙,而且沒有勁道,不宜做拉條子。然而,他參與研製的“高原448”卻在無意間突破了這個問題。“最開始考慮北方缺水,希望研發節水的新品種”,等他們培育出“高原448”後卻發現,它的溼麪筋含量高達32%,“麪條評分”遠遠高於對照品種。“這就等於解決了老百姓‘拉拉條子’的現實需求”,張懷剛樂呵呵地說。
“口感、勁道是一種需求,營養價值則是更高的生活需求”,爲了滿足這些更高的需求,育種人還得不斷探索。
劉寶龍的博士論文《小麥品種高原115紫色籽粒中花青素合成調控機理研究》就屬於這一類新研究。他介紹說,“高原115”是一個紫色籽粒狀的新品小麥,這個品種含有人體所需的鉀、鈣、鎂、鋅、鐵、硒等微量元素,同時富含別的小麥品種所沒有的花青素,後者具有極高的抗突變、抗氧化等營養價值。他至今還記得張懷剛當時“勸”他做課題時說的話,“老百姓既要喫飽肚子,還要追求口感,但未來一定是追求營養價值,我們應好好研究!”
如今,張懷剛團隊不僅深入研究最尖端的分子育種技術,破解小麥育種的一些基礎難題;還深入三江源生態保護領域,研究青藏高原特有“青稞種”的生態價值,培育高產優質的飼用燕麥新品種和既能耐高寒、固水土,又能“食草兩用”的“小黑麥”品種,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恰好與改革開放40年相伴,張懷剛從一個普通農村娃,一步一步成長爲農業學科的帶頭人。回顧40年的生涯,張懷剛用兩句話總結自己的“初心”:一句談事業,他說,“科研總歸要立足於國家、地方和人民的需要”;一句談自己,他說,“一生與種子相伴,挺好。”
張懷剛
作物遺傳育種專家、博士生導師,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研究員;“青海省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主要研究小麥遺傳育種。現任中科院蘭州分院分黨組書記、副院長兼西北高原生物所黨委書記。歷任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農業研究室副主任、農業研究中心主任、副所長,西北高原所所長。他發表學術論文110篇,作爲副主編或主要編寫人出版著作4部(《中國北方春小麥》《小麥體細胞無性系與育種》《青海高原春小麥生理生態》《豐產抗旱春小麥高原602研究與應用》等)。在我國西北春麥區和青藏高原冬春麥區對春小麥高產機理、品質遺傳、體細胞無性系變異機理與利用進行了深入研究,爲春小麥高光效育種和品質改良提供了種質資源與理論依據;爲小麥體細胞無性系變異取得了確切的基因突變證據,併爲解釋無性系變異穩定快提供了基因水平上的證據;參與育成高產優質小麥新品種12個,育成品種在青海、新疆和甘肅推廣應用,產生了較好的經濟與社會效益;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1項(參與者),省級一等獎2項(第一、第五完成人)、三等獎1項(第四完成人),是青海省自然工程科學首批學科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