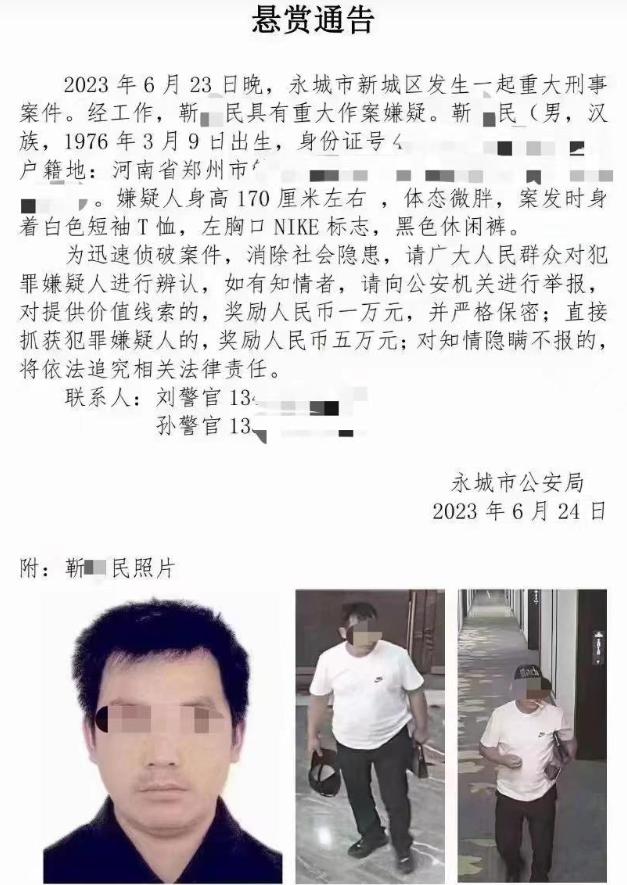鼻子插毛笔,江湖书画家横扫天下
原标题:鼻子插毛笔,江湖书画家横扫天下
(导读:江湖书画家不是靠笔而是靠嘴,一天不吹活不成;都是“大师”,胆子大、脸皮厚;一般来头很猛,寰球、世界,出口就标榜是谁谁关门弟子,他们随身带着各种作品润格、等级证书,甚至还有“国际ISO认证”。)
鼻子插毛笔
江湖书画家横扫天下
如今扔一顶“江湖画家”的帽子在大街上,99%的人都不会去捡。说谁是“江湖画家”,比说谁戴了“绿帽子”好听不了多少。
湖画家如何界定?时人喜欢非白即黑,习惯把美协、画院、研究院所、美术馆、学院之内的画家称为正统的学院派画家,而将剩下的那些学院派外“在野”的画家统统划归江湖画家行列。显然,这种分法没有剥皮见骨,也不够客观公允。其实,无论学院派内外,得先看看他们骨子里有没有江湖习气。只有沾染上了江湖习气的画家才是真正需要反对和贬斥的。确切地说,这类画家应称“江湖气”画家。
什么是“江湖气”?在我看来,有以下八大特征:
一是吹。
这种画家的第一把刷子不是笔而是嘴。他们靠嘴立艺,一天不吹活不成;都是“大师”,胆子大、脸皮厚;一般来头很猛,寰球、世界、国家级,主席、院长、理事长,甚至还有院士,出口就标榜是谁谁关门弟子,是哪里的教授、博导;每天都很忙,这边正开研讨会,那边两场开幕式还等着,车马费、出场费少了不干,昨天飞北京明天赶海南,似乎地球一离开他立马就停转;有时,也与“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师徒互吹。
二是骗。
他们随身带着各种作品润格、等级证书,甚至还有“国际ISO认证”,见人就说自己的画被哪个外国机构买走了,被哪个博物馆、美术馆、领导人珍藏了,在哪个拍卖会拍了高价,被哪些知名画廊追捧抢订,今年不买明年就涨价等等。其目的就是骗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人、手握大钱又附庸风雅的名流、狗屁不懂却到处撒臭钱的土豪和一些只认头衔不问艺术的收藏家。他们屡屡得手,以致市场上李逵敌不过李鬼,垃圾画横行。
三是演。
这种画家觉得,一个人画画就是在浪费生命。他们的用武之地不在画室,而在地摊、宾馆、酒店、广场,人越多、场面越大,越是能“人来疯”、耍得开。一次,笔者看到某画家正在搞“跳大神”式的表演。其不用毛笔,而是用烂抹布蘸墨,然后手舞足蹈地往宣纸上乱甩,时不时还拿嘴吹一下。一片狼藉后,他再拿手指勾勾连连、戳戳点点。不久,一幅“充满禅意的画”诞生了!
四是炒。
他们善于造势,出集子、办展览、开发布会、开研讨会,以捐助的名义搞拍卖、搞“互联网+”灌水,花样繁多。他们有的拉各种媒体吹喇叭、抬轿子,“鸡王”“猴王”“牡丹王”满天飞;有的找拍卖行做局,把几十元的地摊画炒到天价;还有的在画展开幕式上做文章,四处拉并不懂画的土豪、名流撑门面,即使人没来也要把名单列上,以炮制假新闻来求得轰动效应。
五是钻。
这种画家无心钻研学问,终日蝇营狗苟、投机取巧。他们嗅觉灵敏、八面玲珑、无孔不入。随着书画投资市场的逐年升温,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他们开始由艺术品低端市场向中高端市场渗透、冲刺,上下其手,以各种手段牟利。有些人不甘身处江湖,便竭尽各种手段通路子、挖门子、挤圈子,最后钻进金钱堆内,跃身成龙。
六是攀。
这些人相信“艺术可以通天”。他们曲意逢迎,使出全身解数去巴结土豪、名流,张口闭口说自己和某要人或某协会主席是好朋友。他们还拿着印有自己与各级名流及书画名家合影的集子四处招摇,甚至不惜PS造假,拉大旗作虎皮。更有甚者,竟然炮制出“现代中国十大画家”,将自己与齐白石、潘天寿并驾齐驱。
七是装。
这种画家画得不怎么样,却非常注重外在功夫,很善于装———装派头、装斯文、装清高、装深沉、装风雅、装豪气、装神弄鬼。人也怪模怪样,或大胡子、蓄长发、扎小辫;或秃头锃亮,双目微闭,手捻佛珠;或奇装异服、装疯卖傻,十分另类;又或者装“新潮”,动不动就“创新”,哗众取宠。
八是俗。
这是“江湖气”中病得最重的一条。其俗在骨,无药可治。这种画家十分崇拜李白———不是崇拜“诗百篇”,而是崇拜“能斗酒”。这类人不光身上有酒气,还有浊气、村气、匪气。他们交的全是酒肉朋友,聊的都是票子、房子、车子、女人。最可气的是,他们烂醉如泥后会精神病大发,狂涂乱抹,糟蹋宣纸和墨汁。
何谓“江湖”?在笔者看来,江湖就是社会。古时也好,现在也罢,画家有千千万,不“江湖”的能有几人?自古以来,身处江湖却成为大家的例子不胜枚举。齐白石一生江湖,最终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相反,那些被“养在钱中”衣食无忧的天价书画家,却未能飞出几只高翔蓝天的雄鹰。英雄出自草莽,江湖不可怕、不丢人,可怕的是“江湖气”!
“江湖气”是一种流行病毒,随时会侵害人。它不认白脸黑脸,也不管海内外,谁都可能被沾染。依我看,天价的往往比低价的更危险,沾染上的可能性更大。那些穷画家,形单影只、飘忽不定、无“家”可归,闹不到哪儿去。可那些富得流油的画家则大不一样。他们有位置、有地盘、有资源、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可以呼风唤雨,以“江湖气”做事游刃有余。近几年来,有些富得流油的所谓“书画家”利用自身所占有的近水楼台胡作非为,有的甚至走向堕落。
其实,“江湖气画家”是一顶飞来飞去的帽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落到谁的头上。
文章来源网络
鼻子插毛笔
那些超牛B的书法家们
如今江湖上写字杂耍很是流行,一白发老者,除左右手各执一笔外,两只鼻孔还各插一支毛笔来写字,状如怪物;一人将一长发女郎用白布裹成了僵尸状,着人倒抱着用她的头发濡墨写字……呜呼,此等恶俗的写字杂耍,真可谓天才发明,登峰造极!
唐代书法家张旭擅写狂草,性格疏放,落拓自任,嗜酒如命,每次大醉之后,呼叫狂奔,然后下笔,书法越发奇绝。在长安时他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焦遂等当世名流,结为酒友,人们称他们是“饮中八仙”。
唐代诗人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称赞他们过人的酒量、特殊的才艺和蔑视权贵的高贵品质。诗中对张旭作了这样的描绘:“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癫狂豪逸的张旭还有些孩子似的“人来疯”,爱好书法表演。据《书林记事》载:张旭大醉之后,曾经“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视之,自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故时人称之谓“张癫”。张旭脱掉帽子,用头顶上的发髻濡墨作书,大概可以算是如今写字杂耍的鼻祖吧。
如今江湖上写字杂耍很是流行。一些人不是认真习书练字,却醉心于哗众取宠的杂耍勾当:“倒书”丶“背书”、“双管齐下”、抱着如椽大笔在地上数丈的白纸上涂抹、伏在祼女身上写字。
更有甚者,我还惊见这样的图片:一白发老者,除左右手各执一笔外,两只鼻孔还各插一支毛笔来写字,状如怪物;一人将一长发女郎用白布裹成了僵尸状,着人倒抱着用她的头发濡墨写字……呜呼,此等恶俗的写字杂耍,真可谓天才发明,登峰造极!
这种写字杂耍不是书法,因为写出来的字仅有字形而无神采气韵,乌糟邋遢,毫无笔法、章法和美感。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书法、对文字的恶搞和亵渎。这些写字杂耍者哪里知道中华传统文化中原本有两个崇拜(信仰):
一是祖宗崇拜,崇敬老祖宗。这是数千年来中国人信仰系统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今每当清明时节中国人总要回乡祭祖扫墓,感谢祖辈恩德。
二是文字崇拜,敬畏文字。史书记载,汉字的产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创造汉字的仓颉头上有四只眼,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在中国尽管56个民族言语和风俗各不相同,但大家都识得和使用汉字,这才确保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各民族的统一。
的确,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密码,在古人眼里,它有着通神明、知自然、定规范、含历史、示未来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传统的私塾教育中,写着字的纸片不可随便丢弃,更不能踩在脚下;印着字的书籍决不可倒着放。其实,对文字的尊重就是对文化、对知识的尊重。
在中华传统文化百年断层、绝大多数人对笔墨书法完全没有感受的今天,倒是给那些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写字杂耍提供了市场。一些电视传媒也如同获得了“人咬狗”的新闻一般,对江湖上的写字杂耍,大加宣传报道,甚至还将他们请上电视演播厅的舞台。不仅写字杂耍者完全没有对汉字的敬畏之心,而且一些人甚至是政府机关对什么是书法艺术也不甚了解,还把这样恶搞出来的字当作书法作品,挂在厅堂上。
一次,我在深圳市一个政府部门的餐厅,看到墙上挂着一幅行书字,好不容易才辨认出来仿佛写的是“宁静致远”。我便问这幅字是不是裱反了?岂知那位领导笑答:这是某某书法家写的反书。我顿时愕然!还有一次,我在中山市某镇一位老板办公室里,看见赫然挂着一幅反写的“寿”字。老板见我惊讶的样子,解释说这是某位大师“反书”。我说:“怎么能挂这样的‘反书‘呢?‘寿‘字的反面是短命啊!”他听了脸色聚变,立刻将那幅字取下来。
宋代朱长文《续书断》中说张旭学习书法非常用心,“其志一于书,轩冕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终其身。”张旭年少时师从老舅陆彦远学习书法,而陆彦远的父亲就是唐代书法家陆柬之,至今有《文赋》墨迹传世。此外,张旭在常熟县慰任上,还曾学习过民间书法家陈牒父亲的笔法。他还曾勤习篆书、楷书。《郎官石柱记》就是他流传至今的楷书名作。而今江湖上的写字杂耍者没有继承张旭札札实实地学习书法的精神,却把他醉酒后的疯癫之举发扬光大了。那些违背汉字书写基本法则,甚至是违背人伦写出来的字,根本就是不是书法作品,而是毫无艺术价值的垃圾罢了。
作者:王世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