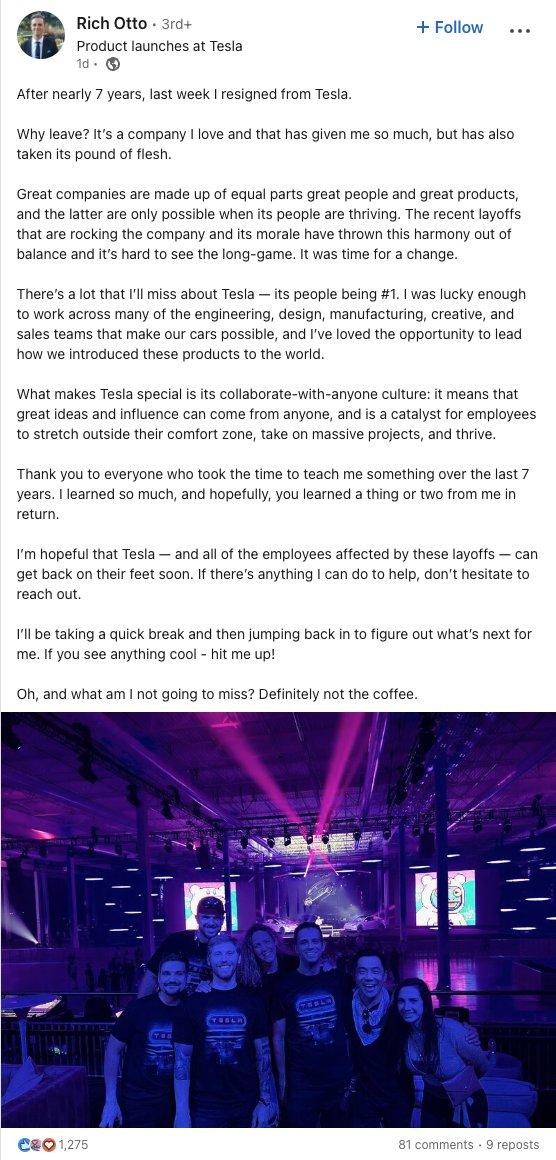2018互聯網黑夜裏的一抹亮色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itlaoyou-com
若給2018年的互聯網定調,那它一定不是暖色調。在中國經濟下行週期下,資本寒冬接踵而至,如何過冬,是大大小小互聯網企業命懸一線的問題。
睿智的企業,往往穩字當頭,因爲,你不知道關鍵“那一棒”到底打在哪兒,所以必須拼命奔跑。2018年上半年很多企業選擇了IPO拓展融資通道,搶在嚴冬到來之前拿到那張“護身符”。因而掀起了自2000年第一批互聯網企業上市潮以來,最爲集中和緊密的第二波浪潮。
在2018的IPO大年中,港交所共有207家公司掛牌,募集資金總額2778.5億港元,全年IPO上市數量和籌資額均位居全球第一。
搶跑同時也意味着有死亡、有徘徊。尤其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企業關張、倒閉、裁員的浪潮如期而至。金立、 ofo、錘子等企業無一僥倖,甚至包括BAT巨頭級別的企業在內,裁員、降薪的消息接連不斷。
互聯網的黑夜來臨。
並不是所有企業都搶跑出線,不過,在一衆掙扎的企業中,我們看到一些律動的音符,在低沉和沮喪中彈出最強音。
它們是小米榮登港股成爲第一支同股不同權的企業;它們是美團點評在生活服務的賽道上搶跑出線,它們是拼多多不到三歲登陸納斯達克,閃電的速度再次刷新記錄,它們是抖音在不到一年時間裏,煉就億級日活用戶這把鋼槍;它們是知識付費賽道里從春走到夏;它們是下沉用戶需求之花綻放……
它們是2018互聯網裏的一抹亮色。
黑夜裏的搶跑
2018年的互聯網故事,可以從IPO開始。
去年1月,華米科技遞交招股書,募資1.5億美元登陸美股;2月28日,華米正式在紐交所敲鐘,首日逆勢收漲2.27%,成爲小米生態鏈中第一家上市公司。
在它之後,也是繼美圖、閱文、衆安新經濟三駕馬車之後,港股大門不斷地被新經濟企業敲開。
2018年4月,港交所迎來25年來最大變革,允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5年前,正是因這條金科玉律,阿里撤出港交所,但過去一年間,香港正吸引着未來的“阿里巴巴們”。
去年5月,新上市規則公佈一月後,平安好醫生率先敲鐘,作爲國內首屈一指的互聯網醫療企業,過往三年累計虧損超20億仍能“平安”上市,港交所也在起變化。
隨後,小米、美團點評、映客、獵聘網、51信用卡等新經濟企業紛紛在港上市,最盛一天,港交所有8家企業同日上市,網友吐槽“鍾都不夠敲了”。
不止香港,這股“新經濟上市熱”持續蔓延到國內和海外,他們都趕在IPO大船起航時登艦。
今年上半年已經或者即將湧進上市之門的有虎牙、B站、愛奇藝、映客、騰訊音樂、鬥魚、快手、多益網絡、指尖躍動(短視頻內容,文娛遊戲類);優信、小米、華米、工業富聯(硬件相關的);美團點評、同程藝龍、獵聘、滴滴(生活服務,資訊服務類);尚德教育、滬江教育(在線教育);寶寶樹、拼多多、找鋼網、(電商類)華興資本、螞蟻金服、(投資、互金類)等等企業。
但波濤四起的海平面下仍埋藏冰山。
據騰訊證券統計,去年港股IPO的破發率31.2%,同比增長16%,爲近四年最高值。在港交所的開放政策下,大量連虧企業流血上市,甚至像歌禮生物這類未盈利企業都被港股開了綠燈。
上市前估值縮水,上市後股價破發,可見資本市場對新經濟盈利模式仍有狐疑,但從另一角度出發,2018年的IPO潮也襯托着資本市場的冷清。
在上市的新經濟企業中,大部分的融資輪次停滯在一年前,雖然業務現金流足以支撐他們前進,但若想在競爭中持續勝出並拓展新領地,資本彈藥依舊需要補給,新經濟需要投資
有VC業內人士表示,兩三年前,互聯網創業只要有個idea就能拿到融資,但現在,創業者要給VC看轉化率、變現率,要讓投資人先看到錢。
觀點或許偏頗,但也是真相的一部分。
當這些成長不到十年的新經濟企業在一級市場失去吸引力時,二級市場就是他們斬獲資本的新希望,即使被媒體塑造爲“流血上市”、“首日破發”,也掩不住他們搶跑成功的“喜悅”,
因此,到下半年,寶寶樹、騰訊音樂仍成功搶跑,滴滴、鬥魚們卻沒等來發令槍,等來的缺失刺骨寒風。
去年10月,有媒體曝出華爲、阿里等企業將停止社招,雖然這一消息被官方指認爲假新聞,但“年末人員優化”卻是不爭的事實。
不止他們,京東、美團、網易、騰訊、知乎、鬥魚等一衆企業都相繼被曝裁員,最高裁員數甚至達到6000人,甚至便利蜂還用“高數大考”這招變相裁員。
雖然,這股裁員潮在官方口中不是變爲“假消息”,就是美其名曰“人員優化”,但聯繫起上半年的IPO上市潮,一幅2018互聯網浮世繪徐徐拉開。
寒風裏,新經濟企業們嗅到了危機,在下行週期中,互聯網創業家帶領團隊用自己的姿勢過冬,無論上市“找錢”還是裁員“省錢”,都是度過週期之道。
曾經的前景正變成“錢緊”,這一幕如期而至。
不止是資本“發難”,互聯網人口紅利消失也是繞不開的話題。在中國互聯網近25年的歷史進程,各類模式創新輪番上演,作爲主力市場的一二線城市過度飽和,拉新成爲一大難題。就連鵝廠掌門人Pony都感嘆:看不懂95後。
錢在哪?人又在哪?這是互聯網企業2018年求解的問題。
只不過,在這個略顯寒冷的冬天中,仍然有一輪暖陽初升。
小鎮中有機會
“二姐,幫忙點下砍個價吧。”
“三叔,這個拼團幫我分享到你那個牌友羣裏唄。”
農曆新年中,家人團聚時,北上廣的“Cindy、Tim”們回到小城裏都變爲“翠花、二狗子”,七大姑八大姨紛紛上你家門,幫你“指點迷津”。
只不過今年回家,三親六戚可能還會讓你幫着“拼個團”,這歸功於電商平臺“拼多多”在三四五線小城的橫空出世。
消費降級、假貨、五環外……2017年“走紅”的拼多多有不少極具爭議的標籤,但在過去一年,“上市公司”將是拼多多的新關鍵詞。
成立不到三年、中美兩地共同敲鐘、創始人曾獲段永平和丁磊提攜,在爭議的背後,拼多多也身披不少光環,這或許也推動它在上市首日股價漲超40%,一掃新經濟破發陰霾。
不止是身份標籤,拼多多各項數據也十分亮眼。根據拼多多最新財報顯示,2018年拼多多的GMV達4716億元,同比增長234%,十倍於行業均值;年度活躍買家達4.185億,以此指標拼多多已經超過京東成爲中國第二大電商平臺;2018年第四季度,拼多多月活用戶達2.73億,單季勁增4200萬元,在流量紅利消盡的大趨勢下,拼多多的漲勢驚人。
對於他的成功,有人說是拼團模式,有人說是微信流量,有人說是價格便宜,而這些觀點也都有正確之處,但都無法概括拼多多的崛起。
拼團與便宜貨,電商巨頭能快速複製這樣的玩法,而且像淘寶“聚划算”、跨境電商“wish”都是這種玩法的先行者,拼多多僅靠這一點不可能如此成功。
因而,拼多多成名關鍵在於“娛樂玩法+社交流量”的雙輪驅動。
在拼多多上,秒殺、拼團、現金簽到、組隊尋寶、分享砍價,衆多遊戲式玩法讓購物變得各有娛樂性,鼓勵對外分享的形式也一點點激活着用戶的社交網絡。
雖然黃錚在採訪中多次否認“流量主要微信”這種說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微信確實給予了拼多多充分施展拳腳的天地,當一個個拼團秒殺鏈接在微信羣中裂變式傳播時,社交關係被一件件“便宜貨”激活,拼多多有了自己的流量池。
數據顯示,截止2018年底,拼多多的活躍買家達4.185億,同比增長71%;截止2018Q4的月活用戶爲2.73億,同比增長94%。
數據固然可喜,“娛樂+社交”固然成功,但更重要的是,在互聯網人口紅利消失之下,拼多多找到了小鎮裏的大機會。
據國泰君安證券研報的相關數據,全國一二線城市居民約3.9億人,三線以下城市及農村鄉鎮地區居民規模多達10億人,佔比超過70%。
龐大的人口基數是新商業故事的開頭,其次,特殊的消費結構將故事推向高潮。
同時,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其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這意味着四線城市外、24歲以下的用戶,人均月薪不足2000元。
與低薪收入相匹配的是,除了影院、餐廳和KTV,他們的娛樂生活相對匱乏,慢節奏的小鎮生活卻反哺出大量休閒時間,智能終端是他們的娛樂利器。
可見,低收入讓小鎮用戶對價格敏感,對品牌不敏感,大量空餘時間讓他們成爲移動互聯網性價比最高的“流量”。這優勢就像一個個火藥桶,只等互聯網的火星來引燃。
顯然,拼多多是點燃後最響的那一個。
不止於此,過去一年,借網賺模式興起的趣頭條也成功上市,更早前,倡導公平原則的快手也曝出將在2019年上市,他們和拼多多一起組成了“下沉三傑”。
電商的拼多多,閱讀的趣頭條,娛樂的快手,下沉市場用戶正被這些APP奪去時間,並且讓國人看到了小鎮的力量,引得巨頭們爭先入局,這也是2018年不多見的一抹互聯網亮色。
當然,如果這抹亮色的筆觸再多描一點,城市裏的年輕人也有大機會。
年輕人愛速成
“好嗨哦,感覺人生達到了巔峯”。
長相清秀的餘兆和沒有想到,一句貴州方言的變裝秀,讓他成爲2018下半年冉冉升起的新抖音網紅。
在他創作的“貴普毛毛姐”一戰成名前,餘兆和只是拍些略帶炫技的生活視頻,點贊數也會到達10萬左右,不過內容缺乏主題。
直到方言表演城鄉蹦迪差異的視頻出現後,餘兆和賬號“多餘和毛毛姐”的粉絲數在2個月內上漲1500萬,3個月內突破2000萬。
一開始,很多人用“好嗨哦”當BGM;之後,很多人盜轉他的視頻;最終,連朋友都告訴他“你火了”。
現在,他儼然成爲網紅界的各種翹楚,平均每條抖音點贊量過百萬,國內拍視頻、出海拍廣告,行程也是滿滿當當。
或許,對餘兆和來說,他的火爆與傳播他內容的“很多人”分不開。
2018年,抖音創造了短視頻新奇蹟,通過音樂短視頻玩法激發用戶創作慾望,今日頭條的算法推薦作爲其技術加成,抖音打造一個有一個流量增長神話。
截止到2018年12月,抖音的國內DAU達2.5億,MAU達5億,這一數字接近微信月活的50%。
和拼多多一樣,抖音流量暴增背後也是對用戶的“新發現”。
據2018年12月的艾瑞數據顯示,抖音的一二線城市用戶佔比45%,略高於行業其他平臺;24歲及以下用戶佔比51%。
生於1995年後,長於互聯網市場飽和的大都市,他們是消費“毛毛姐”的主力人羣;同樣,進入2018年後,最後一批90後成年,他們正扛起中國互聯網的消費大旗。
當然,和7080後不同,他們標識着自己的消費領地。
據騰訊QQ的95後報告顯示,在他們興趣榜單中位列前三的是遊戲、影視和動漫,此外,95後的消費行爲中,超額消費佔比36%,月光族爲38%,存錢的僅爲26%。
在大部分95後身上,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滿足,溫飽不再是問題,他們更願意爲興趣自掏腰包,對於長期金錢規劃並不感冒,“及時行樂”或許是都市年輕人重要的人生信條之一。
就像速成班一樣,用金錢獲得快速滿足,這一點在知識付費領域中尤爲明顯。
以喜馬拉雅爲例,2018年數據顯示,一線城市用戶佔比55.25%,8090後的付費用戶累計佔比超過70%,他們早已是平臺消費主力軍。
或許是因爲這股生力軍,喜馬拉雅去年的123狂歡節以4.35億的最終銷售額收官。
在音頻知識付費中,主講人向用戶傳授一種思維,讓用戶學會一種技巧,並能在實戰中快速落地,這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中,正是8090後所急需的。
因而,花費金錢後,“及時行”地不一定是樂,也可能是自我學習。
但無論知識付費或者抖音等短視頻,平臺牢牢鎖定這批在北上廣大都市裏生活的8090後,在快節奏生活和碎片化時間的環境中,15秒到達人生巔峯的短視頻和15分鐘學會實用技巧的模式同樣適用。
這些模式擊中的,正是都市青年愛速成的心理。或許,他們也和小鎮青年一起在編織着2018年互聯網的一抹亮色。
當中國互聯網即將駛入第25個年頭時,歷史進程中的互聯網弄潮兒正負重前行,IPO、裁員、架構調整,他們都在爲自己謀劃減重道路,而不是逃跑計劃。
2018這抹亮色,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在黑夜中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