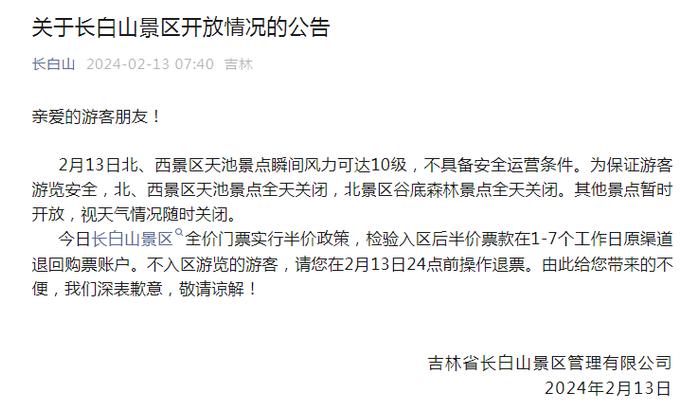史海鉤沉:回首頻頻來時路——話說清帝東巡
摘要:正因爲滿族先人世世代代生息於白山黑水,他們創建的清王朝肇興於關外沃土,其氏族神蹟發於長白,祖宗陵寢基於盛京,因此,當清帝國的統治者們前赴後繼、耗時費力、大張旗鼓地南巡(下江南)、西巡(去西安)、北巡(赴蒙古)、東巡(山東祭孔)時,始終不忘被視爲“祖宗肇跡興王之所”、“興龍重地”的東北和吉林,頻頻將熱切的目光投向關外那片廣袤的黑土地,於是有了又一個區別於赴山東祭孔的“東巡”。這期間康熙兩到吉林,但只有1682年第二次東巡時專門望祭了長白山。
(一)
在中國歷史上,曾被古人名之爲“不鹹”的長白山絕對是一座繞不過去的大山。在現實生活中,它更是一座讓旅人遊客瞻之往之的名山。
自打從關內來到關外的半個世紀中,我和無數來此的遊人一樣,曾經多次在長白山下遙望過林海窮盡處一抹懸浮天際如滾滾雪龍般的白色山影,在沒有親自登臨之前,原以爲它是乍然呈現在眼前的一個與自然界的神祕和人間世的玄奧融合成的巨大傳奇,凡是遙望它的人,都會生出許多奇思玄想……但直到很久之後,才知道早我輩三百多年前的某年某日,一位高踞於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皇座上的年輕男人,也曾於此用他虔敬的、熱切的、深情的目光,凝視着、遙望過這同一座大山山影……
三百多年後,長白山依舊巍然屹立於斯,而那位和我們看同一景物的帝國至尊早已塵歸塵土歸土,虛化無形了。但他確實是在那一天來過此處,構成了驚鴻一瞥的歷史瞬間的啊!
據史料記載,“那一天”是這樣展開的——
從1671年到1698年,康熙皇帝曾三次馳馬關外“東巡”,輪跡蹄痕碾印在白山黑水之間。爲的是“寰宇一統,用告成功”,以此謁祭太祖、太宗山陵。這期間康熙兩到吉林,但只有1682年第二次東巡時專門望祭了長白山。這次東巡,聲勢浩大,據記載,參與人員達七萬人,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描述:“旌旗羽葆絡繹二十餘里,雷動雲從,誠盛觀也。”
是日,天氣晴好,在吉林小白山(溫德亨山)上遙對長白山西北方向的望祭殿,那位高踞帝座的年輕男人帶着平定“三藩”的餘威和榮耀,閱視吉林水師的激情,率先拉開了有清一代望祭長白山盛典的大幕。這位康熙爺,史載“天表奇體,神采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嶽立,耳大聲洪,絢齊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康熙此時28歲,應該就是上文所說的“稍長”之年吧,撇開前面那些對帝王歌功頌德的諛詞套話,“舉止端肅”云云,與我們現在見到的當時康熙的畫像,倒可互爲印證。然不論康熙實際上樣貌如何,“天下第一男人”的至尊身份和他自8歲登基始非同小可的歷練與作爲,都必然會賦予他一種雍容華貴君臨一切的不凡氣度。在莊嚴肅穆的獻祭鼓樂聲中,在隨侍的朝廷和地方官吏的簇擁下,年輕的大清皇帝三拜九叩,行禮如儀,虔誠地朝東南方的長白聖山遙相拜祭。禮畢,隨侍、陪祭臣工恭請聖駕回鑾,但康熙朝東南方向遠眺良久,盤桓再四,遲遲不肯離去。一代英主,心中有着怎樣的化不開的家國情結啊。他的《望祭長白山》詩,揮灑了他彼時的感悟和祈願:
“名山鍾靈秀,二水發真源。翠靄籠天窟,紅雲擁地根。千秋佳兆啓,一代典儀尊。翹首瞻晴昊,岧嶢逼帝閽。”
(二)
莽莽長白山,高天厚土的吉林大地,乃至整個關東白山黑水,對於康熙大帝,對於滿清皇室,對於大清帝國,具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
當年滿人乍興於關外,爾後鐵騎大舉入關,明王朝突然崩塌,小民們三百來年習慣了的紫禁城皇座上的漢族皇帝一夜之間變成了腦後拖着長辮子的異族皇帝,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大變局太突然,太突兀,太不可思議。這個民族,這個王朝,彷彿是從另一個世界闖進來的異類,叫人耿耿於懷,寢食難安,必欲驅之而後快。殊不知這個幾經演變的滿族已在中華大地繁衍生息數千年了。滿族先人可上溯到先秦之前的遠古時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肅慎族,這個肅慎族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連串的更名:東漢時號挹婁,南北朝時改爲勿吉,後又改爲靺鞨,到隋唐時渤海國在吉林的敦化一帶建立,“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這個渤海國是滿族先人建立的第一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渤海亡後其遺族又易名爲女真,建立了滿族史上的第二個政權金朝,其繁衍生息的故土吉林由是被視爲肇興之始的“金源內地”。金朝末年,蒙古崛起,金亡,元興。女真這個有着操弄政權的傳統的民族一度處於蜇伏期,直到明代。此時天降異人,努爾哈赤橫空出世,以文武之道統一女真各部,創立八旗制度,又創建了一個大金政權(史稱後金),並由遼陽遷都盛京(今瀋陽)。這是滿族史上的第三次創建政權。自此,女真族正式改稱滿洲族(簡稱滿族)。隨之,大清政權也正式確立。1644年,清王朝八旗鐵騎將這個“韃虜”政權馱進了北京,滿族第三次建國的權力遊戲也由“大清國”前奏進入大清帝國的高潮,這支由白山黑水奏響的傳奇樂章在轟鳴了268年之久後纔在帝都北京曲終。
滿族作爲一個由白山黑水孕育培植出來,定鼎北京,一統全國的少數民族,其與關外的白山黑水,與吉林的淵源既深且厚。爲了推崇這片誕育了先祖愛新覺羅氏族的發祥地,神化其受命於天的正統性、合理性,清太宗皇太極追溯滿族源流,最早提出了三仙女的神蹟之說。其核心內容就是長白山東北布庫裏山下有一名爲布兒瑚裏的湖泊,一日天降三仙女浴於斯,有神鵲銜一朱果置於小妹佛庫倫衣上,而又爲佛庫倫吞食,感而成孕,生一男,自稱姓愛新覺羅,名布庫裏雍順。這裏的關鍵不僅在於爲大清皇權天授造輿論,還在於三仙女傳說的發生地就在長白山下。長白山東北30公里處有一紅土山,山下有一圓池,立有一碑名“天女浴躬處”,即是愛新覺羅氏族的發祥之地。由此可見長白山在滿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深厚淵源。
正因爲滿族先人世世代代生息於白山黑水,他們創建的清王朝肇興於關外沃土,其氏族神蹟發於長白,祖宗陵寢基於盛京,因此,當清帝國的統治者們前赴後繼、耗時費力、大張旗鼓地南巡(下江南)、西巡(去西安)、北巡(赴蒙古)、東巡(山東祭孔)時,始終不忘被視爲“祖宗肇跡興王之所”、“興龍重地”的東北和吉林,頻頻將熱切的目光投向關外那片廣袤的黑土地,於是有了又一個區別於赴山東祭孔的“東巡”。
首次提出“東巡”構想的是順治帝。清入關第10個年頭,順治就表示,“自登極以來,眷懷陵寢,輒思展謁”,只是由於當時關內戰事仍很緊張,諸王大臣又紛紛表示反對,以致未克成行。將東巡構想變成行動的是順治之子、雄才大略的康熙。1671年清王朝東征西討,大體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剛剛親政不久的康熙皇帝即決意東巡,告諭禮部說:“朕仰體世祖章皇帝遺志,欲躬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以告成功。”經過充分準備,康熙十年九月,玄燁從北京出發,開啓前無先例的首次東巡。但這次東巡是直奔盛京而去,在那裏他親自祭奠福陵和昭陵,在此盤桓月餘,然後返京。此次東巡並沒有來吉林,但回到北京後卻有一系列動作:在順治年間修築的“盛京邊牆”(俗稱“老邊”)之外,又修築了長達690華里的“柳邊”(俗稱“新邊”),對東北局部即長白山地區實行封禁,以收固邊防,劃區界,保龍脈,佔特產之功。又喻禮部等衙門議復封“長白山之神”,在吉林小白山烏拉望祭。並於1677年命內大臣武穆納去關外踏查長白山。“長白山乃祖宗發祥之地,今無確知之人。爾等前赴鎮守烏拉將軍處,選熟悉路徑者導往,詳見明白,以便酌行祀禮。”這是長白山崇祀的準備。
接着,1682年和1698年,康熙又進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東巡,這兩次東巡都來過吉林,先是閱視吉林水師,佈置抗擊日俄事宜,後是抗擊沙俄、平定葛爾丹叛亂成功後,到吉林奉祀祖陵,巡行塞北,經理軍務,尤其是在清朝歷史上首次望祭了長白山。康熙帝的東巡,爲清王朝的東巡制度奠定了基礎,成爲謁祭祖陵、安撫滿族、籌劃東北邊疆建設的國家行爲,同時也成了清朝歷代皇帝要遵奉的一項“祖制”。這之後,還有10次東巡,其中雍正帝在還是雍親王時,曾代父東巡謁陵一次。自己登基後並未親臨。倒是乾隆,挾康雍乾盛世之威,曾4次東巡,大手筆破了乃祖康熙的記錄,其子孫更是難以望其項背。
(三)
公元1754年9月23日,康熙之孫乾隆帝浩浩蕩蕩一行第二次東巡謁陵時到達吉林城。此時乾隆43歲,較其乃祖望祭時年長15歲,登基已19載,正是一個男人年富力強,治國經驗達於成熟之時。“他的目光自信,絲毫沒有掩飾。他的臉形稍長,呈橢圓形狀,五官勻稱而帥氣。他的表情淡定而顯慧智。嘴脣豐潤,雙耳和下頜突出,膚色白皙,面部尚無須髯(在後來的畫像中,就有了細須之跡象)。”美國傳記作家歐立德在這裏描述的是清廷意大利籍畫師郎世寧在乾隆25歲時爲他畫的像。雖然望祭長白山時已過去近20年,但大致形容應不會大變,只不過這位人到中年的皇帝此時脣上已有細須,成熟的經歷了風霜的沉毅面容使其更具最高統治者的威儀。自然,他東巡的排場絕不會遜色於乃祖。翌日,在吉林將軍傅森、副都統額爾登額扈從下,在沉寂了許久的小白山望祭臺繼乃祖之後隆重舉行了大清史上第二次望祭長白山盛典。這位春秋鼎盛的皇帝,在國家治理上已取得政府機構改革的成效,全國稅收蠲免,金川戰爭取勝,拉薩平叛成功,準葛爾戰役大捷等一系列成就之後,腳踏祖先發祥的熱土,遙望滿人心中的長白聖山,一定神思悠悠,追想無極。於是宣讀御製祝文,並留下兩首詩。
其一曰《駐蹕吉林境望叩長白山》:“吉林真吉林,長白鬱嶔岑。作鎮曾聞古,鍾祥亦匪今。邠歧經處遠,雲霧望中深。天作心常憶,明禮志倍欽。”
其二曰:《望祭長白山》:“詰旦升柴溫德亨,高山望祭展精誠。椒馨次第申三獻,樂具鏗鏘葉六英。五嶽真形空紫府,萬年天作佑皇清。風來西北東南去,吹送羶薌達玉京。”
清代康乾二帝皆精通漢文化,尤喜吟詩,據說乾隆一生作詩在萬數以上,但評價不高,能被人記住者幾稀。這兩首詩明白淺達,或許會隨着長白山文化一起流傳下去吧。只不知乾隆彼時彼刻是否會遙想起72年前乃祖康熙爺來此望祭時寫下的那首詩呢?
但這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他們爺孫三代開創的康雍乾盛世已近百年,至乾隆時已達巔峯之狀。據後來國外學者統計,其時中國的GDP佔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國家空前強盛富足,自然給了統治者行使權力,採取行動,制訂遊戲規則的更大空間。終乾隆一朝,將康熙開創的巡遊之治推向了頂點,大大小小共巡遊數十次,期中南巡6次,東巡4次。這樣頻繁的巡視活動,所費必然甚巨,已引起地方和臣子的不滿和非議。對此,乾隆特別強調它對於瞭解民情,安撫民衆,解決民訴,加強民治,整飭武備,強化邊防,整頓吏治的重要性。即以這次東巡爲例,乾隆不僅望祭長白山,到盛京謁祭祖陵,還效法其祖康熙特地到吉林松花江上閱視水師,佈置抗擊沙俄事宜。
說到康熙親臨松花江閱視水師,是在1862年東巡時。其時立國不久,鞏固皇權,維護一統,穩定政局民情,是當時最重要的國家使命,平叛削藩、收復臺灣、保衛東北、反擊沙俄、親征葛爾丹、進兵安藏,加上治理河道,發展農業生產,國家大事不斷。而此時鐵騎入關的八旗軍兵雄風尚在,整個滿清王室尚在勵精圖治。因之康熙東巡除了完成祭陵謁祖的規定動作,他沿途目光所及、情思所牽更多地是在政治生態、人事代謝上勾留。1671年康熙第一次東巡抵盛京,即召見黑龍江將軍巴海,垂詢邊防軍務諸事,告誡巴海:“俄羅斯尤當慎防。”並賦詩一首賜巴海:“夙簡威名將略雄,高牙坐鎮海雲東。……盡使版圖歸化日,遠教邊徼被皇風。”以示嘉勉。1682年二次東巡,對自順治始,中經他自己陸續築成的柳條邊歌詠寄情,對“重關稱第一,扼險倚雄邊”的山海關賦詩致慨,表達了鞏固邊防,通過修明政治消弭戰事的願望。而最能體現康熙心繫天下大事的是,1682年康熙第二次東巡,在望祭長白山之後小憩兩日,即泛舟松花江上,駛往大烏喇(今吉林烏喇街)。康熙在船上襟袖盈風,江上水師船隊帆桅相接,興之所至,揮毫書《松花江放船歌》,除了描繪放船勝景,抒發喜悅的心情,還特意表示:“貔貅健甲皆銳精,旌旄映水翻朱纓,我來問俗非觀兵。”康熙及乃孫都不愧是處理軍務和民生辯證關係的大師,深知爲了加強軍事鬥爭力量,最根本的是要改善民生,而改善民生的首務就是要了解民情民意。一句“我來問俗非觀兵”凸顯出了這個宗旨,同時不着痕跡地隱去了其在軍事武備上的良苦用心。也顯示出一代英主雄兵在握不妨超然的氣定神閒,且帶着幾分顧左右而言他的調侃。
而乾隆,這位自幼深受康熙器重、親政時常以乃祖爲法的皇帝,當他踏足吉林,重循乃祖足跡時,特作《松花江放船恭依皇祖詩韻》:“隆崇長白佑維清,松花江源山頂生,飛流銀河練影明。縈迴行裏竹箭輕,望祭申焑如鸞鳴,臨江遂命青雀橫。水天上下秋光晶,馮夷靜恬濤不驚,擊汰直達吉林城……”
歷史事實表明,康乾二帝東巡,在“觀兵”的同時,對“問俗”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康熙的“問俗”內容寬泛,關心兵民疾苦,革除官員惡習,調整官民軍民關係,緩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發展農業生產,加強東北地區建設,統統包括在內。而乾隆更多地是關注民生民俗和地方的風物人情,這從他4次東巡留下的三百餘首詩作中可以看出來,其中與民生有關的詩多達60餘首。人蔘、貂皮、鹿、山果、松子、鱘鰉魚、駝鹿、熊羆、海東青、東珠、松花玉、五穀、木紙、糖燈、小船、木桶、小匙、爬犁、樺皮屋、麻草束、煙囪、擱板、嘎啦哈等等東北民間起居生活、生產勞動、民俗風情的種種物件和東北特有的動植物、農作物都被貴爲天子撫有四海的乾隆擷取入詩,且都觀察細緻,飽和感情,這不僅在清代歷史上,就是在中國歷史上都十分罕見!作爲一位封建帝王,如果不是真正關心社會民生、江山社稷,怎麼能放低身段,去歌詠這些在時人看來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物事呢!
乾隆之後,嘉慶帝在1805、1818年先後兩次東巡,道光帝1829年也東巡過一次,其時大清王朝已邁過巔峯,敗象初顯,開始走下坡路。嘉慶、道光的東巡已無復乃祖當年的顯赫。道光之後,已是清晚期,疲癃盡顯,自保尚且不足,哪還有餘力餘暇東巡!可以說,東巡的興衰,正是大清王朝由盛世走向式微的窮途末路的一個縮影。
(四)
中國歷史上,帝王巡遊並非自清朝始,其作爲治理天下的一種帝王之術,始作俑者可上溯到上古時代的帝王,黃帝、舜、禹等均曾巡遊天下。但鬧出大動靜來的還屬“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王朝建立後,爲進一步加強對全國的統治,秦始皇效法先王,從公元前219年始,接連5次“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巡遊所到之處,皆立刻石,或頌秦德,或紀秦功,或飭秦法,還針對巡遊發現的問題採取措施,鞏固統一,加強邊備。這些巡遊在當時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其頻繁的出行和龐大的規模,加上始皇帝爲逞私慾,所費靡巨,勞民傷財,激起了民怨民憤,負面效用超過了正面效果,最終導致秦帝國的覆亡。
在巡遊的奢華、排場的浩大上足可與秦始皇PK一下的是800年之後的隋煬帝楊廣。其時隋剛立國,楊廣通過弒父殺兄奪取了皇位,爲了加強對全國政治上的控制,打通南北物資的流通,楊廣幹了兩件大事,一是在洛陽新建一座都城,號東都;二是開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幾年後,從東都到江都的大運河甫一完工,煬帝就率20萬人的龐大隊伍巡幸江都。一則遊玩享樂,二則威懾子民。爲了這次巡遊,幾千艘大船首尾相連竟浮江二百里,一路上8萬多名民工被徵發來爲之拉縴,兩岸百性被逼迫置辦酒席“獻食”。到江都後楊廣領着隨行百官和宮娥妃嬪,各色人等花天酒地,揮霍享受,整整鬧騰了半年才又大張旗鼓地回到東都。這以後楊廣幾乎每年都出巡遊樂,極盡鋪張之能事。
秦始皇,隋煬帝,也曾是史上攪得周天寒徹的狠角色,但他們的巡遊與康、乾二帝相比,在歷史的深刻性上、在治國理政的功效上,在巡遊本身目的的內涵、目的的精神層次上,在巡遊的範圍上都差了好幾個檔次。這裏不說康乾的南巡、西巡、北巡,單說回其祖先發祥地的東巡吧。清帝們的東巡,從一開始就目的明確,路徑清晰,通常都是:一是到盛京謁陵祭祖。祭告的主要內容是總結在關內取得的重大成績;二是通過召見、賞賜、免賦、減刑等安撫滿族,兼及關外的漢、蒙羣衆;三是籌劃建設東北的邊疆大計;四是抵近觀察民情民俗,隨機解決問題;五是到吉林望祭滿族先祖發祥地長白山。而且,清帝的歷次東巡,大多發生在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節點上,如康熙第二次東巡祭祖的重要內容,是稟告三藩之亂的平定,同時也爲反擊沙俄侵略作實地考察。乾隆的4次東巡,雖然龐大的巡遊隊伍沿途也少不了驚官動府、勞民傷財,但確實是爲了清帝國長治久安採取的重大行動。而始皇帝的巡行郡縣,目的就是“以示強,威服海內”,開始也有一些重大設計,如到泰山舉行封禪大禮,但後來逐漸變成了他隨心所欲的享樂之旅,流傳到後世的奇聞軼事是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以獲長生不老藥;興師動衆徒勞地到泗水搜尋周鼎;搏浪爲刺客狙擊;又親自入海在之罘射殺巨魚,最終死在巡遊途中被伴以鮑魚送回長安,等等。至於隋煬帝,他巡幸江都荒淫無道的享樂,已成爲後人小說創作的素材。明代白話小說《隋煬帝逸遊召譴》即其一也。它將煬帝借巡遊大耗民脂民膏荒淫無道最後身死人手的史實用小說手法鋪排開來,內含譴責,足爲後世之警。
從治國撫民的政治層面看,在康乾等清代諸帝的考量中,可能南巡的意義和作用最大,那是要深入南方,行經大半個中國廣大漢人居住的地域,有漫長的海防線,名城巨市旗布,商賈雲集,保持這些地方的安寧繁盛,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看,對於清王朝的安危穩定都至關重要,所以每一南巡,不光聲勢浩大,且須精心佈陣,耗時費力,不可輕心,實際上南巡途中也在不斷演繹精彩故事,不僅在當時,即便今天,也都是文藝作品的保留題材。但是,東巡更有它的獨特性。清統治者精心發起組織這個重走來時路(其祖關外興起奮鬥入關終成大業)的盛大活動,本身就有教育子孫後代不忘根本、銘記先人當年“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創業史的良苦用心。於此也可看出康乾對帝國未來命運的深謀遠慮。此外,撇開它固邊、撫民的功用來說,東巡因其謁陵祭祖、重回故鄉的內容,而使其具有了表達孝敬、釋放鄉愁的意義,具有了濃濃的“常回家看看“的親情味。
最早提出東巡想法的順治帝福臨說:“自登極以來,眷懷陵寢,輙思展謁。”“今將躬諸山陵,稍展孝思”。這裏“孝思”成爲福臨回鄉的出發點。康熙帝決意東巡,也說是“體仰世祖章皇帝遺志”,即表達乃父未盡之孝思。可見,人無分貴賤,上自皇親貴胄帝王家下至黎民百姓,都對生我養我的故鄉一往情深,去國離鄉都斬不斷那片鄉愁,這正是家國之思最深厚的源頭。早在康熙帝尋根敬祖500年前的金王朝,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之孫金世宗完顏雍就遏止不了祖輩傳承的思鄉情結,自京城中都(今北京)東巡魂牽夢繞的女真族興起之地吉林,並在今吉林省扶余縣徐家店鄉石碑崴子村爲其祖金太宗起兵反遼誓師處立碑頌功,這就是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大金得勝陀頌碑》。作爲由女真嬗遞而來的滿族帝王,康熙、乾隆們熟知歷史掌故,他們東巡來吉林重履故土時,該會接續起這代代相承的血濃於水的鄉愁吧。
(五)
康熙、乾隆們俱往矣,唯有長白山依然在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後來人凝注的目光。“遙望山形長闊,近視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盪漾,池畔無草木。”這是1677年6月,內大臣武穆納一行奉康熙之命,實地踏查長白山時所見。而今,白山依舊在,人世幾滄桑。比康熙、乾隆那些貴爲帝國至尊的男人們幸運得多的是,今人、後人們不僅可以遙望長白山,而且可以直登白山之巔,一覽天池勝概。不爭的事實是,長白山因清帝們的崇祀而位比泰山,源遠流長的長白山文化也因此而增添了極爲重要的歷史內涵。清帝們又因東巡、望祭而使人們永遠記住了關東大地和長白山在中原版圖上的重要地位,記住了一個從遠古蠻荒之地走出來的民族是怎樣艱苦奮鬥,一步步走進中華腹地,同漢文明相融合,成就近三百年的一統江山的。現在,當我們再回望長白山時,那一抹如滾滾玉龍般的白色剪影中會時不時浮現出那兩位帝國至尊強悍而虔敬的身影。相信,只要長白山文化在流佈,人們還會不斷地去探尋他們的前世今生……
吉林日報社出品
策劃:姜忠孝
作者:易洪斌
編輯: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