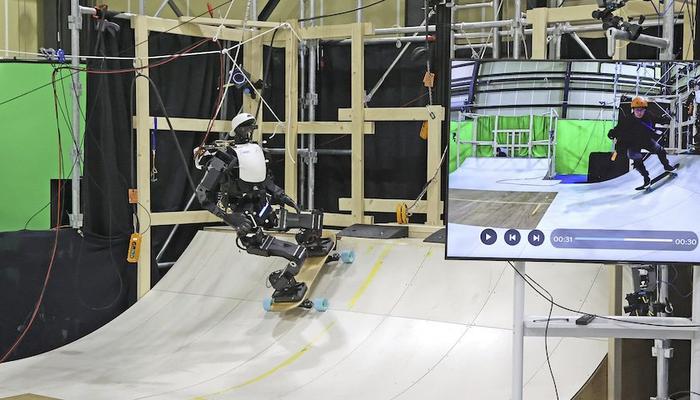书摘|知识分子的光辉道路:古斯曼为何看不起格瓦拉
本文节选自《安第斯山脉的生与死:追寻土匪、英雄和革命者的足迹》,作者:[美]金·麦夸里,译者:冯璇,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光辉道路的创立者阿维马埃尔·古斯曼·雷诺索(Abimael Guzman Reynoso)出生于1934年。他的父亲是省城里的一个小生意人,已有妻室,而他母亲则是个未婚的女佣。曾经一段时间,古斯曼的母亲就住在阿雷基帕市(Arequipa)中距离自己情人家不远的地方。这座城市位于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之上,是一座华美的殖民城市。这里的教堂和建筑都是用白色的火山浮石建造的。在古斯曼只有几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决定离开这里,于是把年幼的阿维马埃尔送到自己居住在海岸地区利马的兄弟家抚养。到古斯曼8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彻底抛弃了他,她在写给自己儿子的最后几封信中说:“我的儿子,照顾好你妈妈的孩子,因为现在只有你能照顾他了。”6换言之,从此刻开始,古斯曼就要靠自己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
所有人都说古斯曼是一个沉静、内向的人。他因为私生子的身份而一直受到别人的非难,不过他仍然是个好学生。被父母遗弃,又没有兄弟姐妹,甚至连朋友都没有的古斯曼选择用阅读来逃避现实。此外,他还很喜欢听收音机或去电影院。与此同时,古斯曼的父亲一直在阿雷基帕市经营着自己的会计业务,而且依然在外面拈花惹草。除了和自己妻子的婚生子女之外,他和不同的女人生下的私生子至少还有十个以上。古斯曼和这个遥远的父亲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偶尔会通信。到古斯曼15岁的时候,他的书信最终还是被父亲的妻子发现了。不过,这位妻子不但没有毁掉信件,反而邀请自己丈夫的私生子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后来她对那些和古斯曼同父异母的其他私生子兄弟姐妹也都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在阿雷基帕市,古斯曼入读了一所私人学校,为人处事也一直很低调。他喜欢下棋、读书,偶尔踢踢足球,不过总体来说他是个羞涩的人,总是把感受藏在自己心底。每当参加集体活动时,他给人的印象都是巴不得别人忽视他的存在。如他同父异母的姐妹苏珊娜(Susana)后来说的那样:“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表现得]像是他认为……[他父亲的]家人会对他感到失望或是会把他当作一个恨不得摆脱的麻烦。”
1950年,古斯曼16岁的时候,秘鲁正处于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General Manual Odría)的独裁统治下。附近一个学院(colegio)的学生指控他们的校长挪用了学校的基金,于是封锁了学校举行抗议。市长随即下令出动坦克进行军事攻击,而学生们则投掷砖块作为回击。学生中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袭击中受伤,他的同学们把他抬到了阿雷基帕市的中央广场。大批的学生迅速地集中到此并进入教堂,敲响了铜钟。市民们也开始汇集到广场上,有些人攻占了兵营,有些人从教堂二层推下了一架钢琴,砸到了广场上。之后人们又点火将兵营烧成了平地。受够了两年来的独裁统治,抗议者们宣布脱离政府的管辖,并开始选举他们自己的省级议会。至此,最初的校园抗议已经升级成为反对秘鲁政府的暴动。
独裁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马上派出军队包围了城市并向广场进军。当抗议者派出代表团前来谈判时,军队却开火了。接着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屠杀,士兵们射杀了大量抗议者并将幸存者关进了监狱。暴动发生时,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他的家人就住在几个街区之外。后来他回忆说:
当时流了很多血……我看到了人民的战斗精神……人民无可抑制的怒火支持着他们反抗屠杀青年的暴行。我还看到他们是如何与军队战斗的,逼迫军队不得不退回自己的营地。政府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集更多兵力来镇压这里的人民。这次事件……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因为由此……我懂得了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无论多么强大的反动派都会感到惧怕。
这次暴动四年后,古斯曼被阿雷基帕市的圣奥古斯丁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Agustín)录取。这个肤色白皙、有黑色卷发、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邻居家美丽的女儿,她的父母都是学校的教师。据别人说,古斯曼陷入了情网,而女方也对他报以同样的深情。不过,和古斯曼最喜欢的那些好莱坞电影不同,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并没有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121女方虽然年轻貌美,但是家里没什么钱。古斯曼虽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产阶级生意人的儿子,但他毕竟不是婚生的。女方父母担心女儿的追求者将来继承不到一分钱,坚持让女儿把眼光放高些,于是事情发展成了一部秘鲁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古斯曼最后一次见到他心爱的姑娘是在他一个亲戚的婚礼上。姑娘和她的父母一起出席,虽然他们禁止她见他,但是古斯曼一直在等待时机邀请她跳舞。女方的父亲虽然心里不赞成,但还是看着两人进入了舞池中央。他们一起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她靠近古斯曼跟他说了一句什么。根据古斯曼的姐妹苏珊娜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突然不跳了,曲子才到一半她就停住了舞步,而他则不得不礼貌地离开了……舞会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站在一面[全身]穿衣镜前,然后用尽全力把镜子踹了个粉碎。”自此古斯曼再也没提过那个姑娘的名字。苏珊娜后来写道:
这个姑娘……实际上决定了当今秘鲁的历史。在那时……[阿维马埃尔]仍然算半个天主教徒,如果他们结婚了,也许他现在就会成为一个有钱的律师。他真的非常爱她,一定会满足她和他们的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失去她之后,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思考他所谓的“生命的不公”上。他对自己失去了兴趣,不再在乎自己的安危或幸福。人们说他在学校里成了左派,但是我相信其实他从童年时期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左派了。索菲娅(Sofía)是唯一能让他离开那条道路的人,但是她不能或是不愿意那样做。因为如果她真的想要和他在一起的话,她父母的命令根本影响不了他们。人生中的事往往就是这样!
最终将领导游击队战争,并让秘鲁陷入分裂的古斯曼此时只是一个伤心失意的单身汉。于是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到了他所学习的两个专业中:法律和哲学。122秘鲁此时仍处于曼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的统治下。像其他很多学生一样,古斯曼加入了共产党,开始成为一名兼具工人和知识分子双重属性的基层革命者。然而作为一名学习哲学的学生,古斯曼和其他大部分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深入研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德国哲学家撰写的著作。古斯曼在27岁时获得了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和一个法学学位。他两个专业的毕业论文题目分别是《论康德的空间理论》(The Bourgeois-Democratic State)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About the Kantian Theory of Space)。后一篇的标题就明确地证实了古斯曼此时已经成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这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的导师,同样是阿雷基帕人的哲学教授米格尔·安赫尔·罗德里格斯·里瓦斯(Miguel Angel Rodríguez Rivas)说,“古斯曼是最高水平的理论家。”
阿维马埃尔·古斯曼28岁时接受了到阿亚库乔(Ayacucho)做一名哲学教授的工作。这座小城只有1.7万人口,是安第斯山脉上的一个省级首府,该省也是整个秘鲁最贫困的省份之一。当地大学里的学生大多是说盖丘亚语的农民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在附近的乡村里种田,但他们辛辛苦苦耕种的土地并不归他们所有。古斯曼是在1962年接受这份工作的。那时距离西班牙征服者野蛮占领秘鲁大约已经过了四个世纪,而秘鲁的社会状况还是:全国0.1%的人口拥有60%的可耕种土地,25%的人口没有上过小学,只有30%的人口进入了中学,还有30%的人口是彻底的文盲。全国25个大区之一的阿亚库乔大区的情况则要比这个数字更加严峻。古斯曼作为一个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儿子,有机会接受了高等教育,所以当他第一次接触到秘鲁农村的农民时,后者的处境让他深受震撼。后来他写道:
现实扩展了我的眼界,也拓宽了我的思维……阿亚库乔的农民们非常贫困……我看到人们像奴隶一样在农场里工作,还要自己准备食物。我见到的有些人要走几十公里、自备食物来工作。我看到了农民们的挣扎和他们受到的严重剥削。我能够感受到贫苦的秘鲁农民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中奋斗和工作的艰难处境。但是他们并没有湮灭在历史中,相反他们不畏任何困难,充满活力地奋斗至今。他们才是这片大地的基石。在我眼中,农民就是秘鲁的基石。12古斯曼的学生就是这些农民的儿女,他们也是克服了各种困难才能最终进入大学的。
古斯曼很快就开始教授他们希腊语和德国哲学的课程,尤其是他最喜爱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古斯曼毫无疑问是对哲学充满热情的,他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对教师的工作也同样充满热情。正如几年前一样,参加哲学讨论再一次让古斯曼从自己封闭的外壳中走了出来。渐渐地,年轻的教授身边聚集起了一批追随者,他们进行的非正式的讨论会常常持续到深夜。古斯曼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农村学校里的教师,他们又把从自己的教授那里学来的东西传授给了小教室中那些穿便鞋、说盖丘亚语的学生们。马克思的哲学就这样渐渐地传到了大学以外,就好像在羊毛上滴一滴颜色,它就会迅速洇开一样,马克思主义就这样传遍了地势崎岖不平的阿亚库乔。
在业余时间里,古斯曼全身心地投入秘鲁共产党的活动,已经逐步晋升到了秘书长的职务。虽然他对哲学教授的工作仍然全心投入,但是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终极问题”:“哲学家只是去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马克思写下的,他在分析了历史和社会之后得出了暴力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的必经之路。然而马克思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流放中,因此他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直到马克思去世之后,列宁、毛泽东等人才实质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了成功。
蛰伏在安第斯山脉上海拔9000英尺的阿亚库乔的这段时期里,古斯曼渐渐认识到他的使命已经不再仅仅是传授,而是行动——要把让他如此着迷的哲学贯彻到行动中去。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马克思的关于社会形式“必将”从原始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只是一种理论。但对于古斯曼而言,马克思的观点已经成为他脑海中人类发展的“自然法则”。如果一个真正的信徒的定义是“坚定地持有某种信念,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心怀崇拜”,那么古斯曼显然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像马克思一样,古斯曼开始相信一个光辉灿烂、没有国家存在的未来在等着人类去实现,哪怕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要依靠枪炮。古斯曼后来宣称:
我们要记住……只有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才是悲观消极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永远是乐观的,因为未来是我们的——历史已经注定,我们要做的就是勇往直前地继续我们的事业。
古斯曼相信,秘鲁的贫穷是具有地方特性的,因为从西班牙征服者来到这里后,资产阶级就占有了一切,并一直剥削着劳苦大众。他认为消除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然而,从教授转变为革命领导人对于古斯曼而言,也是一条精神上的“卢比孔河”——跨过去就没有回头路了,这对于他的人生是有巨大影响的。毕竟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是一位守法的工薪阶层,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他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继续向大批的学生教授他最热爱的马克思主义。也许将来有一天,他的学生中会出现一位革命领导人来把安第斯山脉推进革命的烈焰中。然而事实是从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的某个时间起,古斯曼渐渐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位大学教授,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位未来的革命领导人。他身边也已经有一小拨学生不再是单纯地相信他所教授的主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古斯曼这个人。古斯曼最终认识到,如果自己真的相信自己所教授的一切,那么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应当是把他的话——也就是他的信仰——付诸行动。
“知识分子——我怎么看待他们?”古斯曼后来说,显然是为了划清自己和那些只说不做的哲学家的界限,“……他们能做的只有说教。似乎对这些人而言,说说就足够了……[然而]不管你说得多么正确,话语总是很容易被击碎的。”
1965年,当古斯曼还在阿亚库乔过着平静的生活时,秘鲁爆发了一次起义。两支游击队开始袭击安第斯山脉多个地区的大庄园和警察站。这两支游击队属于一个名为“左派革命运动”(MIR)的组织,这个组织认同切·格瓦拉的理论,相信仅凭一支武装的革命者(foco)小队就可以获得当地贫苦农民的支持,从而发动群众战争。然而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成员主要都是来自利马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学生和职业人员,他们既不会说盖丘亚语,也没有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生活的经验。相反,秘鲁的武装军队则接受了美国反暴动专业指导和他们提供的汽油弹,所以很快就消灭了这两支游击队,并杀死了他们的领导人。
两年之后,也就是1967年,切·格瓦拉亲自在玻利维亚尝试了他的革命理论,主要依靠一小拨古巴革命者和几个在1965年革命失败后幸存下来的秘鲁人。然而同之前以利马为基地的中产阶级游击队一样,切·格瓦拉的队伍也没能成功征召到哪怕一个农民加入他们。切·格瓦拉和他的队伍根本不了解周围的文化环境,也没有花时间或是只花了一点点时间动员当地人民参与武装斗争。结果就是当地人把这些古巴人看作外国人,而且很快就开始向当局通风报信。和对付秘鲁游击队的策略一样,玻利维亚的军队很快就使切·格瓦拉的队伍被当地人民所孤立,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并消灭了所有的力量。古斯曼这个执着的游击队运动研究者仔细地研究了前述这些起义的结果,后来他轻蔑地称切·格瓦拉无果的努力是“业余游击队”的事业。
切·格瓦拉的失败实际上凸显了古斯曼已经意识到并坚决想要避免的几个错误。显然,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是了解当地情况与文化的游击队员。把外来的游击队员硬插进来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了。动员当地人民参与游击战争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在开第一枪之前就要先抓住农民的“心灵和思想”。古斯曼的结论是:只有在给当地农民做好政治准备之后才能开展武装革命。因此,古斯曼耐心地进行着他让马克思主义理念缓缓传遍整个阿亚库乔地区的努力,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努力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到1976年,做了14年大学教授的古斯曼已经教出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这一年他从学校辞职,开始全心全意地筹划他的革命运动。又过了四年,在1980年发起内战的前夕,在只有一小拨未来的革命家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古斯曼忠告他们要坚强地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未来:
同志们,我们即将迎来巨大的破裂……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主人公:我们是负责任的、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我们将揭开新的黎明……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所有的劳动者,我们整个国家的国民,我们的党和党委会、基层人员和领导者们:20世纪所有伟大的运动将在历史的这一刻达到巅峰。预言即将实现,未来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盼望的未来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实现,为了人民,为了无产阶级,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付出多少努力就会实现多少功绩……未来是靠枪炮打出来的!武装革命已经开始了!
不到一个月,在1980年5月17日这一天,也是在古斯曼开始精心培养他的学生们树立战斗思想将近20年之后,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和他的几百个追随者一起发动了他们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