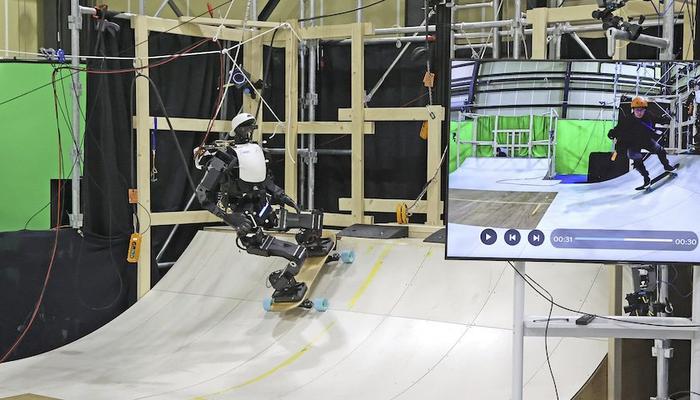書摘|知識分子的光輝道路:古斯曼爲何看不起格瓦拉
本文節選自《安第斯山脈的生與死:追尋土匪、英雄和革命者的足跡》,作者:[美]金·麥誇裏,譯者:馮璇,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光輝道路的創立者阿維馬埃爾·古斯曼·雷諾索(Abimael Guzman Reynoso)出生於1934年。他的父親是省城裏的一個小生意人,已有妻室,而他母親則是個未婚的女傭。曾經一段時間,古斯曼的母親就住在阿雷基帕市(Arequipa)中距離自己情人家不遠的地方。這座城市位於祕魯南部的安第斯山脈之上,是一座華美的殖民城市。這裏的教堂和建築都是用白色的火山浮石建造的。在古斯曼只有幾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決定離開這裏,於是把年幼的阿維馬埃爾送到自己居住在海岸地區利馬的兄弟家撫養。到古斯曼8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已經徹底拋棄了他,她在寫給自己兒子的最後幾封信中說:“我的兒子,照顧好你媽媽的孩子,因爲現在只有你能照顧他了。”6換言之,從此刻開始,古斯曼就要靠自己了。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母親。
所有人都說古斯曼是一個沉靜、內向的人。他因爲私生子的身份而一直受到別人的非難,不過他仍然是個好學生。被父母遺棄,又沒有兄弟姐妹,甚至連朋友都沒有的古斯曼選擇用閱讀來逃避現實。此外,他還很喜歡聽收音機或去電影院。與此同時,古斯曼的父親一直在阿雷基帕市經營着自己的會計業務,而且依然在外面拈花惹草。除了和自己妻子的婚生子女之外,他和不同的女人生下的私生子至少還有十個以上。古斯曼和這個遙遠的父親之間一直保持着聯繫,他們偶爾會通信。到古斯曼15歲的時候,他的書信最終還是被父親的妻子發現了。不過,這位妻子不但沒有毀掉信件,反而邀請自己丈夫的私生子來和他們一起生活,後來她對那些和古斯曼同父異母的其他私生子兄弟姐妹也都發出了這樣的邀請。
在阿雷基帕市,古斯曼入讀了一所私人學校,爲人處事也一直很低調。他喜歡下棋、讀書,偶爾踢踢足球,不過總體來說他是個羞澀的人,總是把感受藏在自己心底。每當參加集體活動時,他給人的印象都是巴不得別人忽視他的存在。如他同父異母的姐妹蘇珊娜(Susana)後來說的那樣:“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表現得]像是他認爲……[他父親的]家人會對他感到失望或是會把他當作一個恨不得擺脫的麻煩。”
1950年,古斯曼16歲的時候,祕魯正處於曼努埃爾·奧德里亞將軍(General Manual Odría)的獨裁統治下。附近一個學院(colegio)的學生指控他們的校長挪用了學校的基金,於是封鎖了學校舉行抗議。市長隨即下令出動坦克進行軍事攻擊,而學生們則投擲磚塊作爲回擊。學生中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員在襲擊中受傷,他的同學們把他抬到了阿雷基帕市的中央廣場。大批的學生迅速地集中到此並進入教堂,敲響了銅鐘。市民們也開始彙集到廣場上,有些人攻佔了兵營,有些人從教堂二層推下了一架鋼琴,砸到了廣場上。之後人們又點火將兵營燒成了平地。受夠了兩年來的獨裁統治,抗議者們宣佈脫離政府的管轄,並開始選舉他們自己的省級議會。至此,最初的校園抗議已經升級成爲反對祕魯政府的暴動。
獨裁政府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馬上派出軍隊包圍了城市並向廣場進軍。當抗議者派出代表團前來談判時,軍隊卻開火了。接着又發生了更大規模的屠殺,士兵們射殺了大量抗議者並將倖存者關進了監獄。暴動發生時,阿維馬埃爾·古斯曼和他的家人就住在幾個街區之外。後來他回憶說:
當時流了很多血……我看到了人民的戰鬥精神……人民無可抑制的怒火支持着他們反抗屠殺青年的暴行。我還看到他們是如何與軍隊戰鬥的,逼迫軍隊不得不退回自己的營地。政府不得不從其他地方調集更多兵力來鎮壓這裏的人民。這次事件……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裏。因爲由此……我懂得了只要人民團結起來……無論多麼強大的反動派都會感到懼怕。
這次暴動四年後,古斯曼被阿雷基帕市的聖奧古斯丁國立大學(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Agustín)錄取。這個膚色白皙、有黑色捲髮、戴着眼鏡的年輕人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初戀——鄰居家美麗的女兒,她的父母都是學校的教師。據別人說,古斯曼陷入了情網,而女方也對他報以同樣的深情。不過,和古斯曼最喜歡的那些好萊塢電影不同,這兩個人的愛情故事並沒有迎來一個美好的結局。121女方雖然年輕貌美,但是家裏沒什麼錢。古斯曼雖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產階級生意人的兒子,但他畢竟不是婚生的。女方父母擔心女兒的追求者將來繼承不到一分錢,堅持讓女兒把眼光放高些,於是事情發展成了一部祕魯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古斯曼最後一次見到他心愛的姑娘是在他一個親戚的婚禮上。姑娘和她的父母一起出席,雖然他們禁止她見他,但是古斯曼一直在等待時機邀請她跳舞。女方的父親雖然心裏不贊成,但還是看着兩人進入了舞池中央。他們一起跳了一會兒舞,然後她靠近古斯曼跟他說了一句什麼。根據古斯曼的姐妹蘇珊娜說:“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她突然不跳了,曲子纔到一半她就停住了舞步,而他則不得不禮貌地離開了……舞會結束後,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站在一面[全身]穿衣鏡前,然後用盡全力把鏡子踹了個粉碎。”自此古斯曼再也沒提過那個姑娘的名字。蘇珊娜後來寫道:
這個姑娘……實際上決定了當今祕魯的歷史。在那時……[阿維馬埃爾]仍然算半個天主教徒,如果他們結婚了,也許他現在就會成爲一個有錢的律師。他真的非常愛她,一定會滿足她和他們的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失去她之後,他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思考他所謂的“生命的不公”上。他對自己失去了興趣,不再在乎自己的安危或幸福。人們說他在學校裏成了左派,但是我相信其實他從童年時期開始就已經是一個左派了。索菲婭(Sofía)是唯一能讓他離開那條道路的人,但是她不能或是不願意那樣做。因爲如果她真的想要和他在一起的話,她父母的命令根本影響不了他們。人生中的事往往就是這樣!
最終將領導遊擊隊戰爭,並讓祕魯陷入分裂的古斯曼此時只是一個傷心失意的單身漢。於是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到了他所學習的兩個專業中:法律和哲學。122祕魯此時仍處於曼努埃爾·奧德里亞將軍的統治下。像其他很多學生一樣,古斯曼加入了共產黨,開始成爲一名兼具工人和知識分子雙重屬性的基層革命者。然而作爲一名學習哲學的學生,古斯曼和其他大部分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深入研讀了許多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德國哲學家撰寫的著作。古斯曼在27歲時獲得了一個哲學博士學位和一個法學學位。他兩個專業的畢業論文題目分別是《論康德的空間理論》(The Bourgeois-Democratic State)和《資產階級民主國家》(About the Kantian Theory of Space)。後一篇的標題就明確地證實了古斯曼此時已經成了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是這個人才輩出的年代裏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他的導師,同樣是阿雷基帕人的哲學教授米格爾·安赫爾·羅德里格斯·裏瓦斯(Miguel Angel Rodríguez Rivas)說,“古斯曼是最高水平的理論家。”
阿維馬埃爾·古斯曼28歲時接受了到阿亞庫喬(Ayacucho)做一名哲學教授的工作。這座小城只有1.7萬人口,是安第斯山脈上的一個省級首府,該省也是整個祕魯最貧困的省份之一。當地大學裏的學生大多是說蓋丘亞語的農民家的孩子,他們的父母就在附近的鄉村裏種田,但他們辛辛苦苦耕種的土地並不歸他們所有。古斯曼是在1962年接受這份工作的。那時距離西班牙征服者野蠻佔領祕魯大約已經過了四個世紀,而祕魯的社會狀況還是:全國0.1%的人口擁有60%的可耕種土地,25%的人口沒有上過小學,只有30%的人口進入了中學,還有30%的人口是徹底的文盲。全國25個大區之一的阿亞庫喬大區的情況則要比這個數字更加嚴峻。古斯曼作爲一個小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兒子,有機會接受了高等教育,所以當他第一次接觸到祕魯農村的農民時,後者的處境讓他深受震撼。後來他寫道:
現實擴展了我的眼界,也拓寬了我的思維……阿亞庫喬的農民們非常貧困……我看到人們像奴隸一樣在農場裏工作,還要自己準備食物。我見到的有些人要走幾十公里、自備食物來工作。我看到了農民們的掙扎和他們受到的嚴重剝削。我能夠感受到貧苦的祕魯農民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在社會中奮鬥和工作的艱難處境。但是他們並沒有湮滅在歷史中,相反他們不畏任何困難,充滿活力地奮鬥至今。他們纔是這片大地的基石。在我眼中,農民就是祕魯的基石。12古斯曼的學生就是這些農民的兒女,他們也是克服了各種困難才能最終進入大學的。
古斯曼很快就開始教授他們希臘語和德國哲學的課程,尤其是他最喜愛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馬克思的思想。古斯曼毫無疑問是對哲學充滿熱情的,他的學生們很快發現他對教師的工作也同樣充滿熱情。正如幾年前一樣,參加哲學討論再一次讓古斯曼從自己封閉的外殼中走了出來。漸漸地,年輕的教授身邊聚集起了一批追隨者,他們進行的非正式的討論會常常持續到深夜。古斯曼的很多學生後來都成爲農村學校裏的教師,他們又把從自己的教授那裏學來的東西傳授給了小教室中那些穿便鞋、說蓋丘亞語的學生們。馬克思的哲學就這樣漸漸地傳到了大學以外,就好像在羊毛上滴一滴顏色,它就會迅速洇開一樣,馬克思主義就這樣傳遍了地勢崎嶇不平的阿亞庫喬。
在業餘時間裏,古斯曼全身心地投入祕魯共產黨的活動,已經逐步晉升到了祕書長的職務。雖然他對哲學教授的工作仍然全心投入,但是他不可避免地面臨着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終極問題”:“哲學家只是去解釋世界……關鍵在於改變世界。”這正是馬克思寫下的,他在分析了歷史和社會之後得出了暴力革命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烏托邦”的必經之路。然而馬克思本人一生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流放中,因此他所進行的革命戰爭是理論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直到馬克思去世之後,列寧、毛澤東等人才實質性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並獲得了成功。
蟄伏在安第斯山脈上海拔9000英尺的阿亞庫喬的這段時期裏,古斯曼漸漸認識到他的使命已經不再僅僅是傳授,而是行動——要把讓他如此着迷的哲學貫徹到行動中去。對於大多數學者而言,馬克思的關於社會形式“必將”從原始社會進化到資本主義社會最終進化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只是一種理論。但對於古斯曼而言,馬克思的觀點已經成爲他腦海中人類發展的“自然法則”。如果一個真正的信徒的定義是“堅定地持有某種信念,對現狀不滿,對未來心懷崇拜”,那麼古斯曼顯然就是一個真正的信徒。像馬克思一樣,古斯曼開始相信一個光輝燦爛、沒有國家存在的未來在等着人類去實現,哪怕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要依靠槍炮。古斯曼後來宣稱:
我們要記住……只有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纔是悲觀消極的,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者永遠是樂觀的,因爲未來是我們的——歷史已經註定,我們要做的就是勇往直前地繼續我們的事業。
古斯曼相信,祕魯的貧窮是具有地方特性的,因爲從西班牙征服者來到這裏後,資產階級就佔有了一切,並一直剝削着勞苦大衆。他認爲消除貧困的唯一辦法就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然而,從教授轉變爲革命領導人對於古斯曼而言,也是一條精神上的“盧比孔河”——跨過去就沒有回頭路了,這對於他的人生是有巨大影響的。畢竟他是一位大學教授,是一位守法的工薪階層,是無產階級的一員,他完全可以安安穩穩地繼續向大批的學生教授他最熱愛的馬克思主義。也許將來有一天,他的學生中會出現一位革命領導人來把安第斯山脈推進革命的烈焰中。然而事實是從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的某個時間起,古斯曼漸漸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位大學教授,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位未來的革命領導人。他身邊也已經有一小撥學生不再是單純地相信他所教授的主義,更重要的是他們同樣堅定地相信古斯曼這個人。古斯曼最終認識到,如果自己真的相信自己所教授的一切,那麼唯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應當是把他的話——也就是他的信仰——付諸行動。
“知識分子——我怎麼看待他們?”古斯曼後來說,顯然是爲了劃清自己和那些只說不做的哲學家的界限,“……他們能做的只有說教。似乎對這些人而言,說說就足夠了……[然而]不管你說得多麼正確,話語總是很容易被擊碎的。”
1965年,當古斯曼還在阿亞庫喬過着平靜的生活時,祕魯爆發了一次起義。兩支游擊隊開始襲擊安第斯山脈多個地區的大莊園和警察站。這兩支游擊隊屬於一個名爲“左派革命運動”(MIR)的組織,這個組織認同切·格瓦拉的理論,相信僅憑一支武裝的革命者(foco)小隊就可以獲得當地貧苦農民的支持,從而發動羣衆戰爭。然而左派革命運動組織的成員主要都是來自利馬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學生和職業人員,他們既不會說蓋丘亞語,也沒有在安第斯山脈地區生活的經驗。相反,祕魯的武裝軍隊則接受了美國反暴動專業指導和他們提供的汽油彈,所以很快就消滅了這兩支游擊隊,並殺死了他們的領導人。
兩年之後,也就是1967年,切·格瓦拉親自在玻利維亞嘗試了他的革命理論,主要依靠一小撥古巴革命者和幾個在1965年革命失敗後倖存下來的祕魯人。然而同之前以利馬爲基地的中產階級游擊隊一樣,切·格瓦拉的隊伍也沒能成功徵召到哪怕一個農民加入他們。切·格瓦拉和他的隊伍根本不瞭解周圍的文化環境,也沒有花時間或是隻花了一點點時間動員當地人民參與武裝鬥爭。結果就是當地人把這些古巴人看作外國人,而且很快就開始向當局通風報信。和對付祕魯游擊隊的策略一樣,玻利維亞的軍隊很快就使切·格瓦拉的隊伍被當地人民所孤立,然後再將他們一網打盡並消滅了所有的力量。古斯曼這個執着的游擊隊運動研究者仔細地研究了前述這些起義的結果,後來他輕蔑地稱切·格瓦拉無果的努力是“業餘游擊隊”的事業。
切·格瓦拉的失敗實際上凸顯了古斯曼已經意識到並堅決想要避免的幾個錯誤。顯然,革命運動的基礎必須是瞭解當地情況與文化的游擊隊員。把外來的游擊隊員硬插進來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大錯特錯的了。動員當地人民參與游擊戰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點——在開第一槍之前就要先抓住農民的“心靈和思想”。古斯曼的結論是:只有在給當地農民做好政治準備之後才能開展武裝革命。因此,古斯曼耐心地進行着他讓馬克思主義理念緩緩傳遍整個阿亞庫喬地區的努力,他相信總有一天這些努力會結出豐碩的果實。到1976年,做了14年大學教授的古斯曼已經教出了成千上萬的學生。這一年他從學校辭職,開始全心全意地籌劃他的革命運動。又過了四年,在1980年發起內戰的前夕,在只有一小撥未來的革命家出席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古斯曼忠告他們要堅強地面對擺在他們面前的未來:
同志們,我們即將迎來巨大的破裂……這個時刻已經到來……我們將成爲歷史的主人公:我們是負責任的、有組織的、武裝起來的……我們將揭開新的黎明……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人民,所有的勞動者,我們整個國家的國民,我們的黨和黨委會、基層人員和領導者們:20世紀所有偉大的運動將在歷史的這一刻達到巔峯。預言即將實現,未來在我們面前展開……我們盼望的未來需要我們用生命來實現,爲了人民,爲了無產階級,爲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志們,我們付出多少努力就會實現多少功績……未來是靠槍炮打出來的!武裝革命已經開始了!
不到一個月,在1980年5月17日這一天,也是在古斯曼開始精心培養他的學生們樹立戰鬥思想將近20年之後,阿維馬埃爾·古斯曼和他的幾百個追隨者一起發動了他們的革命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