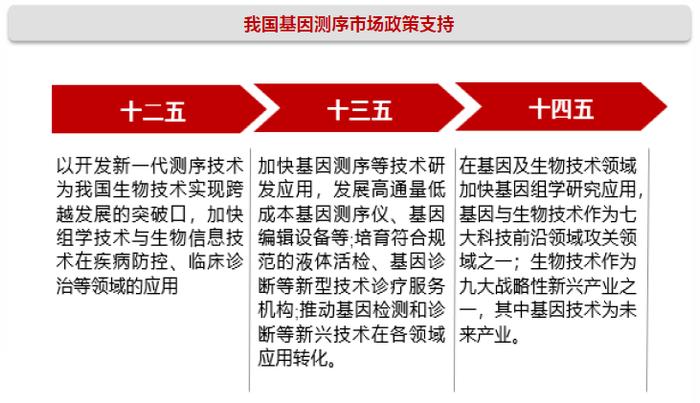飽和式論文:爲了發論文而發論文......
看過《流浪地球》的人都知道一個詞,
那就是飽和式救援,
意思是出動足夠數量的救援隊,保證有至少一支救援隊到達目的地,從而進行有效的救援。
也就是說,從第一個救援隊到達之後,後面的救援隊就都是飽和式救援。
飽和式科研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的科研模式就是:面對一個熱門的研究方向,無數人一次又一次的蹭熱點,發各種論文,誰發的論文分高,就是誰的成果,
剩下的人就是炮灰。
同一個idea,一個組幾個博士/碩士一起做,誰做出來誰發paper,
剩下的就是被飽和的那個人。
更爲嚴峻的是,
不管你有沒有認真學習認真搞研究,你的畢業小論文還是有要求的,
所以,那就湊唄,
生搬硬湊,沒有研究也要發論文,
好一點的,強行找一個完全沒什麼實際意義的方向去搞,
差一點的,甚至會直接自己編造數據或者抄襲論文,
這種“論文”,
只會成爲一個個沒有用的數據,成爲科學大廈裏無人問津的“垃圾”。
“中國式科研” 讓人擔心
“我以前曾經預測,中國會在2020年論文數超過美國,沒想到我們提前完成了。”
這是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上,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原副校長施一公先生說的。
面對這項數據,爲何施一公臉上沒有一絲驕傲,反倒是一臉擔憂。
確實,
論文多並不代表研究水平高,
飽和式救援是有意義的,
只要有一支救援隊達到目的地就可以了,
大部分救援隊會遭遇意外,幸運的無功而返,不幸的全軍覆沒。
但是他們的犧牲是有意義,當足夠多的發動機被重啓,人類就能得救,這值得付出任何代價。
但被飽和式科研犧牲掉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誰也不知道,誰會成爲被飽和的那個人。
M理論之父、超弦理論的“教皇”愛德華·威頓有次申請經費時,
基金委員會的人問他: "每年我們國家會新產生出多少弦論方向的物理學家?"
威頓教授: "估計100人吧。"
基金委: "那我們需要多少弦論方向的物理學家? "
威頓教授: "一個就夠了。"
基金委: "那我們爲什麼需要培養這麼多? "
威頓教授: "因爲我們不知道要去掉哪99個。
科研之路本不存在飽和,發論文的人多了,也就“飽和”了。
其實,學霸姐姐並不認爲我們現在的科學研究已經飽和了,
在《流浪地球》中,飽和式救援是有目標的,有方向的,大家從不同地方出發,向同一個點匯聚。
科研呢,科研總是孤獨的,最起碼是迷茫的,
你沒有方向,你要向未知出發,
你要彎彎曲曲地探索人類知識的邊境,
你要在一片區域猶猶豫豫反反覆覆地打轉直到找到接近中心的最短路徑。
所以科研纔要強調自由和創新,科研的核心也就是創新。
創新就意味着不走尋常路,在科研人員對某方向感興趣,並且提出了有理有據,能夠自圓其說的理論和實踐路線時,就應該讓其進行嘗試。
從這個角度出發,在他選擇的方向上,他註定是孤單單的一個人,
不可能存在所謂的飽和式科研這種方式。
然而,在大環境的影響下,
在論文、期刊、影響因子等等的衡量標準下,
科研工作當中,我們只認同the first,或者是the best,
所以,讓人覺得其它人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給人的感覺是很多科研工作已經飽和了,其實並不是。
真正有意義的方向不管最後有沒有成功發表論文都有借鑑意義。
然而,還有一種飽和是——孤注一擲、不計後果
比如完全沒有基礎理論方向的研究,
導師讓你從頭開始搭建,
不計人力物力,在有限的技術基礎上,硬堆出沒有實際意義的成果,發了一堆所謂的論文,
結果就是某些大教授勝利,學生全都成爲炮灰。
學霸姐姐想說,在現在的條件下,
飽和式湊論文科研是對廣大科研人員的一種極大的浪費,阻礙了科研工作的正常發展。
我們作爲科研人員,
應該要做的是修補科學大廈的邊邊角角,而不是成爲這座大廈的蛀蟲。
多做有用的研究,少發灌水的論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