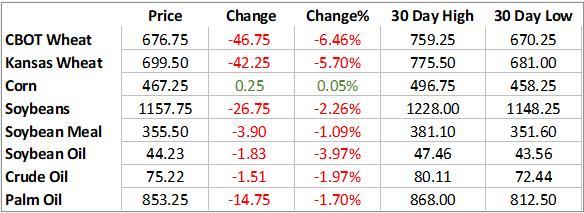我要彻底抛弃故乡 | 小青
搁 浅
题 记:
在西湖边走了十几年,在这个秋天里渐渐抛弃了故乡的底色。桂花和龙井相伴的气息,渐渐让我忘却了记忆深处的一些味道。仔细回想,那是什么味道呢?夏天的雨,落在玉米田里的野坟。坟头有纸灰,腐烂的贡品,还有诡异的红红绿绿的布条,残破的旧鞋。这些被一场雨发酵之后的味道,我大约用了半生的漂泊来远离,甩干,脱轨。近闻生育政策可能放开,我应该终于彻底忘却了,却奇怪清晰地回忆起一些片段,那片我肉身原生的青纱帐和坟头。我想,写完了,就可以彻底抛弃她们了。
这篇大概会被删吧,它有点写实,又近乎迷幻。昨夜潇潇发了一个小红包,记忆里一些姊妹相依的断章又涌了上来,如深海的游鱼。
那些鱼儿从未消失过,可能一辈子不会变成飞鸟,但是就是封存在那个梦境深处,不生不灭。我说的是一片夏日的植物群,浩浩汤汤,有蒿草、野坟上开着花的蓖麻、诡异的马蹄莲,如针刺的麦芒和拔节得近乎疯狂的青纱帐,那是一个夏日,有雨。
妹妹出生后我们就躲到一个远方的亲戚家去了,那大概是我最早的旅行,远方要看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计量,妈妈月子中,不能颠簸,镇上最好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机,太抖了,于是我们坐了牛车。
对,牛车,那时不忍心,总觉得亏欠这头蹒跚而善良的牛,外婆家的牛是我小时候可以对话的神兽,一群野孩子玩不知名的游戏,我不合群,也很少出去,舅舅家的哥哥弟弟们和姨妈家讨人喜的妹妹玩鬼子来了,地道战,没有我的角色,那时他们疯跑在院子里,我去和牛对视,给他喂草,那头牛是我默契的朋友,怎么忍心给他负重呢?
我就谎称晕车。
后来的漫长年月里,我遇到一些闪烁的眼神,总是可以感触到那背后的隐晦,不可说。可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谎的呢?又是为了什么口是心非?
于是总会轻易地原谅那些掩饰时的慌乱,也许,他们的记忆里也有一头负重的牛,善良美好。
跟在车后跑,有时比车还快,我是无牵无挂的,一路遇见的是不熟悉的田野,渴了有盖着小草棚的西瓜田,路旁的小树林里有蘑菇和开粉黄色小花的野草,还会有骑着自行车卖棒冰的吆喝声飘来,那个小贩后座上绑着的盒子是用棉被包裹的,盒子打开有好闻的糖水味道,有冷气冲上来,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在我的记忆分类里,就是这样,破旧的棉被是用来包裹棒冰盒的;新的棉被是用来包裹妹妹的,棒冰很冷,婴孩温热。
婴儿是热的,在八月的田野深处,我在逃离中祈盼那些追击超生的叔叔阿姨快点离开,祈祷可以有一阵风一场雨,甚至有一朵云把我们腾空架走,否则我的妹妹要热死了。
那天妈妈交给我这个回忆起来带着神秘气息的任务,带着妹妹去田里躲远,等到天黑再回家。那时妹妹刚出生十几天。
好像一瞬间就长大了,慎重地接过婴儿包裹,还有一个奶瓶,再没有其它,妹妹很重,像一颗炸弹。和妈妈告别时我哭了,妈妈也哭。之前爸爸有教我一些句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妹妹长大后叫潇潇。
怕熟悉的田梗有人索迹追踪,躲进去穿越的是一片不熟悉的玉米田,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我是横着走的,一步一垄,那些肥大的玉米叶擦在脸上脖子上,一开始很凉快,后来就疼起来了,像碎碎的刀子。
后来读到莫言,《檀香刑》也没怎么心悸,9岁时,故乡的植物让我见识到了,世界上最柔软的力量不是滴水穿石,而是那种绵密的刀子。
元朝末年,在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孩叫朱元璋。这一天,朱元璋和小伙伴来到山上放牛。到了傍晚,他们都饿得打晃了。朱元璋就和小伙伴商量说:“我们把牛杀死一头烧着吃了。”另一个小伙伴说:“那怎么行,财主查牛的时候少了一头牛怎么交待?”朱元璋低头想想,一拍大腿说:“有了!”说罢,就要杀牛。又有一个小伙伴说:“你说说怎样对付财主?”朱元璋说:“我们把牛杀了,把牛头放在山前用石头压得谁也拽不出来。”说完,又问谁带刀了。小伙伴都说没带刀。朱元璋一看都没带刀,那怎么办呢?他寻思了一会说:“我们拿玉米叶来杀牛。”
小伙伴们都大吃一惊。其中一个问朱元璋玉米叶怎么能杀牛?朱元璋说:“你想想,人们拿玉米叶的时候,手都被划出血来。”小伙伴们都说行,就一起动手,有的按牛,有的拿玉米叶划。不一会,牛就被划死了。他们把牛烧着吃了。吃完牛,把牛头放在山前,牛尾放在山后。用石头压上就赶着牛回村了。
——《中国民间故事》
这应该是个写实的传说,因为拙朴,没有春秋史记那样肃穆,却活泼得近乎真实。后来读到这个故事我庆幸那次逃离没有自己把自己杀死,玉米叶可以杀牛,也绞杀了9岁时一部分的我。
走累了找到一处圆地坐了下来,玉米田里密不透风,闷热让人绝望,看到这样的天井似的亮光,恍惚桃源,我坐在那,妹妹在怀里睡得很香,天空上有飞鸟,旁边有一从开着紫色小花的马蹄莲,那种马蹄莲有个姐姐曾教我可以用它的梗做耳环,那是多么难得的一项手工呢,植物的丝络剪不断理还乱,左右抚弄之下就变成翠绿的环佩了,我做成了一根小项链,放在妹妹的包裹里,她们都是我要护着的珍宝;田里有好吃的小黑果子,珍珠大小,绿色的不能吃,黑色的才好吃。
后来我才知道那片圆地是一处野坟,宿主也许是无子女的孤老,也许是莫名死去的疯子傻子,也也许是早夭的孩子,聚到一处栖息。
那个午后因为有这种叫“天天”的小野果而有了一刻异乎寻常的美好,后来下雨了,夏日的雷雨轰隆隆,我又抱着妹妹躲回田里,刀子一样的叶子也挡不住雨,田垄泥泞,走一步就滑倒,只能原地等待,等待雨停,等待天黑,妹妹的包裹湿了更重,可我不能把她放下。
后来怎么走回去的在记忆里居然完全消失了,这也就成了一个谜,人在负重的时候,没把包裹放下,却把记忆搁浅了。
夜 朦 胧
据说世界上最迷人的夜总会在巴黎,有电影为证的。
故乡的一处省会有两个妙称:“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这样迥异的两处城池都成了她容颜的一部分外像,而玉米田是她的素颜,她的子宫深处的羊水,广袤得近乎荒芜的流放之地,因着近代的几场战争,居然孕育出肃穆与瑰丽双生的胚胎。
到了我青春的时候,冰城里那些俄蒙日满交错相争的烟云早已散去了,大街上夜里总是灯火阑珊,像极了古诗里的“花市灯如昼”,只是没有花,都是冰雕,那时没有暖冬,冰灯的漂亮可以燃烧几个月。
那时城市的冬天很冷,有暖气,越发显得室外的寒凉,冬天到了一切都冻得脆生生的,“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萧红的文字里这样记录着那种冷,让大地撕裂的温度。
奇怪的是那个时候,那个城市在一年的几个月内,会涌来中国最富有的一些人,男人居多,钱的味道也会燃烧成光,扑火而来各种各样讨生活的人,冰灯一样漂亮的女孩,有一些是俄式的混血,白白的皮肤,眼睛是闪着金黄色的,吸烟的样子像一首歌——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冬夜里烟火褪去的午夜之后,街上就冷得真实凛冽了,香烟和酒精的味道散去,各家铺面渐渐上了锁,上锁的小哥,扔垃圾的厨工,开夜车的司机,一群失魂落魄的影子涌上来。
这团回忆里的海藻总是黏糊糊的,时时让我忆不起那个倚在夜总会门口吸烟的女孩,她是进了即将上锁的门,还是踩了烟蒂走上了大街,我的记忆也就分成了两条路——
一条路,教堂
我们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一半融了又冻成冰的雪踩上去已经有些危险了,我们手拉着手像一对知己的朋友。
她是留学生,中文名字是我给取的,叫吴可,应了谐音,乌克兰来的。我总把那记错成波兰,因着喜欢北岛的《波兰来客》,总觉得像她连吸烟都这么诗意的人要来自波兰,乌克兰人太强势了,有历史学家说,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用了将近160余种方法对沃伦地区的波兰人进行屠杀。
乱世中人是什么东西呢?是草,乱蓬蓬的,春天来了又生出来,也除不尽;是冰,消失了依旧是水,轮回是自然的法则。可可没有父母,她说是不记得,也许是饿死了,她被教会学校收留,也就长大了。
外面太冷了,那夜我们去了教堂,走小门。教堂里有暖气,椅子上坐着聊天,应该是忏悔吧。她只对着我说话,这个教堂她很熟悉,不用光亮也能找到熟悉的椅子,她从小习惯了睡在教堂的椅子上。
人的原罪可以通过圣殿前絮语的方式清零,这大概是神对人类最宽容的救赎法门。可可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她的语言混杂,我懂不了太多。那天她是喝了一些酒,也没有遭遇什么匪夷所思的尴尬,夜总会里大多数富有的男人,尤其是中国男人,是谨慎而小心的,对于混血的外族,也就仅限于几杯酒,几首歌,几张纸币,而那夜可可的絮语中也大抵是关于她童年的一些食物,奇怪的名称,我听不懂也记不得了,我们在凌晨的暖气中醒来,薰薰然的暖,帮神父擦洗扫地,教堂是水泥地面,扫过之后再用手掸着撒水,几缕阳光进来,就有了尘埃落定的味道。
一条路,夜朦胧
她说,你过来,我带你进去,里面有床。
夜朦胧的名字是大哥取的,可可叫他“大哥”,这个称谓我从来叫不出口,他有些老,对老的前辈总是敬仰的,叫“老师”,那时不行,大哥有枪。
当时外面下着一些雪,走上楼梯的时候在放什么音乐我忘了。楼梯口的冷气在二楼转角就突然被迷幻气息的暖意层层袭来,人一下子就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很多身影在旋转的音乐声里晃来晃去,楼上传来一个很好听的声音:来三楼。
居然是一张茶桌,桌面有风水轮,小桥流水的声音,烟丝下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也是混血,坚挺的底部弯曲的鼻子,手上细绒绒的汗毛,很像狼獾的爪子,可可的大哥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定格了,二十几年过来,从没有变过。
茶桌背后有个屏风,木质的,温润厚实,穿过去就会隐约散着好闻的香气,那种奇异的香味让夜朦胧的三楼依稀似电影中的某个道场,大哥说那都是香樟木,火车皮从上海运来的,地板也都是,“你这么文气,去上海吧,杭州也行,有咱们的茶楼,火车皮把你发过去”,大哥边笑边泡茶,他笑起来很认真,让人怕。
可可不喝茶,只是在床上抽烟,那时我要写一段剧情,就问了大哥好多为什么,他说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夜朦胧是弟弟的,弟弟去年死了,就在这个茶桌后的床上,保镖偷了枪做好了就逃了,他现在就要做两件事,要把这改成茶楼,要活着等凶手落网。
大哥的混血故事,以及他的夜总会因果,一半被拍入了电视剧,叫《大雪无痕》。
后来我真的跳上了火车,来了上海。不是黑社会的车皮,是自己偷偷买的票,那种还有汽笛声的绿皮车,撕心裂肺的鸣音,那时车子过了山海关,哭着哭着就发誓,我不会再回去了。可近几年却一直很怀念故乡的雪,一场很大的雪,铺天盖地白茫茫,无始无终,躺上去就是来处也是去处,是最禅意也野性的床吧,床这个概念他妈的像雪地上的秋千,我的青春在上面摇啊摇。
那时和可可有没有第三条路呢,我确实不记得了。
萨 满 国
回忆就是把意识中的黑洞洗白吗?也许玉米田没那么可怕,野坟上并没有半只腐烂的鞋子,可可抽烟时没那么漂亮,夜朦胧的香樟木不是火车皮运来的,那么还有什么好念念不忘的,她们已经被我的回忆封神,但他们不是真正的神灵。
据说神灵曲高和寡,不喜人身的浊气,北地苦寒,冰雪把大地封印,那热乎乎的暖气熏着的屋子里,乡下人家土炕上烘着的,就是神仙的理想国了。
怎么形容那种冷呢,这冷如今是再也寻不到了,冷如果不和人发生最直接的生死关联,就只是一种温度的表达。爸爸小时候迷路过,在满天飞雪的荒野。
恢复高考后的求学特别难得,爸爸和几个兄弟步行200多公里从学校回家,快到家时下雪了,那是怎样的一场雪呢?在一个距离家十几公里的荒草甸上,一会儿风雪呼啸,就看不见路了,再一会儿,大雪淹没了脚踝,及膝,天黑的时候要及腰了。及腰的大雪不会吞没一个人,踩上去也就到小腿就可以拔出,如果有武侠小说里的功夫是可以飘行的。而更为残酷的现实是,一片荒野里,不见路也不见光,血气方刚的青年们走不动了。爸爸无数次的描述里,依旧有恐惧涌上来。
迷路了,再走不到家,雪会冻死人的。
雪冻死过人的。明永乐年的时候,京城的监狱里,锦衣卫的头目纪纲,宴请在押的犯人大才子宰相解缙。那时窗外大雪纷飞,在狱中熬过五年了,突然一顿丰盛的酒食,解缙总也明白什么意思。他大口吃菜大碗喝酒,醉成烂泥。醉了就好了,纪纲打个手势,几个衙役过来,把解缙拉了出去。
白茫茫的大雪世界,挖了个浅坑,人往里一丢,堆上雪,解缙就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了。明代真正的大才子,《永乐大典》的总编,就这么在醉乡中进入冰寒彻骨的鬼域。
爸爸和他的兄弟们在寒冷绝望中唱歌,有什么唱什么,嗓子沙哑的时候,有个奇异的幻像出现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提着红彤彤的灯笼带路,他们欣喜地跟着,像被倩女招魂的书生,不唱了,随光漫行,走着走着,就回到了镇上的家。
这个幻象在三个叔叔的回忆中都出现过,那老爷爷就是狐仙。
狐仙、黄鼠狼、神婆、神汉,还有日落后村镇上某户人家神秘飘出的招魂神曲,以混白的冰雪为底色,这个国度里的巫是神和人之间的信使,怎么通信呢?
萨满术!招魂时唱着歌的——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催开我绿色年华
炸毁树根的力量是我的毁灭者而我哑然告知弯曲的玫瑰我的青春同样被冬天的高烧压弯驱动穿透岩石之水的力量驱动我的鲜血
枯竭滔滔不绝的力量使我的血凝结而我哑然告知我的血管同样的嘴怎样吮吸那山泉
……
时间之唇蛭吸源泉
爱情滴散聚合,但沉落的血会平息她的痛楚我哑然告知一种气候的风时间怎样沿星星滴答成天堂
而我哑然告知情人的墓穴我床单上怎样蠕动着同样的蛆虫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狄兰托马斯(北岛译)
诗歌是语言的神咒,第一次听到这首翻译的诗的时候,就丝毫没有疏离感。这些意向组合起来的奇妙图腾,在冰雪中升腾出一个海市蜃楼,夭折的孩子,青纱帐里的谋杀,坟头的枯朽,乌克兰女孩的烟,大哥那双拿过枪也泡着茶的毛茸茸的手,我的故土上的生死场啊,有那么多想忘都忘不掉,想抛都抛不开的人......他们是雪国的西西弗斯,转世为人都带着一块原石,滚上去,滚下来,滚上去,滚下来......
后来听到狄兰本人朗诵的录音带,他的声音隔着电流,黑天鹅绒般浑厚低沉,颤抖顿挫,如同萨满教巫师的祈祷和诅咒,让人颤栗,让人惊悚。
他预言了我的国吗?我的雪国究竟是被那个举着灯笼的白衣狐仙,被深夜招魂的萨满祝福还是诅咒?
时间怎样沿星星滴答成天堂?没人告诉我,可可留给我一件黑色的纱裙,和写着这句话的信箴,就真的消失了,大哥也找不到她。我问过一个萨满,萨满说,她向南面,坐火车走的,去了一个有水的暖和的地方。
小青,原名孙琳琳,头号地标乡愁大版主,于文字典籍中深游浅耕,作品散见于《红蔓》、《首席》、《华亭诗稿》等。
文 | 小 青 出品|头号地标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