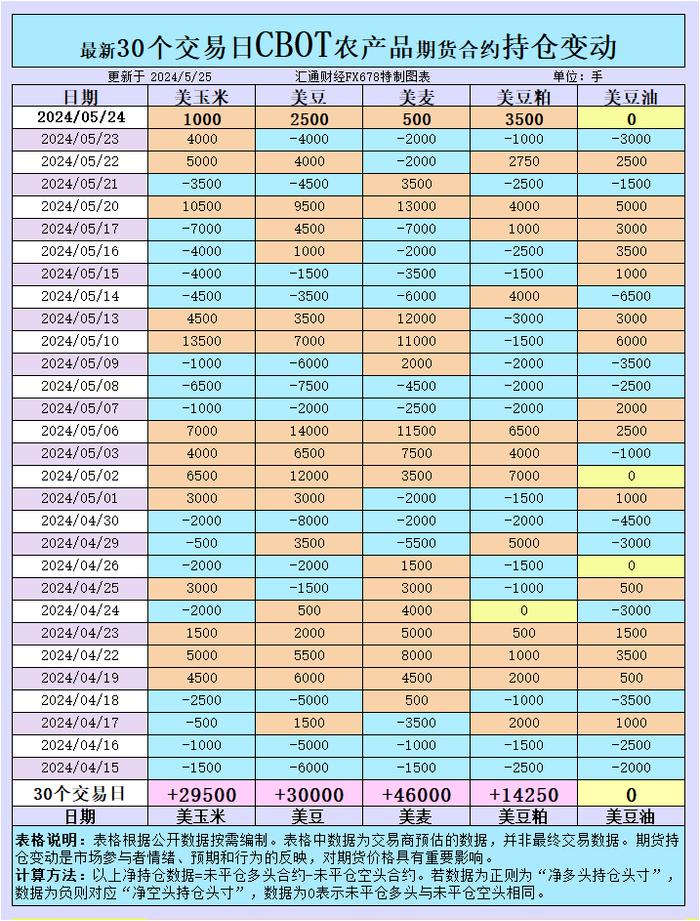我要徹底拋棄故鄉 | 小青
擱 淺
題 記:
在西湖邊走了十幾年,在這個秋天裏漸漸拋棄了故鄉的底色。桂花和龍井相伴的氣息,漸漸讓我忘卻了記憶深處的一些味道。仔細回想,那是什麼味道呢?夏天的雨,落在玉米田裏的野墳。墳頭有紙灰,腐爛的貢品,還有詭異的紅紅綠綠的布條,殘破的舊鞋。這些被一場雨發酵之後的味道,我大約用了半生的漂泊來遠離,甩幹,脫軌。近聞生育政策可能放開,我應該終於徹底忘卻了,卻奇怪清晰地回憶起一些片段,那片我肉身原生的青紗帳和墳頭。我想,寫完了,就可以徹底拋棄她們了。
這篇大概會被刪吧,它有點寫實,又近乎迷幻。昨夜瀟瀟發了一個小紅包,記憶裏一些姊妹相依的斷章又湧了上來,如深海的游魚。
那些魚兒從未消失過,可能一輩子不會變成飛鳥,但是就是封存在那個夢境深處,不生不滅。我說的是一片夏日的植物羣,浩浩湯湯,有蒿草、野墳上開着花的蓖麻、詭異的馬蹄蓮,如針刺的麥芒和拔節得近乎瘋狂的青紗帳,那是一個夏日,有雨。
妹妹出生後我們就躲到一個遠方的親戚家去了,那大概是我最早的旅行,遠方要看用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去計量,媽媽月子中,不能顛簸,鎮上最好的交通工具是拖拉機,太抖了,於是我們坐了牛車。
對,牛車,那時不忍心,總覺得虧欠這頭蹣跚而善良的牛,外婆家的牛是我小時候可以對話的神獸,一羣野孩子玩不知名的遊戲,我不合羣,也很少出去,舅舅家的哥哥弟弟們和姨媽家討人喜的妹妹玩鬼子來了,地道戰,沒有我的角色,那時他們瘋跑在院子裏,我去和牛對視,給他喂草,那頭牛是我默契的朋友,怎麼忍心給他負重呢?
我就謊稱暈車。
後來的漫長年月裏,我遇到一些閃爍的眼神,總是可以感觸到那背後的隱晦,不可說。可人是什麼時候開始說謊的呢?又是爲了什麼口是心非?
於是總會輕易地原諒那些掩飾時的慌亂,也許,他們的記憶裏也有一頭負重的牛,善良美好。
跟在車後跑,有時比車還快,我是無牽無掛的,一路遇見的是不熟悉的田野,渴了有蓋着小草棚的西瓜田,路旁的小樹林裏有蘑菇和開粉黃色小花的野草,還會有騎着自行車賣棒冰的吆喝聲飄來,那個小販後座上綁着的盒子是用棉被包裹的,盒子打開有好聞的糖水味道,有冷氣衝上來,像來自另一個世界。
在我的記憶分類裏,就是這樣,破舊的棉被是用來包裹棒冰盒的;新的棉被是用來包裹妹妹的,棒冰很冷,嬰孩溫熱。
嬰兒是熱的,在八月的田野深處,我在逃離中祈盼那些追擊超生的叔叔阿姨快點離開,祈禱可以有一陣風一場雨,甚至有一朵雲把我們騰空架走,否則我的妹妹要熱死了。
那天媽媽交給我這個回憶起來帶着神祕氣息的任務,帶着妹妹去田裏躲遠,等到天黑再回家。那時妹妹剛出生十幾天。
好像一瞬間就長大了,慎重地接過嬰兒包裹,還有一個奶瓶,再沒有其它,妹妹很重,像一顆炸彈。和媽媽告別時我哭了,媽媽也哭。之前爸爸有教我一些句子,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妹妹長大後叫瀟瀟。
怕熟悉的田梗有人索跡追蹤,躲進去穿越的是一片不熟悉的玉米田,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我是橫着走的,一步一壟,那些肥大的玉米葉擦在臉上脖子上,一開始很涼快,後來就疼起來了,像碎碎的刀子。
後來讀到莫言,《檀香刑》也沒怎麼心悸,9歲時,故鄉的植物讓我見識到了,世界上最柔軟的力量不是滴水穿石,而是那種綿密的刀子。
元朝末年,在一個村子裏,有個小孩叫朱元璋。這一天,朱元璋和小夥伴來到山上放牛。到了傍晚,他們都餓得打晃了。朱元璋就和小夥伴商量說:“我們把牛殺死一頭燒着喫了。”另一個小夥伴說:“那怎麼行,財主查牛的時候少了一頭牛怎麼交待?”朱元璋低頭想想,一拍大腿說:“有了!”說罷,就要殺牛。又有一個小夥伴說:“你說說怎樣對付財主?”朱元璋說:“我們把牛殺了,把牛頭放在山前用石頭壓得誰也拽不出來。”說完,又問誰帶刀了。小夥伴都說沒帶刀。朱元璋一看都沒帶刀,那怎麼辦呢?他尋思了一會說:“我們拿玉米葉來殺牛。”
小夥伴們都大喫一驚。其中一個問朱元璋玉米葉怎麼能殺牛?朱元璋說:“你想想,人們拿玉米葉的時候,手都被劃出血來。”小夥伴們都說行,就一起動手,有的按牛,有的拿玉米葉劃。不一會,牛就被劃死了。他們把牛燒着喫了。喫完牛,把牛頭放在山前,牛尾放在山後。用石頭壓上就趕着牛回村了。
——《中國民間故事》
這應該是個寫實的傳說,因爲拙樸,沒有春秋史記那樣肅穆,卻活潑得近乎真實。後來讀到這個故事我慶幸那次逃離沒有自己把自己殺死,玉米葉可以殺牛,也絞殺了9歲時一部分的我。
走累了找到一處圓地坐了下來,玉米田裏密不透風,悶熱讓人絕望,看到這樣的天井似的亮光,恍惚桃源,我坐在那,妹妹在懷裏睡得很香,天空上有飛鳥,旁邊有一從開着紫色小花的馬蹄蓮,那種馬蹄蓮有個姐姐曾教我可以用它的梗做耳環,那是多麼難得的一項手工呢,植物的絲絡剪不斷理還亂,左右撫弄之下就變成翠綠的環佩了,我做成了一根小項鍊,放在妹妹的包裹裏,她們都是我要護着的珍寶;田裏有好喫的小黑果子,珍珠大小,綠色的不能喫,黑色的纔好喫。
後來我才知道那片圓地是一處野墳,宿主也許是無子女的孤老,也許是莫名死去的瘋子傻子,也也許是早夭的孩子,聚到一處棲息。
那個午後因爲有這種叫“天天”的小野果而有了一刻異乎尋常的美好,後來下雨了,夏日的雷雨轟隆隆,我又抱着妹妹躲回田裏,刀子一樣的葉子也擋不住雨,田壟泥濘,走一步就滑倒,只能原地等待,等待雨停,等待天黑,妹妹的包裹溼了更重,可我不能把她放下。
後來怎麼走回去的在記憶里居然完全消失了,這也就成了一個謎,人在負重的時候,沒把包裹放下,卻把記憶擱淺了。
夜 朦 朧
據說世界上最迷人的夜總會在巴黎,有電影爲證的。
故鄉的一處省會有兩個妙稱:“東方莫斯科”,“東方小巴黎”,這樣迥異的兩處城池都成了她容顏的一部分外像,而玉米田是她的素顏,她的子宮深處的羊水,廣袤得近乎荒蕪的流放之地,因着近代的幾場戰爭,居然孕育出肅穆與瑰麗雙生的胚胎。
到了我青春的時候,冰城裏那些俄蒙日滿交錯相爭的煙雲早已散去了,大街上夜裏總是燈火闌珊,像極了古詩裏的“花市燈如晝”,只是沒有花,都是冰雕,那時沒有暖冬,冰燈的漂亮可以燃燒幾個月。
那時城市的冬天很冷,有暖氣,越發顯得室外的寒涼,冬天到了一切都凍得脆生生的,“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着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地,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嚴寒把大地凍裂了。”蕭紅的文字裏這樣記錄着那種冷,讓大地撕裂的溫度。
奇怪的是那個時候,那個城市在一年的幾個月內,會湧來中國最富有的一些人,男人居多,錢的味道也會燃燒成光,撲火而來各種各樣討生活的人,冰燈一樣漂亮的女孩,有一些是俄式的混血,白白的皮膚,眼睛是閃着金黃色的,吸菸的樣子像一首歌——
讓薔薇開出一種結果
孤獨的沙漠裏
一樣盛放的赤裸裸
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冬夜裏煙火褪去的午夜之後,街上就冷得真實凜冽了,香菸和酒精的味道散去,各家鋪面漸漸上了鎖,上鎖的小哥,扔垃圾的廚工,開夜車的司機,一羣失魂落魄的影子湧上來。
這團回憶裏的海藻總是黏糊糊的,時時讓我憶不起那個倚在夜總會門口吸菸的女孩,她是進了即將上鎖的門,還是踩了菸蒂走上了大街,我的記憶也就分成了兩條路——
一條路,教堂
我們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一半融了又凍成冰的雪踩上去已經有些危險了,我們手拉着手像一對知己的朋友。
她是留學生,中文名字是我給取的,叫吳可,應了諧音,烏克蘭來的。我總把那記錯成波蘭,因着喜歡北島的《波蘭來客》,總覺得像她連吸菸都這麼詩意的人要來自波蘭,烏克蘭人太強勢了,有歷史學家說,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用了將近160餘種方法對沃倫地區的波蘭人進行屠殺。
亂世中人是什麼東西呢?是草,亂蓬蓬的,春天來了又生出來,也除不盡;是冰,消失了依舊是水,輪迴是自然的法則。可可沒有父母,她說是不記得,也許是餓死了,她被教會學校收留,也就長大了。
外面太冷了,那夜我們去了教堂,走小門。教堂裏有暖氣,椅子上坐着聊天,應該是懺悔吧。她只對着我說話,這個教堂她很熟悉,不用光亮也能找到熟悉的椅子,她從小習慣了睡在教堂的椅子上。
人的原罪可以通過聖殿前絮語的方式清零,這大概是神對人類最寬容的救贖法門。可可說着說着就睡着了,她的語言混雜,我懂不了太多。那天她是喝了一些酒,也沒有遭遇什麼匪夷所思的尷尬,夜總會里大多數富有的男人,尤其是中國男人,是謹慎而小心的,對於混血的外族,也就僅限於幾杯酒,幾首歌,幾張紙幣,而那夜可可的絮語中也大抵是關於她童年的一些食物,奇怪的名稱,我聽不懂也記不得了,我們在凌晨的暖氣中醒來,薰薰然的暖,幫神父擦洗掃地,教堂是水泥地面,掃過之後再用手撣着撒水,幾縷陽光進來,就有了塵埃落定的味道。
一條路,夜朦朧
她說,你過來,我帶你進去,裏面有牀。
夜朦朧的名字是大哥取的,可可叫他“大哥”,這個稱謂我從來叫不出口,他有些老,對老的前輩總是敬仰的,叫“老師”,那時不行,大哥有槍。
當時外面下着一些雪,走上樓梯的時候在放什麼音樂我忘了。樓梯口的冷氣在二樓轉角就突然被迷幻氣息的暖意層層襲來,人一下子就好像來到另一個世界,很多身影在旋轉的音樂聲裏晃來晃去,樓上傳來一個很好聽的聲音:來三樓。
居然是一張茶桌,桌面有風水輪,小橋流水的聲音,菸絲下一雙鷹一樣的眼睛,也是混血,堅挺的底部彎曲的鼻子,手上細絨絨的汗毛,很像狼獾的爪子,可可的大哥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定格了,二十幾年過來,從沒有變過。
茶桌背後有個屏風,木質的,溫潤厚實,穿過去就會隱約散着好聞的香氣,那種奇異的香味讓夜朦朧的三樓依稀似電影中的某個道場,大哥說那都是香樟木,火車皮從上海運來的,地板也都是,“你這麼文氣,去上海吧,杭州也行,有咱們的茶樓,火車皮把你發過去”,大哥邊笑邊泡茶,他笑起來很認真,讓人怕。
可可不喝茶,只是在牀上抽菸,那時我要寫一段劇情,就問了大哥好多爲什麼,他說哪來那麼多爲什麼,夜朦朧是弟弟的,弟弟去年死了,就在這個茶桌後的牀上,保鏢偷了槍做好了就逃了,他現在就要做兩件事,要把這改成茶樓,要活着等兇手落網。
大哥的混血故事,以及他的夜總會因果,一半被拍入了電視劇,叫《大雪無痕》。
後來我真的跳上了火車,來了上海。不是黑社會的車皮,是自己偷偷買的票,那種還有汽笛聲的綠皮車,撕心裂肺的鳴音,那時車子過了山海關,哭着哭着就發誓,我不會再回去了。可近幾年卻一直很懷念故鄉的雪,一場很大的雪,鋪天蓋地白茫茫,無始無終,躺上去就是來處也是去處,是最禪意也野性的牀吧,牀這個概念他媽的像雪地上的鞦韆,我的青春在上面搖啊搖。
那時和可可有沒有第三條路呢,我確實不記得了。
薩 滿 國
回憶就是把意識中的黑洞洗白嗎?也許玉米田沒那麼可怕,野墳上並沒有半隻腐爛的鞋子,可可抽菸時沒那麼漂亮,夜朦朧的香樟木不是火車皮運來的,那麼還有什麼好念念不忘的,她們已經被我的回憶封神,但他們不是真正的神靈。
據說神靈曲高和寡,不喜人身的濁氣,北地苦寒,冰雪把大地封印,那熱乎乎的暖氣燻着的屋子裏,鄉下人家土炕上烘着的,就是神仙的理想國了。
怎麼形容那種冷呢,這冷如今是再也尋不到了,冷如果不和人發生最直接的生死關聯,就只是一種溫度的表達。爸爸小時候迷路過,在滿天飛雪的荒野。
恢復高考後的求學特別難得,爸爸和幾個兄弟步行200多公里從學校回家,快到家時下雪了,那是怎樣的一場雪呢?在一個距離家十幾公里的荒草甸上,一會兒風雪呼嘯,就看不見路了,再一會兒,大雪淹沒了腳踝,及膝,天黑的時候要及腰了。及腰的大雪不會吞沒一個人,踩上去也就到小腿就可以拔出,如果有武俠小說裏的功夫是可以飄行的。而更爲殘酷的現實是,一片荒野裏,不見路也不見光,血氣方剛的青年們走不動了。爸爸無數次的描述裏,依舊有恐懼湧上來。
迷路了,再走不到家,雪會凍死人的。
雪凍死過人的。明永樂年的時候,京城的監獄裏,錦衣衛的頭目紀綱,宴請在押的犯人大才子宰相解縉。那時窗外大雪紛飛,在獄中熬過五年了,突然一頓豐盛的酒食,解縉總也明白什麼意思。他大口吃菜大碗喝酒,醉成爛泥。醉了就好了,紀綱打個手勢,幾個衙役過來,把解縉拉了出去。
白茫茫的大雪世界,挖了個淺坑,人往裏一丟,堆上雪,解縉就被凍死在冰天雪地裏了。明代真正的大才子,《永樂大典》的總編,就這麼在醉鄉中進入冰寒徹骨的鬼域。
爸爸和他的兄弟們在寒冷絕望中唱歌,有什麼唱什麼,嗓子沙啞的時候,有個奇異的幻像出現了,一個白鬍子的老爺爺提着紅彤彤的燈籠帶路,他們欣喜地跟着,像被倩女招魂的書生,不唱了,隨光漫行,走着走着,就回到了鎮上的家。
這個幻象在三個叔叔的回憶中都出現過,那老爺爺就是狐仙。
狐仙、黃鼠狼、神婆、神漢,還有日落後村鎮上某戶人家神祕飄出的招魂神曲,以混白的冰雪爲底色,這個國度裏的巫是神和人之間的信使,怎麼通信呢?
薩滿術!招魂時唱着歌的——
通過綠色導火索催開花朵的力量
催開我綠色年華
炸燬樹根的力量是我的毀滅者而我啞然告知彎曲的玫瑰我的青春同樣被冬天的高燒壓彎驅動穿透岩石之水的力量驅動我的鮮血
枯竭滔滔不絕的力量使我的血凝結而我啞然告知我的血管同樣的嘴怎樣吮吸那山泉
……
時間之脣蛭吸源泉
愛情滴散聚合,但沉落的血會平息她的痛楚我啞然告知一種氣候的風時間怎樣沿星星滴答成天堂
而我啞然告知情人的墓穴我牀單上怎樣蠕動着同樣的蛆蟲
《通過綠色導火索催開花朵的力量》
狄蘭托馬斯(北島譯)
詩歌是語言的神咒,第一次聽到這首翻譯的詩的時候,就絲毫沒有疏離感。這些意向組合起來的奇妙圖騰,在冰雪中升騰出一個海市蜃樓,夭折的孩子,青紗帳裏的謀殺,墳頭的枯朽,烏克蘭女孩的煙,大哥那雙拿過槍也泡着茶的毛茸茸的手,我的故土上的生死場啊,有那麼多想忘都忘不掉,想拋都拋不開的人......他們是雪國的西西弗斯,轉世爲人都帶着一塊原石,滾上去,滾下來,滾上去,滾下來......
後來聽到狄蘭本人朗誦的錄音帶,他的聲音隔着電流,黑天鵝絨般渾厚低沉,顫抖頓挫,如同薩滿教巫師的祈禱和詛咒,讓人顫慄,讓人驚悚。
他預言了我的國嗎?我的雪國究竟是被那個舉着燈籠的白衣狐仙,被深夜招魂的薩滿祝福還是詛咒?
時間怎樣沿星星滴答成天堂?沒人告訴我,可可留給我一件黑色的紗裙,和寫着這句話的信箴,就真的消失了,大哥也找不到她。我問過一個薩滿,薩滿說,她向南面,坐火車走的,去了一個有水的暖和的地方。
小青,原名孫琳琳,頭號地標鄉愁大版主,於文字典籍中深遊淺耕,作品散見於《紅蔓》、《首席》、《華亭詩稿》等。
文 | 小 青 出品|頭號地標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