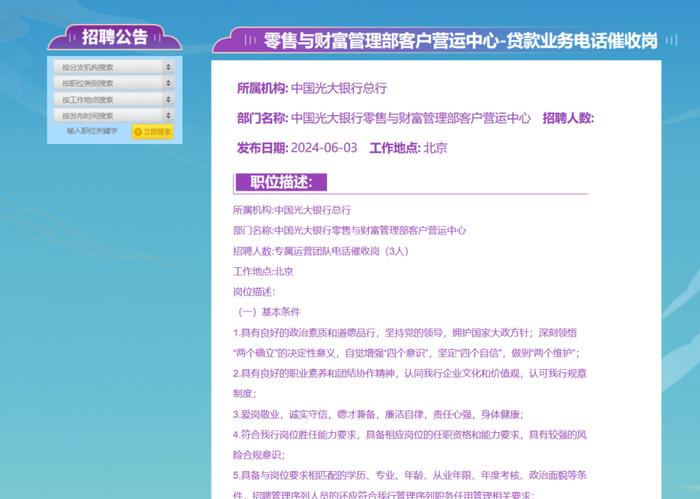童年的記憶 · 兒時的老礦
"\u003Cdiv\u003E\u003Ch1\u003E寫在前面\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賈汪的小河向西流》發佈以後,得到父老鄉親的厚愛,到目前爲止共有三千多人閱讀轉發,上百人跟帖,很多常年失聯的老鄰居、老同學都在文章後面評論,在此我表示萬分的感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的文章也觸發了一些賈汪人的思鄉情懷,他們也敲擊起久違的鍵盤,寫出自己對賈汪的一往情深。二姐魯\u003Cspan\u003E慶玲\u003C\u002Fspan\u003E年已七旬,也記敘了對老賈汪的一片情愫,加入了寫賈汪的行列,由於她年長我幾歲,所記敘的往事填補了我的不少記憶空白,有很好的史料價值。我的一篇文章能誘導更多的人回憶老賈汪,也算是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幸哉、幸哉。現特向大家推薦這篇文章,希望能引發您的共鳴。 ——周生元 2019.7.9\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童年的記憶 · 兒時的老礦\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魯\u003Cspan\u003E慶玲\u003C\u002Fspan\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周生元先生的《賈汪的小河向西流》讓我思緒萬千,喚醒了沉睡多年的記憶,許多往事彷彿就在眼前。欲罷不能,一吐爲快!\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謹以此文獻給我的同齡人。——魯\u003Cspan\u003E慶玲\u003C\u002Fspan\u003E \u003C\u002Fp\u003E\u003Ch1\u003E童年的記憶 · 兒時的老礦\u003C\u002Fh1\u003E\u003Cp\u003E 離別五十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彷彿從未走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我時常思念,\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思念你那曾經的容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童年的記憶裏,老礦的鐵道門外沒有人民醫院,只是一片水塘,西面還有一家\u003Cspan\u003E醬菜場\u003C\u002Fspan\u003E和兼賣肉的屠宰場。三號井圍牆西的路對面,沒有工農劇場,只是一片民房。碴子堆西的路對面沒有工人俱樂部,而是民宅和一年四季充滿生機的菜園地。菜園地的南面有一條自北而來又拐向西的涓涓小河,河水清澈。奶奶家離那不遠,夏天我常\u003Cspan\u003E去那兒\u003C\u002Fspan\u003E戲水玩耍。有一次正在興頭上,突然感覺右小腿外側不對勁,低頭一看是條螞蝗,我嚇得邊叫邊拽,就是拽不掉。這時只聽一個聲音大聲嚷道:用鞋底拍!用鞋底拍!!第一次沒拍掉,然後又狠狠地拍了一下,螞蝗才捲縮着掉進水裏。那時候,勞工街三號井後的北面沒有民房,也沒有新新校和八初中。近處是菜園地,遠處是莊稼地,菜園地的東北方向有一片松樹林,是一孫姓人家的祖墳地。不遠處就是自來水的源頭泉沿。\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兒時的老礦,沒有寬闊的馬路、沒有高大的樓房,也少有機動車輛。只是有時能看到救護車和救火車(消防車)及軍用吉普、軍用摩托車呼嘯而過,還有從部隊營房開出來的龐然大物,轟隆隆慢騰騰地向新礦方向駛去,所過之處,都會給路面留下兩道深深的“傷痕”。大人們說,那是打仗用的大炮坦克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小時候自來水也沒有進入尋常百姓家,只有幾個公用自來水供水點(免費),大部分生活用水靠石砌的水井,洗滌大件衣物傢什去河沿或泉沿。當然也沒有明清建築,因爲它當時只是一個不足百年因煤而興的蘇北煤窯,俗稱南窯(相對於北窯棗莊而言)。\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兒時的老礦,有東街、西集、南場子、鐵道門,有官坊裏、三號井、后王莊,大溝沿、酒精廠;有銀行、郵局、礦醫院,有中心校、部隊、照相館,有戲園子、說書場、澡堂、旅店、商店和飯店,還有染坊……人們生活必須的店鋪一應俱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小時候,教師和醫生分別被稱爲教書先生和看病的先生。小學階段分爲初小(一至四年級)和高小(五、六年級)。小學課程分別叫國語和算術,圖畫和唱歌,用的還是繁體字。當時的理髮店叫剃頭鋪,理髮師叫剃頭匠。留兩條辮子的是大姑娘,剪短髮、燙髮或盤髮髻的年輕女性是小媳婦。女性從服裝也能看出是職業婦女還是家庭婦女,着制服者(如列寧裝)爲職業女性(我母親是剪短髮着列寧裝的),穿大襟衣服的小腳女人一般都是家庭婦女。(到了公私合營特別是五八年大躍進之後,有不少小腳女人也參加了工作。)男女結婚分別稱“娶媳婦”和“出門子”。大人小孩的衣服大多是家庭縫製的老款式,講究點的就去裁縫鋪定製,印象中好像很少有買賣成衣的。衣服的面料都是棉、麻、絲、毛,沒有化纖。洗滌用品只有肥皂和鹼面,人們洗頭髮也用鹼面,當然更沒洗衣機和各種各樣的大小家用電器,只有手電筒。買包子或者熟菜都是用荷葉包裝,買糖果用專用包裝紙,買魚或肉用細麻繩穿着提在手上,買菜用竹籃子,沒有塑料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那時候,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和手藝人很多。有搖撥浪鼓的貨郎擔,有敲梆梆的賣油郎,還有修盆補鍋焊洋鐵壺的、戧刀磨剪子的、捏麪人的、吹糖人的、炸米花的、賣糖葫蘆和賣棉花糖的,還有玩皮影的、放洋片的、唱蓮花落的、玩雜耍的……這個走了那個來了,叫賣聲不絕於耳。\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每到春節更是熱鬧,街公所都會組織遊行慶祝活動,遊行隊伍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有坐花轎的、有騎毛驢的、有劃旱船的、有耍獅子舞龍的、有扭秧歌的。在扭秧歌的隊伍中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大活寶,其中一人耳朵上綴着一對紅辣椒???,另外一個打扮得十分誇張,兩人配合默契非常可樂。還有踩高蹺的、打腰鼓的……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活動都消失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童年的記憶裏,東街是指老城區東門外的區域,是較早的商業區,逐漸被西集取代。到我記事時起,就只有很少的幾家小門面,但仍有老礦唯一的大澡堂,澡堂門口有叫賣青蘿蔔和糖葫蘆的商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西集在老城區西門外,沿着西門的東西路向西走一里多路的區域。西集有兩條南北走向的道路,東面的一條稍寬,這裏商鋪雲集,有小百貨店、雜貨鋪、水果店、修車鋪、鐘錶鋪、飯店、中藥鋪、中醫所(有位老中醫權先生醫術不錯)、畫像館、茶爐房等,再向南還有新華書店、醫療所、機關幼兒園(全託,每週接送一次,我弟弟就是在這裏長大的)。西面的一條是菜市,魚市在最南頭菜場的路西,菜市場的南端出口右手旁是老戲園子,不僅演戲還放電影,同時也是賈汪柳琴劇團的所在地,大概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劇團解散了,附近似乎還有說書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官坊裏(現已消失)在老城區的東北方向,有高大的門樓,沒設門崗,大家可以隨便出入。中間是個小廣場,四周有許多院落。小時候,我們常去那裏玩耍。記得有一次,我抱着一歲多的弟弟在新栽的小樹旁玩耍,不小心一轉身弟弟的肚皮被圍在小樹一週的荊棘刮傷了,流了好多血(是夏天,弟弟只穿了一件擰腿褲),我又心疼又害怕。六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疤痕仍依稀可見。官坊裏的北面有兩個坐北朝南的院子,西邊的一處是政府機關,東面的一處是醫院(我弟弟就出生於此)。東北角是派出所和看守所,工商所、稅務所、法院等執法行政部門都在這個大院裏,還有工會、廣播站等部門。西南角是中國人民銀行(現在的工商銀行),最西南角的高牆上有一個高音喇叭,每次開播都會說“賈汪有線廣播站,各位聽衆請注意”,被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誤聽成是“賈汪有錢的王八旦,各位窮種請注意”,結果成爲經典的笑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南場子在老城內的西南方向,是慶祝會、審判會等大型活動的場所,有時也有跑江湖的馬戲團、雜技團在此表演。北面正中有一個幾十平米的臺子,臺子的後面緊貼部隊家屬院的南牆。場子的南面是當時徐州煤礦唯一的一家醫院,坐南朝北。礦醫院的後面是部隊營房,部隊營房有一個北門(正門)一個西門(後門)。記得文革時期因爲看電影,北門曾發生踩踏事故(具體詳情想不起來了)。廣場的東面是賈汪中心小學校(賈汪最早的一座小學),學校裏有一座老礦唯一的一座紅磚小洋樓,是當年日僞時期的建築。(學校後來更名爲團結小學現爲幼兒園)\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郵電局的地址百年沒變,只是進行了改造擴建。記憶中的郵電局門面不大,坐北朝南三間房,門前有一位代寫書信的老先生(那時候好多人不識字沒文化),進門正面是服務檯,右側是一電話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郵電局的西山牆有一家醬菜店,店主是一位個子不高身材微胖的孫姓老先生,非常乾淨利落,有一對雙胞胎孫女和我同齡。這裏的醬菜很有特色,其中的南方乳黃瓜、小蘿蔔頭、八寶菜、海帶絲等小菜甜鹹適度,至今回味無窮。這種小菜現在仍有賣的,只是再也喫不出當年的味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繼續向西,在西門裏的路北有一個剃頭鋪,簡易的兩層小樓。記得有一位年輕點的剃頭師傅徐大個子,和我身高一米九一的堂哥,是老礦人人皆知的兩個大個子。剃頭鋪對面是一修傘鋪,店主是一位從小得過天花的中年男子,其妻是一位白白胖胖的殘疾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當時,唯一的柳氏照像館在西門外南北路(就是“一條馬路寬又長,老礦新礦到韓場”的前身)的路西,離我奶奶家很近。攝影師的二女兒和我同齡,我常去她家玩,當時還搞不懂爲什麼鏡頭裏的人都是頭朝下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從照像館向南幾十米,是劉家饅頭房,鄰居們稱他們爲大賣饃饃和二賣饃饃,(因爲他們是堂兄弟)。他們每家都弟兄好幾個,有的蒸賣饅頭,有的是礦工。公私合營後,其中一家的三哥到徐州七中做了炊事員,其餘幾個去了前進飯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三號井和三號井後都屬於勞工街,勞工街的居民大部分是國家公職人員,以礦工家庭居多。以我們院五家爲例,三家礦工、一家學校教師、一家銀行職員。後來其中的一家礦工搬走了,新搬進的一家,其父爲郵電局老職工而倆兒子都是煤礦的。三號井與三號井後一南一北,(按照習慣北爲後)中間隔着高牆和一條寬約數米的排水溝(等同徐州市內的奎河)。從郵局東面的大巷子一直向北行約200米,巷子東面是機關家屬院,巷子的出口處有一座小橋,跨過小橋有一條小路向左右伸展,西到碴子堆上沿,東至援工隊的菜園地,北到後河沿的一大片民居,都屬於三號井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勞工街是個老先進,街道的所有活動都走在其他街道的前面,特別是愛國衛生更是領先!(徐州有個鐵貨街,賈汪有個勞工街)。掃過的街道路面都要用裝有石灰粉的圓底籃子等距離的頓一頓,既衛生又美觀。街道主任經常陪着一些領導戴着白手套到各家各戶檢查衛生,這兒抹抹那兒擦擦。儘管那時生活貧困,但衛生工作絲毫不馬虎。每年夏天街道都會免費發放滅蠅水、(一次隔壁的小弟誤喝了滅蠅水,幸虧發現及時,有驚無險。)在規定的時間裏統一行動薰蚊子、給孩子們免費注射各種疫苗,家家戶戶的牆壁上都貼有愛國衛生公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我們也由娃娃變成了古稀老人,百年煤城更是萬象更新地覆天翻!目前正在轉型發展,潘安湖國家溼地公園、大洞山、茱萸寺、萬畝石榴園等十大旅遊景點深受遊客稱讚!一座新興的山水文化旅遊城正在崛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俱往矣,換了人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所以我更想“常回家看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魯慶玲\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2019、7、6、\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203e10aa5cbe45369dfeb48f153fb438\" img_width=\"438\" img_height=\"787\" alt=\"童年的記憶 · 兒時的老礦\"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附:魯慶玲,老三屆知青,土生土長的老賈汪老礦人。祖父母爲煤城的第一代居民,其家族在此生活了百年,繁衍生息了六代人。父輩中最小的姑母尚在,已九十二歲高齡。第四代長孫幾年前已升級爲爺爺,現在是兩個孩子的祖父。2019、7、6、\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518944719903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