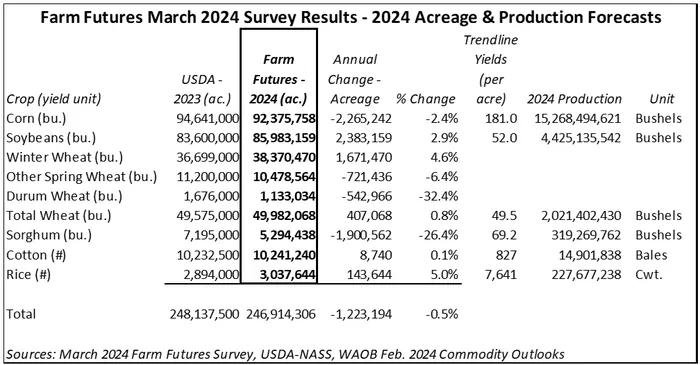毛主席:“魯迅活着會怎樣”?
"\u003Cdiv\u003E\u003Cp\u003E來源:中國新聞網,作者:何立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的兩位偉人。毛澤東是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學造詣很高。魯迅是思想家、文學家和革命家。同爲思想家,毛澤東與魯迅看問題都很深刻,但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不同。毛澤東更多地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上,而魯迅則定位在思想家的位置上。他們雖然未曾謀面,但是毛澤東對魯迅充滿了尊敬和敬仰之情,他多次表明:“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u003C\u002Fp\u003E\u003Cdiv class=\"pgc-img\"\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3.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ed279b83af2d4eeba5ea2e407948b874\" img_width=\"300\" img_height=\"300\" alt=\"毛主席:“魯迅活着會怎樣”?\" inline=\"0\"\u003E\u003Cp class=\"pgc-img-caption\"\u003E魯迅\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互相神交:毛澤東與魯迅\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魯迅與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的心是相通的。他雖然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是對毛澤東卻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魯迅向左聯文委書記馮雪峯以及茅盾打聽中央蘇區和毛澤東的情況,極爲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圍剿”鬥爭中的戰績,因爲他們把氣焰囂張的國民黨反動派“嚇壞了”。魯迅對英勇作戰的紅軍十分欽佩。1932年秋,在馮雪峯等人的陪同下,魯迅曾在家中兩次會見陳賡。陳賡講的紅軍英勇戰鬥的情形以及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給魯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魯迅非常重視這次談話,以後一再提及,認爲確實比《鐵流》、《毀滅》裏寫的生活更動人。他曾一度想寫一部反映蘇區紅軍戰爭題材的小說,但是終因沒有實際生活經驗而未動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首府江西瑞金。臨時中央博古提議,可以讓魯迅來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主持中央蘇區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魯迅身邊的聯絡員馮雪峯不贊成博古的意見,認爲博古不瞭解魯迅,低估了魯迅在白區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並提出還是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爲好。張聞天贊同馮雪峯的意見,並徵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表示:“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4年1月,因爲馮雪峯在上海的安全難以保證,黨中央把他調到瑞金,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毛澤東此時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擠,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權,處境艱難。聽說馮雪峯來到了瑞金,毛澤東專門拜訪了他。毛澤東遺憾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馮雪峯向毛澤東彙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特別詳細地介紹了魯迅的情況。毛澤東對馮雪峯講述的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峯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曾經說過,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後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爲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馮雪峯還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毛澤東的詩詞,認爲他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非常開心,因爲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岡山之前的演講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天晚上,毛澤東再次約見馮雪峯。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毛澤東接着說:“我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阿Q是個落後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羣衆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弱點,滿腔熱情地將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幹部,很多人看不到,對羣衆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持。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毛澤東還對馮雪峯說:“我也想重讀一遍,可惜當地找不到這部書。”毛澤東又問魯迅這幾年寫了些什麼,馮雪峯扼要介紹了魯迅到達上海後所寫的文章,尤其是在幾次論爭中的文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馮雪峯接着反映,臨時中央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毛澤東問:“幹什麼?誰主張的?”馮雪峯解釋說:“不是正式主張,只是隨便說說。”毛澤東嘆息道:“這些人真是一點也不瞭解魯迅!”馮雪峯還把魯迅不想離開上海,並謝絕到蘇聯去,認爲在崗位上,總能打一槍兩槍的想法詳細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感慨地說:“這纔是實際的魯迅!一個人遇到緊要關頭,敢於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堅決將艱鉅的任務承擔下來,是符合人民願望的最可貴的品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多次瀕臨危亡,終於能夠維持不墮,就因爲人民有這樣的品格,這點在魯迅身上集中地體現出來。”1935年10月,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帶領紅軍衝破蔣介石几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經過萬里長征,勝利到達陝北。魯迅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寫下了著名的《亥年殘秋偶作》一詩,其中有“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的句子,表現了魯迅遙望北斗星,對遠在陝北的紅軍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無限牽掛之情。1936年3月29日,魯迅抱病和茅盾一起爲紅軍東征勝利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了賀信:“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衆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奮鬥,爲你們的後盾,爲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歡迎與擁護。”“在你們的身上,寄託着人類和中國的將來。”魯迅從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類和中國的將來”,看到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無限光明前途。\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6年4月,馮雪峯奉黨中央之命離開陝北到上海同中共祕密組織建立聯繫。馮雪峯在上海住到了魯迅的家中,同魯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魯迅講述了紅軍長征的經過、遵義會議情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魯迅靜靜地傾聽着,馮雪峯每次提到毛澤東,提到毛澤東周圍的中共領導人,魯迅總是流露出親切信任的表情。魯迅還委託馮雪峯把自己抱病編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購買的火腿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6年初,在上海的“託派”組織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爲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企圖挑撥魯迅與中共的關係。6月9日,已經病重的魯迅口授了一封信,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魯迅提及毛澤東見諸文字者爲數不多,這是十分難得的一次。正由於此,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多次講話中都提到了魯迅,稱讚“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聯名發表了《爲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爲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在《爲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中決定:一、在全蘇區內下半旗誌哀並在各地方和紅軍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10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爲魯迅圖書館;四、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五、蒐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爲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中,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還對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魯迅先生遺體進行國葬,並付國史館列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爲魯迅縣;三、改北平大學爲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蒐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一切有關禁止他的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魯迅病逝後,黨中央委託馮雪峯主持治喪工作。馮雪峯還特意把毛澤東的名字寫進了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1937年1月,馮雪峯迴延安彙報工作,毛澤東一再關切地詢問魯迅逝世前後的情況,表示了對魯迅的懷念之情。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魯迅美術學院)。毛澤東親自爲學院書寫校名和“緊張、嚴肅、刻苦、虛心”的校訓。毛澤東對魯迅的尊敬與熱愛,還體現在他對魯迅的學生的關懷上。1938年春,毛澤東從前來彙報工作的丁玲處獲知魯迅的弟子蕭軍來到延安的消息,便親自到招待所探望蕭軍,還邀請他一起共進午餐。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抵達延安後,由於人際關係上出現問題,曾一度萌生離開延安的念頭。毛澤東知道後,一次又一次挽留他,與他促膝長談,幫助他解開心頭疙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先後10次寫信給他,多次接他到楊家嶺談話。1945年11月,蕭軍赴東北工作前夕,毛澤東又兩次接見他,與他親切交談,期盼他能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還邀請蕭軍去朱德總司令家共進午餐。飯後,毛澤東與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揮手告別。毛澤東對蕭軍的關懷,尤其是對魯迅的評價,影響了蕭軍一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毛澤東指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愛讀魯迅的書,非常推崇魯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學功績,在其著作、報告、講演和口頭談話中,有不少關於魯迅的論述,僅130多萬字的《毛澤東選集》五卷中就達20處之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10月19日,陝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大會。毛澤東出席會議並發表了演講。毛澤東在演講中指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爲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爲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輕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裏,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陝北公學的同志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裏勤謹地學習革命理論一樣,是充滿了艱苦鬥爭的精神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這次演講中,毛澤東明確指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他還概括了魯迅的三個特點:“政治的遠見;鬥爭精神;犧牲精神。”他指出:“綜合上述幾個特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所以,他在文藝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優秀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爲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的演講,被陝北公學學員汪大漠記錄下來。汪大漠將演講記錄稿帶到武漢後,交給曾協助魯迅編過《海燕》雜誌的左聯重要成員、著名文藝理論家胡風。胡風將毛澤東的演講稿刊載於自己主編的《七月》雜誌上。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這篇題爲《論魯迅》的演講記錄稿,後編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新創刊的《中國文化》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對魯迅給予高度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評價魯迅的短短四句話中,毛澤東使用了4個“偉大”、9個“最”和“空前”等最高級的形容詞和副詞。在毛澤東對古今中外人物的評價中,還沒有第二個受到過如此高的評價,他把對魯迅的評價推向了最高峯。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這一篇專門談文藝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學作品就是魯迅翻譯的《毀滅》。他還從魯迅的《自嘲》詩中引出“橫眉俯首”一聯,說是應該拿它做座右銘。同時,毛澤東還說:“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學他“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49年7月,全國文聯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會議召開期間,各位代表都獲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這就是毛澤東和魯迅的雙人像章。這枚像章爲銅質,圓型,直徑2.2釐米,中上方一面飄卷的紅旗,有毛澤東和魯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樣,下方“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15個繁體字呈半圓型。毛澤東與魯迅雙人像章的出現,反映了毛澤東對魯迅的感情。\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毛澤東對魯迅著作的喜愛和運用\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7年3月,毛澤東會見了到延安訪問的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談到《阿Q正傳》。這是第一次毛澤東談魯迅作品的書面記載。毛澤東說:國內有一部分帶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做“屈服、投降與悔過”,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8年l月12日,毛澤東寫信給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主任教員的青年哲學家艾思奇說:“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個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毛澤東在此之前已經讀了一些魯迅作品,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系統地讀到魯迅的全部著作,因此對《魯迅全集》充滿着濃厚的興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8年8月,中國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魯迅全集》,毛澤東通過上海中共祕密組織得到了一套。毛澤東對這套《魯迅全集》十分珍愛,他轉移、行軍到哪裏,就把它帶到那裏。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毛澤東的不少書籍和用品都丟棄了,可是這套20卷本的《魯迅全集》卻一直伴隨着他。到了中南海以後,有一天,他在書房裏閱讀這套《魯迅全集》,一邊翻閱,一邊飽含深情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書保存下來不容易啊!當時打仗,說轉移就轉移,有時在轉移路上還要打仗,書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謝那曾爲我背書的同志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他也隨身帶着幾本魯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讀。有一天,外事活動後回到住地,離開飯的時間不到半小時,他又拿出魯迅的書讀起來。開飯時間到了,工作人員把飯菜放在桌子上,輕聲催他喫飯,他說:“還有一點,看完就喫。”毛澤東一邊用筆在書上圈圈畫畫,一邊自言自語道:“說得好!說得好!”一直把20來頁書讀完,纔去喫飯。他一邊喫,一邊笑着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愛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讀魯迅的書,常常忘了睡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魯迅的著作中,毛澤東最愛讀、談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傳》。在回答一些重大現實問題的時候,毛澤東常常利用這個人物形象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在與斯諾談話時,毛澤東批評蔣介石否認統一戰線的事實,便以阿Q爲例,說蔣是阿Q主義者,是看不到統一戰線存在的自欺欺人。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以阿Q不許人家揭他的瘡疤,但他鬥爭起來也算英雄的性格,比喻犯了“左”傾錯誤的同志。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讚揚“《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魯迅在這篇小說裏,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特別指出:“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有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在1959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道:“阿Q這個人是有缺點的,缺點就表現在他那個頭不那麼漂亮,是個瘌痢頭,因爲他就是講不得,人家偏要講,一講就發火,發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贏,他就說兒子打老子。”在這裏,毛澤東講這些話,意在說明有缺點要允許別人講,有缺點或犯錯誤的同志要準備聽閒話,多準備聽一點。毛澤東還非常喜愛魯迅的舊體詩。魯迅的詩歌揭露黑暗,歌頌光明。毛澤東曾熱情地指出:“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1958年12月1日,著名粵劇演員紅線女在武昌爲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代表演出,並請求毛澤東寫幾個字。當晚,毛澤東欣然揮毫寫了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魯迅詩句的鐘愛和讚賞。60年代初,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魯迅的戰鬥方法很值得學習。”“魯迅戰鬥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只准談風月,他就出了《準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他臨死時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毛澤東閱讀《魯迅全集》非常認真仔細。從他在書上批劃的情形來看,凡是原書中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們一一改正過來。例如,《魯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盯梢》裏有一段文字:“那裏面有張泌的《浣溪沙》調十首,其九雲:晚逐香車入鳳城,東風斜揭繡簾輕,慢回嬌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計從,便須佯醉且隨行,依稀聞道太狂生。”這首詞中的“消息未通何計從”的“從”字,如果僅僅從詞義來看,看不出是一個錯字;但從詞律的音韻來看,顯然是錯了。毛澤東讀到這裏時,便將“從”字改爲“是”字。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卷八百九十八顯示,原詞確實是“是”字,而不是“從”字。1981年新版《魯迅全集》據此作了改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推崇魯迅的同時,毛澤東也實事求是地指出魯迅的某些不足。1939 年11月7日,毛澤東在給周揚的信中曾經說過:“魯迅在表現農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義的一面,忽略其英勇鬥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爲他未曾經歷過農民鬥爭之故。”新中國成立後,在同音樂工作者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指出:“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魯迅)的看法不大正確。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他對地方戲還是喜歡的。”\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 \u003Cstrong\u003E“魯迅活着會怎樣”\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前後,是毛澤東一生當中比較多地談及魯迅的時期,而他談得最多的是魯迅的雜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瞭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33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中央宣傳部辦公室1957年3月6日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彙集》,共彙集了33個問題,即毛澤東所說的“33個題目”。“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上傳說,毛澤東認爲魯迅可做個文聯主席,可能這篇講話是個緣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談道:\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裏。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爲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捱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捱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爲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裏面就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毛澤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u003C\u002Fstrong\u003E\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魯迅被林彪、“四人幫”利用起來,作爲推行崇拜毛澤東的工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66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30週年紀念日。這天,《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都發表了紀念社論。《紅旗》雜誌社論的題目是《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其中說:“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爲代表的正確路線。……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魯迅那樣,堅決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這無疑是把“古史現代化”,讓今天的人感到啼笑皆非。《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社論,指出:“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着鬥爭的暴風雨奮勇前進!”說魯迅“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更是荒唐不已,反映了那個特定年代的特殊政治氣氛。\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輿論把魯迅打扮成爲毛澤東的“崇拜者”,而實際上,毛澤東卻是魯迅的真正“知音”。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信江青:“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指林彪,編者注)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毛澤東個人已經被神化的情況下,他對魯迅的評價仍然是很高的。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大病一場。此刻他又一次想到了魯迅,他命人將《魯迅全集》排成線裝大字本,認真重讀並批註。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在武漢接見曾思玉等軍區領導人的時候說:“勸大家再看看魯迅全集,他的書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毛澤東的晚年,多次發出“學魯迅的榜樣”、“讀點魯迅”的號召。1975年7月14日晚,毛澤東同江青談調整文藝政策問題,對他們把周揚等一批文藝界負責同志長期關押提出批評。毛澤東說:“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羣衆。”1975年8月,毛澤東用顫抖的手在《魯迅全集》線裝本第5卷第5分冊的封面上寫下了“喫爛蘋果”幾個字,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讀此分冊中的《關於翻譯(下)》一文。當讀到魯迅用“剜爛蘋果”的比喻,主張正確批評,反對“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時,毛澤東非常高興,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對於《魯迅全集》的出版,毛澤東非常關心。1975年11月,毛澤東在周海嬰的來信中就魯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做了重要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出版部門和研究人員聞風而動,一套嶄新的《魯迅全集》很快就呈現在全國廣大讀者的面前,對進一步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發揚魯迅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u002Fdiv\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6413099127079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