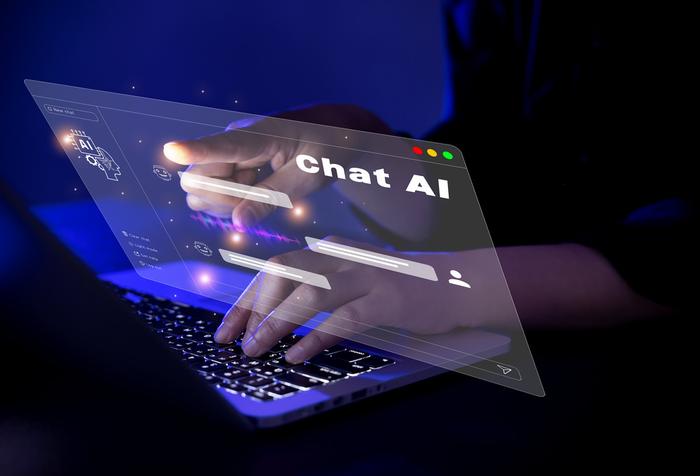18岁,走向远方|怀旧党
1986年春节在前黄中学,我唯一留存的2张18岁照片之一
1985年,我18岁。
这一年,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关口,高考。
高考之于我这一代乡下农家子弟,几乎是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跳出农门,赢得不愁饥馁甚至能够福泽全家的唯一机会。尽管这个时候,农村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对贫穷生活恐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们。所以,千军万马挤上高考这座独木桥,意义远非未曾亲历那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
前庙(前黄-庙桥)公路,我上初二时开筑
1985年上半年,我在前黄中学高三文科班就读准备应考,每天往返在简陋的前庙公路,步行上下学——多年之后,我曾化用美国民谣歌手约翰·丹佛的名曲,把前庙公路视为带我走向远方的村路。即将来临的高考的紧张气氛自然笼罩着我们,尤其像我这样的成绩还过得去,被预期总能考上个大学的人。但是,即便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我依然偷偷在自习课上读小说。
记得85年春天一个早自习上,我正埋首在堆满复习资料的书桌上,透过桌子上的窟窿读着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解放军文艺》上刊载的李存葆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莹》,看到悲伤处,忍不住抽噎。适值我的历史老师李培森先生巡视经过,被他发现,他没有严厉批评我,也没有没收我的小说,只是说,这个时候了,要收心准备迎考了。考上大学,会有更多小说可读。
也就此以后,我放下了小说,那是我那个年代唯一的课余爱好,专心复习考试。
80年代前黄中学。平房第一间是我初三教室,三层楼第一间是高三教室
大河边上的前黄中学宿舍
在我18岁之前,第一次坐汽车的经历,就是17岁时跟着村里人从前黄坐农公车到常州,我想去看看真的火车是怎样,我认定将来要带我去向远方的火车,然后,找不到回家的车站,从常州火车站徒步走回了前黄。
这是我当时的世界。我的世界,主要是由父母师长的见识构建的。因为出身农家,我熟悉周边乡村的田野河流以及各种农作物鸟雀鱼虾植物;因为我的师长,他们给我们在知识教育之外给我们打开的视野,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比我父母期待更多的渴望;因为前黄中学的图书室——我从初中起即是这个图书室阅览室的常客——我对1980年代复兴的文学作品有了最初的接触,而且几乎是跟潮流同步——接触了某种程度上超越师长视野的世界,也因此,1984年我在前黄中学图书室读到的程乃珊的小说《蓝屋》,它所蕴含的自我奋斗的价值观,在1985年高考后终于发芽了。
《蓝屋》,程乃珊著,它给了我自我奋斗的启蒙
在高考前填志愿时,我谢绝了学校给我的报考南京大学的推荐指标,而选择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刚开始填了吉林大学哲学系,因为李培森老师对吉大高清海老师的推许(我上大学后知道,高先生彼时就是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之一),虽然因家人反对,最终报考了人民大学,但依然还是自己的决定。其实,这决定的背后,就是要去远方,要去没有熟人的地方,凭自己的努力闯出来一番天地来。这是程乃珊女士的《蓝屋》教给我的,而且,这种自我奋斗的价值观塑造了一个新的我,至今仍是我的精神底色。
尽管高考结束,自我预估尚可(我预估的总成绩与最终考分几乎是一样的),我还是和初中毕业的弟弟一起,学起了站脚盆,想着万一没考上,也可求个主动,将来跟着父亲打鱼,贴补家用。直到高考发榜,我磕破了腿也没学会站脚盆。
9月,我洗脚上岸,背着行囊,在常州火车站坐上了绿皮火车,与一位高中同学就伴,一起奔向遥远而陌生的北京。这一走,走得很远,在精神世界,毫不夸张说,我走得可能比前黄中学我所有的同学师长更远。
从此,江南少了一个站脚盆的捉鱼佬,也可能少了一个乡镇企业家,但是,多了一个至今怀着赤诚之心的自由而孤傲的读书人。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