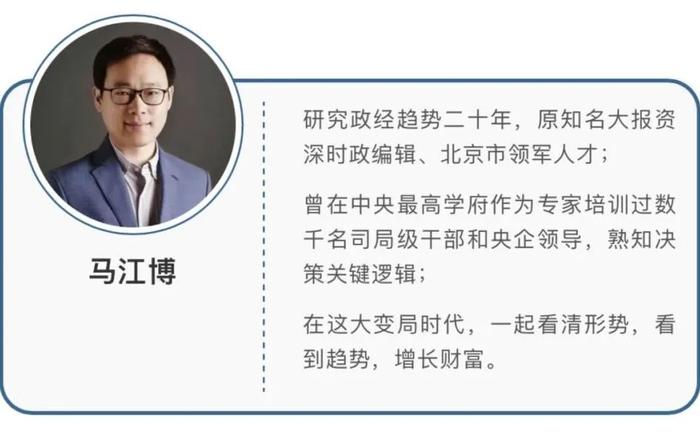18歲,走向遠方|懷舊黨
1986年春節在前黃中學,我唯一留存的2張18歲照片之一
1985年,我18歲。
這一年,我迎來了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關口,高考。
高考之於我這一代鄉下農家子弟,幾乎是擺脫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跳出農門,贏得不愁飢餒甚至能夠福澤全家的唯一機會。儘管這個時候,農村的物質生活已經有了很大改觀,但對貧窮生活恐懼的陰影,依然籠罩着我們。所以,千軍萬馬擠上高考這座獨木橋,意義遠非未曾親歷那個時代的人所能理解。
前廟(前黃-廟橋)公路,我上初二時開築
1985年上半年,我在前黃中學高三文科班就讀準備應考,每天往返在簡陋的前廟公路,步行上下學——多年之後,我曾化用美國民謠歌手約翰·丹佛的名曲,把前廟公路視爲帶我走向遠方的村路。即將來臨的高考的緊張氣氛自然籠罩着我們,尤其像我這樣的成績還過得去,被預期總能考上個大學的人。但是,即便在如此緊張的氛圍中,我依然偷偷在自習課上讀小說。
記得85年春天一個早自習上,我正埋首在堆滿複習資料的書桌上,透過桌子上的窟窿讀着從學校圖書室借來的《解放軍文藝》上刊載的李存葆的小說,《山中那十九座墳瑩》,看到悲傷處,忍不住抽噎。適值我的歷史老師李培森先生巡視經過,被他發現,他沒有嚴厲批評我,也沒有沒收我的小說,只是說,這個時候了,要收心準備迎考了。考上大學,會有更多小說可讀。
也就此以後,我放下了小說,那是我那個年代唯一的課餘愛好,專心複習考試。
80年代前黃中學。平房第一間是我初三教室,三層樓第一間是高三教室
大河邊上的前黃中學宿舍
在我18歲之前,第一次坐汽車的經歷,就是17歲時跟着村裏人從前黃坐農公車到常州,我想去看看真的火車是怎樣,我認定將來要帶我去向遠方的火車,然後,找不到回家的車站,從常州火車站徒步走回了前黃。
這是我當時的世界。我的世界,主要是由父母師長的見識構建的。因爲出身農家,我熟悉周邊鄉村的田野河流以及各種農作物鳥雀魚蝦植物;因爲我的師長,他們給我們在知識教育之外給我們打開的視野,讓我對外面的世界有了比我父母期待更多的渴望;因爲前黃中學的圖書室——我從初中起即是這個圖書室閱覽室的常客——我對1980年代復興的文學作品有了最初的接觸,而且幾乎是跟潮流同步——接觸了某種程度上超越師長視野的世界,也因此,1984年我在前黃中學圖書室讀到的程乃珊的小說《藍屋》,它所蘊含的自我奮鬥的價值觀,在1985年高考後終於發芽了。
《藍屋》,程乃珊著,它給了我自我奮鬥的啓蒙
在高考前填志願時,我謝絕了學校給我的報考南京大學的推薦指標,而選擇了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剛開始填了吉林大學哲學系,因爲李培森老師對吉大高清海老師的推許(我上大學後知道,高先生彼時就是中國哲學界的領軍之一),雖然因家人反對,最終報考了人民大學,但依然還是自己的決定。其實,這決定的背後,就是要去遠方,要去沒有熟人的地方,憑自己的努力闖出來一番天地來。這是程乃珊女士的《藍屋》教給我的,而且,這種自我奮鬥的價值觀塑造了一個新的我,至今仍是我的精神底色。
儘管高考結束,自我預估尚可(我預估的總成績與最終考分幾乎是一樣的),我還是和初中畢業的弟弟一起,學起了站腳盆,想着萬一沒考上,也可求個主動,將來跟着父親打魚,貼補家用。直到高考發榜,我磕破了腿也沒學會站腳盆。
9月,我洗腳上岸,揹着行囊,在常州火車站坐上了綠皮火車,與一位高中同學就伴,一起奔向遙遠而陌生的北京。這一走,走得很遠,在精神世界,毫不誇張說,我走得可能比前黃中學我所有的同學師長更遠。
從此,江南少了一個站腳盆的捉魚佬,也可能少了一個鄉鎮企業家,但是,多了一個至今懷着赤誠之心的自由而孤傲的讀書人。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