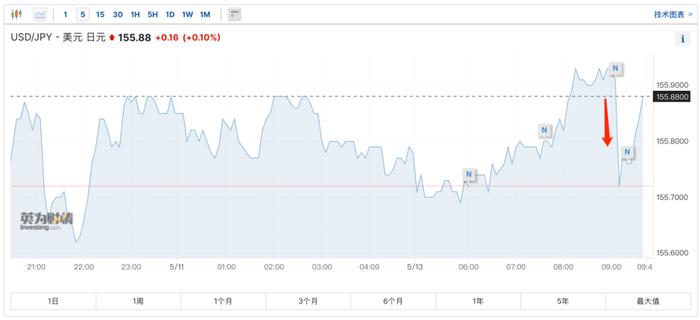賀江楓:華北自治運動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
摘要:宋哲元在日軍壓力之下,29日致電蔣介石,希望中央贊同華北自治,“近日徵詢多數意見,有主張如能在中央系統之下,\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予以適應環境辦法,既不喪失主權,亦可應付艱迫外交,是否可備採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結 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華北自治運動是內政外交雙重因素交互影響的產物,不僅是日本有預謀地蠶食華北、實施其侵略中國計劃的重要步驟,亦是1935年6月《何梅協定》達成後,在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對日妥協的背景之下,華北政治失序、中央與地方矛盾衝突激化的結果。
"\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FjYwCHOmbb37\" img_width=\"1080\" img_height=\"721\" alt=\"賀江楓:華北自治運動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 inline=\"0\"\u003E\u003Cp\u003E1933年,日軍兵臨平津,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被迫簽訂《塘沽停戰協定》。此後,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主張對日妥協,華北局勢表面暫趨穩定。然而就在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高呼“中日親善”之時,1935年,日軍先後製造河北事件、張北事件、華北自治運動,各地方實力派蠢蠢欲動。內憂外患之下,華北危機日益深重。6月19日,駐日大使蔣作賓致電南京外交部,不無憂慮地報告到:日本“以中國將趨統一,認爲不利,欲在北方組織一反中央勢力。先以冀晉察綏魯爲範圍,俾與中央脫離,以便爲所欲爲。現正積極進行,並欲利用閻主任爲傀儡”。此後,面對日軍威逼利誘,韓復榘、宋哲元含糊其辭、遊移不定,閻錫山卻逐漸轉向與中央合作。蔣介石認爲,“倭寇在華北策動五省自治獨立,必欲於六中全會或五全大會時達成其目的,對各省主官威脅利誘,無所不至,魯韓尤爲動搖,而閻則深明大義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華北各地方實力派態度的不同實則反映的是華北地方實力派面對日軍侵略,在夾縫之中謀求生存的現實邏輯,有其典型性與普遍性。海內外學界圍繞1935年華北自治運動與中日關係已有諸多精深研究,但重在探討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危機應對與日軍侵華政策的演變,至於華北自治運動過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各地方實力派,彼此之間如何考量與抉擇,缺乏充分探討。李君山從華北內部權力格局的角度論述宋哲元與華北自治運動的複雜關係,但未展現華北地方實力派內部的差異與互動。馬振犢比較分析了宋哲元、韓復榘、閻錫山對日態度的差異,但受時代與資料所限,無從展現地方實力派差異變化的具體過程。此外,肖自力通過考察20世紀30年代何鍵與中央、西南的彼此關係,分析地方實力派政治存在的特性,但華北與南方地方實力派所處外部環境迥異,內在邏輯亦有所差異。故而,本文試圖探究華北地方實力派在1935年華北危機的複雜局勢之下,如何處理與日本、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關係,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過程,進而管窺抗日戰爭期間華北地方實力派政治選擇背後深層次的原因。\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一、日軍侵略與華北政治失序\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3年《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日軍並未停止對華北的蠶食與滲透,“日方所亟亟求解決之根本問題,爲近期的經濟合作,遠期的對俄作戰之軍事協定”,“膺白(黃郛)初到華北,未能順利與之解決,於是日本改變方針,乃向華南、華北各部分別進行”。1934年12月,日本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聯合制定《關於對華政策的文件》,特別就華北問題提出:(1)逐漸形成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政令不及於華北地區的趨勢;(2)擴大日本在華北的各項權益;(3)將華北政權官吏更換爲便於日本實施對華政策的人物。爲落實這一文件,1935年1月4日至5日,包括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徵四郎、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內的諸多日軍在華高級將領,在大連召開幕僚會議,達成策動華北自治等若干共識:(1)在華北地區,逐漸強化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政令被削弱的局面;(2)對能夠實現華北獨立的勢力予以支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華北軍政要務此時名義上雖由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組建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政整會”)與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以下簡稱“北平軍分會”)全權負責,但所能控制的區域僅限於北平及冀東戰區各縣,晉察冀綏魯五省仍由各地方實力派分別掌控。東北軍自1930年中原大戰後長期掌控河北,自1932年由於學忠出任河北省省主席。二十九軍亦因長城抗戰的緣故進駐察哈爾,此後由宋哲元執掌察哈爾軍政大權。韓復榘則在中原大戰時期助蔣有功,獲委山東省省主席,成爲獨佔一省的大吏。尤其以閻錫山爲首的晉系,自民國建立後長期控制山西,自成體系,逐漸成爲華北地方實力派中歷史最爲悠久、影響最爲廣泛的派系。晉系雖在中原大戰失敗後實力嚴重受損,但根基尚存,各部經蔣介石、張學良改編後,仍得以保留四軍兵力,即軍長爲商震的三十二軍、軍長爲徐永昌的三十三軍、軍長爲楊愛源的三十四軍、軍長爲傅作義的三十五軍。即便1931年8月商震與閻錫山心生嫌隙,率軍進駐河北邢臺,在冀南、豫北獨樹一幟,但畢竟同氣連枝。徐永昌爲山西省省主席,傅作義爲綏遠省省主席,晉系仍舊控制晉綏兩地部分軍政權力。故而閻錫山能夠於1932年利用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內憂外患、無暇顧及的時機,重掌晉綏政權。“查閻先生此次重主晉綏軍政以來,雖聲言從事建設,不問外事,而骨子裏絕不如此簡單,殆屬人所共知。”\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鑑於晉系在華北實力最爲雄厚,日方迅即將其確立爲策動華北分離工作的重要拉攏對象。事實上,日方對閻錫山的聯絡早已有之,“\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九一\u003C\u002Fi\u003E八以後,日本軍政人員來晉者時有所聞,就中往來最頻且最惹人注目者爲柴山氏(柴山兼四郎),與閻會晤之地點或在河邊,或在省垣”,“並屢有表示”。1934年3月26日,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武官柴山兼四郎派人前往太原與閻錫山會晤,明言目前負責華北軍政大局的政整會委員長黃郛與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皆不能主治華北”,日軍必欲打倒而後快,至於山東省省主席韓復榘“不無可慮”,難堪重任,希望閻錫山出面重組華北政局,同時河北省省主席于學忠、察哈爾省省主席宋哲元“都非換不可”,爲拉攏閻錫山,特別強調“於擬換以商,因商曾爲閻先生部下也”。閻錫山面對日軍誘導,態度含糊其辭。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着推動華北自治成爲日本侵略華北的首要目標,日軍亦加速對閻錫山的引誘工作。1935年1月初,柴山兼四郎派人警告閻錫山:“日本決不能坐待日俄戰時,令中國襲擊其後路,爲自救起見,不能不造成華北爲日本絕對友誼區域”,希望晉系迅即與日本聯合策動華北自治,“今日華北,閻先生如能領導之,與日謀妥協,固甚佳,否則日本亦自有法”。閻錫山初始“表示苦無應付策”,當其得悉日軍要求晉系選派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賈景德其中之一與日談判,“乃曰:此有辦法矣”,趙戴文主張由傅作義負責與日談判,但傅作義再三推辭,晉系內部意見分歧,“請次隴(趙戴文)走河邊回覆之”。1月14日,閻錫山召集部屬再次商議,決定“對日方之示意應再沉靜,以觀其究竟”。此次會議中,閻錫山“話極多,過慮及不切實際的想象亦復不少,惟結論至扼要”。2月8日,閻錫山獲悉1935年1月4日日軍大連會議詳情,表示對日軍仍應暫取觀察態度,“因日甚疑閻先生傾赤”,但爲消除日軍顧慮,特令靳祥垣“往解釋物產證券與\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勞資\u003C\u002Fi\u003E問題之意見”。然而至5月河北事件爆發,日軍提出撤銷河北省國民黨黨部、中央軍退出河北、撤換河北省省主席于學忠等多項無理要求,何應欽在日軍壓力下被迫應允。《何梅協定》使得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在華北的權力基礎蕩然無存,同時東北軍被迫他調,河北省省主席于學忠亦宣佈辭職,華北各派勢力的脆弱平衡被日軍打破。\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河北省省主席的人選隨即成爲各方勢力覬覦的目標。圍繞河北省府改組問題,日方躍躍欲試,急欲安插親日人士。日軍鑑於商震與閻錫山關係密切,意圖拉攏晉系,希望具有親日背景的商震出任河北省省主席。蔣介石則有意令何應欽重新北上,執掌河北。他於6月17日致電何應欽,強調“華北環境實爲最苦痛惡劣之環境,然亦爲民族生死存亡最大之關鍵,蓋中本不欲強兄再任此難局,然兄不北返,則事實上以後華北紛亂日甚一日,更難收拾,此時惟有忍辱含羞,以維現局,而收人心,爲\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我黨\u003C\u002Fi\u003E國保持革命歷史一線之榮光”。他認爲何應欽“此時直接回平又非得計,故只可以河北主席名義先到保定就職,而將分會事務逐漸移保維持三月,再另覓人替代,此乃爲今日惟一救國之道”。爲慎重起見,蔣介石同日致電閻錫山,徵詢華北應對方略,“華北事態急變至此,此中經過想尊處必略已有聞,瞻念前途,實深焦慮,如何應付,我兄老成謀國,卓見所及,切盼電示”。閻錫山對蔣介石的信任頗爲得意,強調“爲與否,當以國家大義爲準,不能爲威迫利誘所操縱”,當即召集趙戴文、徐永昌商議如何回覆蔣電,“結果以爲乘機取消北平軍政分會,使日在華北尋不見整個對象,則今後各省市縱受壓迫,亦只枝節或部分的,此意並電何敬之主持,免受整個壓迫”。閻錫山遂即致電蔣介石,主張裁撤北平軍分會與政整會,由何應欽主掌河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閻錫山所提由何應欽擔任河北省省主席的建議與蔣介石不謀而合,無奈何應欽再三推辭。6月23日,汪精衛詢問晉系駐南京代表臺林一,可否由徐永昌“犯難一往否?”徐永昌認爲如若他出任河北省省主席,有引火燒身之虞,斷然回絕,“當答以河北事難易及餘個人願去與否?均爲另一問題!蓋河北事果難,則誰去亦難,吾人於此時會,不應避難就易。今只就山西與日本交涉言,是否尚系兩重,若餘往,則恐有聯成一氣之虞”。閻錫山深以爲然,“立電汪,仍主敬之北來”。局面僵持之下,蔣介石決定商震執掌河北,汪精衛認爲“此次啓予(商震)任河北主席,百川(閻錫山)頗不滿”。爲安撫閻錫山,汪精衛乃建議“趙丕廉可調爲國府委員”,“可使百川安心也”。6月29日,汪精衛請趙丕廉向閻錫山特爲解釋,商震出自閻部卻又棄閻錫山而去,但畢竟同屬晉系,因此閻錫山當即表示商震“亦甚相宜”。\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局勢惡化顯然不止於此。1935年6月張北事件爆發,日軍本欲藉此逼迫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罷免宋哲元職務,調離二十九軍,但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等冀圖離間二十九軍與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及商震之間的關係,“謂如將宋軍他調,中央必另以他部填防冀察,反不如宋軍之可利用云云。惟關東軍始終堅持其主張,遂令土肥原向我提出免宋(宋哲元)及趙(趙登禹)師離察之要求,待我方照辦後,彼復將計就計,乘機挑撥宋與中央與商閻間之感情,不曰宋之免職令非出日方之要求,即曰商啓予曾電蔣委員長,對廿九軍表示不滿,此種伎倆近已逐漸施行,意在使我內部自生變化”。張北事件使得晉繫有脣亡齒寒之感。6月27日,徐永昌面見閻錫山,強調“察省關係晉綏較河北特甚,吾人安可坐視”,力主閻錫山向中央建議由宋哲元部屬秦德純出任察哈爾省主席,使二十九軍仍可掌握察省。閻錫山表示贊同,迅即致電中央,同時決定派黃臚初勸說秦德純,“恐其拘泥義同進退,不同意也”。二十九軍作爲西北軍舊部,與中央多有疏離之感,“罷宋案”使得中央與二十九軍之間的矛盾衝突更趨激化。爲避免二十九軍被調離華北,宋哲元心腹蕭振瀛建議與日本合作,“公開發表改變對日態度,主張中日合作的談話,這樣一方面緩和日本,一方面給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一個顏色看看。他認爲這樣做,‘官’一定會送上門來,而且官做得會愈來愈大”。27日,吳鼎昌向蔣介石密報:“宋部不願退出華北,正與日方接洽,仍分住察平保,並希望中央予宋以冀察綏靖主任名義,日軍方面認宋非國民黨軍系,且軍隊比較有力,逼走費事,樂得利用,似有諒解。”恰逢28日白堅武煽動豐臺兵變,蕭振瀛以平亂爲名,利用北平軍分會委員的名義,急調二十九軍馮治安部進入北平,順勢獲得北平控制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着二十九軍勢力從察哈爾拓展至北平,蕭振瀛與商震對北平控制權的爭奪日趨公開。蕭振瀛向中央明言:“商震何功?一日三遷!宋明軒(宋哲元)何罪免職?要求任宋以北平綏靖主任,渠爲北平市長”。商震與日軍關係本甚密切,但此時日本態度有所轉變,“惟近來日人態度似稍變,叔魯(王克敏)曾言:土肥原數日前在津約商之祕書劉繼昌往談,謂河北情形複雜,不易應付,商主席對此有何辦法?劉不能答。土續稱,商來津已逾半月,未見有何辦法,倘無相當把握,河北不如不就爲妙”。商震內外樹敵,壓力倍增,閻錫山極爲憂慮,“謂啓予不易就職,以日方既戲弄之於外,而萬(萬福麟)、宋等復痛惡之於內,前定五號就職,今已後推矣”。在商宋政爭的背景之下,閻錫山認爲黃臚初赴津與宋哲元聯絡已無必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日軍窺悉華北權力格局之關鍵,採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驅逐華北中央軍勢力,隨着《何梅協定》的達成,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在日軍壓力之下被迫禁止中央軍進入河北平津地區,因此中央毫無鉗制華北各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日方周旋於各方實力派之間,“一面勾結閻錫山,一面聯絡白崇禧,對閻則謂白已同意,對白則謂閻已同意”,“同時謀煽惑韓復榘獨立,以達其分化我整個國家之目的”,利用華北地方實力派爭權奪利的心理,引誘各方與日合作,“謂華北將來非由某某二公者,請一維持,所以政客又在各處奔走”,從而使得“華北全局對外陷於競賣狀態,對內近於火併狀態”。華北政局又因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拒絕北上,無人負責,頓失重心,華北各地方實力派密謀聯絡,北洋安福系、地方雜軍、西南軍閥又躍躍欲試,秩序混亂已達極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華北五省自治暗流湧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河北事件、張北事件的爆發,使得於學忠、宋哲元相繼被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免職,引發華北各地方實力\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派對\u003C\u002Fi\u003E自身利益的擔憂。韓復榘公開表達對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不滿,“魯韓近甚憤慨,認中央處理冀察事件失當,對人談省主席權不在國府,而在日軍部,日本不滿於學忠,中央就撤於職,日本不滿宋哲元,中央亦撤宋職,將來日本若對我不滿,中央也必撤我職”。他甚至對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信任喪失殆盡,認爲中央終將放棄華北,“數月來日人希望甚殷,倘我方長此敷衍,仍無具體辦法,恐陽曆年底,平津方面終不免釀成鉅變。屆時\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如置平津於不顧,則山東亦當受其影響”。他的擔心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華北各地方實力派普遍的生存焦慮。日本天津駐屯軍對此有清晰的認知,強調“迄今爲止,華北的各實力派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場上與中央\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打交道,其態度各異。然而,大體而言,都懼怕中央\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對其行使武力,在獨立問題上逡巡不前,難下決心。然而自河北事件以來,他們的對日依賴觀念逐漸加強”。日方雖對閻錫山出面組織華北自治運動多有疑慮,但仍試圖施加壓力,迫其就範。閻錫山面對華北政局重心缺失的混亂局面,亦開始試探性地與華北各地方實力派合作,意圖實現利益最大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晉系此前對日本的“示好”,態度模棱兩可,日軍頗多微詞。1935年6月,日本陸軍中央中國科科長大城戶前往太原拜訪閻錫山,“系代表日陸相與主任直接談判,問能否與日本提攜合作?主任頗難遽答,只好婉詞敷衍,談約三小時,大城戶不得要領,稍形不快”,日方對此大爲不滿。故而,當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武官高橋坦計劃再次赴太原之時,閻錫山爲緩解來自日方的壓力,態度開始發生變化。7月13日,閻錫山與徐永昌商討應對辦法,詢問是否應報告中央,徐永昌表示:“拒絕應有妥善之法,若來,則必須報告,其如何來一節,可任其自然,不必管其乘車或乘飛機也”。至於高橋坦所言華北經濟合作,7月9日閻錫山已知悉其內容,“其要點:一、開發山西東北南部各地礦產,建滄石線、大同通州秦皇島線、赤峯、承德、多倫聯絡北寧線等鐵路。二、開通內外蒙古生意。三、以現在滿鐵在山東種棉之資本爲基礎,圖向華北擴大,使日本棉供給不缺,不久即在天津設統制機關”。遲至8月3日,高橋坦才前往太原與閻錫山會談,徐永昌本欲提醒閻錫山,“注意彼來本有求於我,今因連日各代表之慫恿,應付間必至反有求於彼,猶之關賊於室內,此如何可者?”但當其觀察到閻錫山態度曖昧之時,亦不再多言,“主任似已動心,說又何益,彼左右誠多喜事而藉圖權利者,且此事與主任大不利,然主任果於不得已時出任艱鉅,於人民或有益也,總比石友三等出來強得多”。高橋坦爲誘惑閻錫山出面組織華北五省自治,甚至承諾由晉系幹部出任察哈爾省主席,晉系勢力可擴展至華北三省。閻錫山態度模糊,請部屬轉告日方,“閻先生出來也辦不了甚事,因爲韓等縱擁閻出,有利他們接受,有害他們不聽,徒毀閻與日,希望毫不能達到”,建議由日方“向我們中央要求閻先生出來負責”。日方“認爲有理,當本此進行”。8月8日,高橋坦向外界明言:“閻對華北問題,看測甚透,所論極足,予雖與閻晤談一次,而印象殊深”,強調“晉省之工業,將來之發展,與冀省農業改進之情形相埒,而與未來之中日貿易亦有重大關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外,日方意欲加強對綏遠的軍事、經濟滲透,並清除綏遠國民黨黨部勢力,高橋坦會晤閻錫山、傅作義之時,明確表示,“此後如有日人前赴綏蒙各地偵察等事,請予便利諒解,勿加干涉,但綏省府雖取締排日行動,然黨部爲排日機關,現仍存在,前次冀察事件中央與日訂約,業將平津冀察等黨部撤消,綏察立於同一線上,此事似解決,不應以綏未生事件而與華北各省不一致,要知華北諸省已全無黨部矣”,“近聞平綏路黨部又暗移綏遠工作,此事殊爲日方所難允許”。在日方的壓力下,8月6日,傅作義致電何應欽,請求裁撤綏遠國民黨黨部,“此次高橋又來正式口頭表示,情形勢已至決意之時,究應如何辦理之處,伏祈示遵”。13日,蔣介石在獲悉何應欽報告後,迅即命令葉楚傖、陳立夫,“綏省及平綏路等黨部一律自行撤消”。傅作義此舉不僅使得日軍無從尋釁,更藉此清除國民黨黨部勢力,免卻中央權力向綏遠擴展。至於日軍在綏遠的經濟滲透,傅作義則採取消極抵抗之策,“對於赴西北視察之日人行動密加註意,並通令所部防範日人查詢與努力使用國貨各問題”。\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在日方向晉系施加壓力,迫使其與日本合作的同時,各派勢力均欲拉攏閻錫山,以期在華北自治運動中佔據有利地位。華北各地方實力派爲使其五省自治更具“合法性”,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理論爲依據,“石曾主張晉、綏、察、魯對外之分治合作,即前此之分治合作是防內亂,今時是對外的。藉分治以緩和外交,藉合作以備萬一,因爲退讓,亦有限度,不到限度,一切隱忍。至不能忍之限度,合而與敵致命,其約略之意義爲排除障礙,不作權利分配”。1935年7月,韓復榘密派私人代表柴東生前往太原,與晉系展開聯絡。7月31日,柴東生向徐永昌表示希望閻錫山出面組織華北自治政權,“蓋中央已無力問華北事,吾人若不早自爲計,恐山東、山西禍患已到不遠,即咱們自己不有組織,等到日本對咱失望後,他隨便擁個任何無賴到北平,那時人家假日本力以臨咱,恐山東、山西也只好低頭服輸,所以韓先生意,與其坐以待斃,何如早自打算,不過今日之事,韓決無任何野心或權利思想,純爲華北自身打算,以爲請閻先生出任華北艱鉅,爲今日自救唯一決策”。8月1日,賈景德在閻錫山的授意下詢問徐永昌,“如仍北平現機關或將軍政兩分會合並,請閻先生出而領導之,惟須徐韓先見面一商步趨,柴意韓到平,太令各方先注意,詢有何善法?賈意餘(徐永昌)可借看汪,往青島,韓可到青相晤”。徐永昌表示最好不去青島,因柴東生曾言“可否慫恿王叔魯召集五省主席會議,彼(王克敏)正謀召集而未敢遽行者”,在北平與韓復榘會晤更爲合適。儘管徐永昌對華北五省聯合自治頗多疑慮,“五省問題,我不敢有意見,因爲站到國家方面看,前途太黑暗”,但顧忌同僚態度,最終仍勉強答應,“言下賈先生似很失望,然而即此,我也是勉強答覆,否則不定誤會些什麼出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王克敏自1935年6月出任政整會代理委員長後,爲見重於日方,計劃8月初在北平召集察哈爾省省主席秦德純、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山西省省主席徐永昌、山東省省主席韓復榘,舉行聯合會議,“商討關於促進中日提攜、開發華北產業、經濟合作諸問題,屆時關東軍將派代表參加”。8月13日,徐永昌從太原前往北平,入住協和醫院治病。王克敏初始擔心各省主席難以齊聚北平,王紹賢乃向王克敏明言:“徐現在平,韓與最密,即不召,渠(韓復榘)亦且來晤徐,至宋等,則皆在附近,韓既來,他人更無問題也”。此時晉系內部圍繞閻錫山主導華北五省自治一事展開討論。賈景德主張與韓復榘聯合,“至盼向方(韓復榘)出而倡行”;楊愛源以爲不可;徐永昌認爲,“如料日對華北無甚遽迫,則儘可以現狀安渡下也,若向方料日必將遽進,則所謀是亦有益於國家者,總之,對外交問題,餘素主由中央主持者,不過當茲非常之內外情況下,向方苟有利國主張,餘決以全力助之。”最終決定採取順勢而爲,以利害大小爲依歸。韓復榘的代表劉熙衆急於促成華北五省聯合會議,23日再次催促王克敏,“不然徐出院,即歸晉矣”。孰料28日行政院明令取消政整會,王克敏的計劃胎死腹中,但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未因此停止,“日本軍方仍舊試圖依靠宋哲元和其他軍事將領,努力擴大在華北的經濟、政治權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華北各省擁護閻錫山領導五省自治,可謂各懷鬼胎,即如劉熙衆向黃臚初所言:“宋、商是個擁閻的麼?韓是個擁閻的麼?反之數年來,閻何事能令人滿意,柴東生日前黃袍加身式的請閻先生答應出任五省首領,實則袍料在杭州還沒有織”。9月13日,韓復榘駐北平代表劉熙衆向徐永昌明言,“蕭仙閣有一種野心,即擬於一年內運用外交,以二十九軍統一華北”,認爲“商太滑(一方拉日,一方擁蔣),宋太蠻,(又以蕭仙閣能左右宋)無從提攜,縱使強合,徒增紛擾”,建議“似不如晉魯聯盟,作華北之砥柱,既可安內,亦可攘外,即以閻先生之耕者有其田爲主義,而漸行表見”,劉熙衆坦承:“如得晉方讚許,當歸語向方也”。14日,劉熙衆詢問徐永昌,如若贊同他所提主張,可否親筆致函韓復榘。徐永昌明確回絕,示意“此諸問題贊同則可,不願自主張也”。\u003C\u002Fp\u003E\u003Cimg src=\"http:\u002F\u002Fp1.pstatp.com\u002Flarge\u002Fpgc-image\u002FRXFjYwf1f0U4qu\" img_width=\"268\" img_height=\"262\" alt=\"賀江楓:華北自治運動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 inline=\"0\"\u003E\u003Cp\u003E日軍窺知華北亂象,認爲河北事件之後,各地方實力派“彼此相互聯絡,促進了與中央對抗的決心,這一點非常明顯。有鑑於此,我們判斷而今華北的獨立只不過是時機成熟與否的問題,而且華北獨立勢必影響到西南及其他各地的雜牌軍。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會給中國全國帶來重大變化”,加速推進華北自治運動。9月,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武官高橋坦前往張家口,“名雖視察特務機關,實系迫使華北改變局面”,向宋哲元部兜售華北自治計劃,“(一)先唱聯省自治,使華北事實上脫離中央。(二)第二步逐漸實現華北之獨立組織”。爲引誘二十九軍,土肥原特別主張華北稅收應由華北自治政權掌握,“第一步截留關鹽等各稅,年約四千萬,予中央根本上之財政打擊,以所截留之稅款,作華北建設公債基金,由中日僞市場發行公債,其規劃甚巨”,“此爲對軍人最大之誘惑,最易促成變局之原因”。經土肥原策動,蕭振瀛等主張籌設華北防共自治委員會,“魯方爲緩和蕭等急轉起見,在原則上主張須共同縝密起草研商,聞\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5\"\u003E三二\u003C\u002Fi\u003E日內劉熙衆代表來平”;“晉方自板垣派人催逼,去後尚無報告,但楊星如(楊愛源)派人來聲明,閻在可能範圍內,救國總不後人”。9月27日,徐永昌得悉華北防共自治委員會內情之後,立即向閻錫山彙報:“一、政整會取消,向方不能北來,劉熙衆二次來平,未伸前題,逕談華北局面,以爲商不可靠,宋有大欲,均難拉攏。爲消弭北方隱患計,莫若晉魯先確實團結,對內對外完全一致等語,我以爲此語完全系向方授意,蓋對商、宋交惡,各走路線,不能貫徹其原來主張,既感不快,藉此收場。二、華北革命委會(即華北防共自治委員會)之醞釀固出於關東軍對中國整個的壓迫,但宋、商雙方正在此幕中各有作用,故兩方面傳出消息都須斟酌,我於未晤宋、秦前,認爲出入尚多,是以不願輕下斷語”。\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宋哲元、蕭振瀛爲儘早實現華北自治,急欲拉攏閻錫山和韓復榘。10月2日,宋哲元拜訪徐永昌,提議與晉、魯合作,實現華北自治,“華北在日本壓迫、中央不管的處境下,不能不自己聯合,閻先生首領、向方副之,咱們大家幫助辦,實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我想請向方來,大家商議商議,大約十之六能來。”徐永昌不置可否,提醒宋哲元切莫因“一念之差,便身敗名裂,爲後世笑”。7日,宋哲元向韓復榘代表劉熙衆明言:“時局\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吾人不能坐視,誤國等於害國,向方最好來平一聚,熙衆到平,可請徐主席晚走幾天聚會聚會,說之再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鑑於宋哲元、韓復榘等各派勢力彼此各做主張、莫衷一是,此時無論是身處太原的閻錫山,抑或是北平養痾的徐永昌,均認爲由晉系主導華北自治根本無從實現,故而對待華北自治的態度又趨消極。10月10日,徐永昌向秦德純直言華北自治不可爲,“以一個武官或一個特務機關長指上幾個中國流氓擾亂的恫嚇,我們幾省即從之獨立,我們如此,河南、陝西亦如此,安徽、江蘇亦如此,是不是中國將來亡國,是被日本一個武官指揮上劉桂堂,即可臻事有餘。華北真要亡了,你我可以說是閻、宋、商、韓亡的,他人能不把你我加上麼?”事實上,晉系自中原大戰之後,實力已今非昔比,隨着二十九軍的異軍突起,晉系固守山西有餘,但掌控華北全局力所不逮。軍政實力的強弱仍是華北政治博弈最爲重要的現實規則。因此,保存實力、維持存在成爲華北各地方實力派行爲邏輯的關鍵,政治選擇往往具有投機性與多變性,尤其是面對力量遠超過自己的日軍與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爲避免引火燒身,地方實力派在抉擇之時往往更加謹慎與善變。日軍對此認知清晰:“華北各將領爲了自己維持將來的勢力,也深知與帝國提攜親善的合作十分必要。對於這種情況,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壓力和牽制也十分強烈,一旦和日本聯合、輕易和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公開背離的話,會被南京各個擊破,導致嚴重的後果。所以各個軍閥都是非和別的軍閥相聯合,否則就不會輕舉妄動,十分機智謹慎,他們都在逐漸變的青睞機會主義的做法。”\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面對日軍策動以及韓復榘、宋哲元的拉攏,晉系對待華北五省自治的態度,從初始的含糊其辭,轉向順勢而爲、主動參與,再至消極應付,看似反覆無常,實則均以現實政治利益爲依歸,閻錫山所言“看利大害小出負責,即利害相半亦爲之,如利小害大即不爲”也就不難理解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三、華北地方實力派內部分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華北各地方實力派彼此合縱連橫,尤其是在日方的壓力與策動下,自治運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乃至關東軍信心滿滿地認爲,“實現華北分離,用內部工作的手段即有達成目標之希望”。面對這一局面,蔣介石感慨:“華北局勢危急,其病尚在內部之將領不明利害,不知廉恥與輕重也”,迅即採取措施,以圖挽救華北危局。蔣介石對日方策動華北自治暗流並非毫不知悉,1935年7月5日,陳方向楊永泰密報:“日來北平謠言甚熾,撮要報告:(甲)閻韓商合作,推閻成新局面。(乙)中日經濟提攜後,日擬組華北國”。此後接連獲悉的閻日合作密報,使得蔣介石不免心生疑竇,“在華北出現一個像日軍期望的那樣主要領導人,看上去並非不可能,謠言迅速蔓延開來”。但是在華北地區現有的軍事格局之下,相較於宋哲元、韓復榘,閻錫山需要承受更多來自中央的現實壓力,“根據業已簽訂的《何梅協定》,中央軍禁止進入河北境內。同時依照濟南慘案先例,中央軍礙難出兵山東,否則日軍將派兵保護當地日僑。因此,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對冀魯兩省無能爲力”。日本對於山西的得失更爲憂慮,“但是值此之際,我日本帝國應該擔憂的是原東北軍和中央軍可能會從陝西和河南方向進入山西一事”。與此同時,中共紅軍先後抵達陝甘,晉綏毗鄰陝北,閻錫山倍感壓力,曾向蔣介石報告陝北中共“日來澎漲甚速”,而“日方對茲極爲重視,倘若澎漲,必以之藉口”,哀嘆“山曾迭次電呈,此任絕非孫楚所能事,仍請鈞座注意爲禱”。因此,當閻錫山處在日軍南下與中共、國民黨中央軍先後北上的三重壓力之下,抉擇之時更須考量中央態度。\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即便1935年7月,閻錫山決定與日方展開試探性接觸,仍舊不忘維持與中央的聯絡以獲取蔣介石的信任。7月18日,閻錫山致電蔣介石,“國步艱難,一得之愚,屢欲派員密呈,難得適當人選,可否由鈞座指派一人到晉,由山面請轉達”。蔣介石遲遲未予回覆,25日,他再次電蔣,請示可否派王靖國前往。26日,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王靖國“來川至爲恰當,徐次宸(徐永昌)身爲主席,現值華北外交\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閻未必準其遠離,現既派王前來,故覆電準之”,蔣介石當即允准。邵元衝27日抵達太原,閻錫山向邵元衝坦言,“日寇中無賴浪人,近屢來晉糾纏,作不負責任及無聊之語,並散佈與晉已默契之風說,甚爲煩悶”,希望中央對日外交“總應確定一方針,即究竟退讓應至若何限度,對地方負責者亦應明示應付辦法,否則,枝枝節節,地方當局頗感困難也”。8月3日,王靖國啓程南下,此行目的“除報告對外態度竭誠擁護鈞座外,並攜有清折一具,內系孫楚部赴陝北‘剿匪’應需款項數目”。閻錫山希望以擁護中央爲籌碼,換取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財政援助,蔣介石悉數應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時,晉系內部對與日合作實施華北自治意見不同,但主張向中央靠攏者不乏其人,閻錫山對此亦須有所考量。徐永昌向閻錫山明言,山西擁護中央“其目的在安定國家、安定山西及進行其建設,非徒以擁護中央、助蔣爲目的也,希望主任以目的爲前提,華北危機的解決應待中央作最後決策,“因爲日本國策在不要中國統一,凡是有統一力量的,日視之都如蔣,知己知彼也有分際,如做盾的不能聽做矛的話,所以無論地方及中央,對外交只論應做與當做而已”。8月29日,綏遠省省主席傅作義又向蔣介石詳細解釋拒絕對日合作內情,“職前次到並(太原),日武官高橋晤閻主任及職,面提爲防止赤化,擬在綏設連絡員,經答以防止赤化,我中央已有整個辦法,綏省刻正積極防遏,以絕蔓延,日在綏設任何名義之人員,均無權允可,須請示中央”。\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於蔣介石與閻錫山關係而言,蔣介石嫡系吳鼎昌等人先後向蔣介石力陳,中央惟有與晉系合作,方能穩定華北。1935年8月6日,吳鼎昌致電蔣介石,直言“閻百川對日持負責應付之態度,日方誘其反中央,單獨妥協,閻已明白婉拒,故日方對閻不滿,北方今日閻爲最識大體、有責任心之人,望公與之密切籌商,示以機宜,囑其負責應付”。正因如此,蔣介石對閻日合作的疑慮大爲消減。蔣介石逐漸認識到“華北形勢可危,其受倭煽惑,爲中華禍首者,恐不在冀晉而在魯乎”,一方面“對華北各省明告其方針與其各人之地位”,並請沈鴻烈“勸韓以大義與利害”;另一方面迅即展開對閻錫山的爭取與安撫,試圖將華北五省聯合自治各個擊破,消弭於無形。\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0月12日,蔣介石接獲張學良來電,“談閻頗有覺悟,態度極佳”,當即致電閻錫山翌日飛晉,“與兄相敘,如時間許可,擬當日回豫,萬勿有所招待,免人注目”。13日,蔣介石“由開封起飛,十一時半到太原,下午與閻、趙協議各種注意問題。百川對土地問題,自信在山西有實行之把握,餘未與詳討,但確有解決之必要,唯此時對共俄與外交關係,亦不能忽諸,談至晚深十二時始息”。蔣介石向閻錫山明言:如果閻錫山能夠說服華北將領,團結一致對外,可請閻錫山負責華北全局,並且該項工作所需經費由中央承擔。此外,中央將賦予閻錫山統理華北外交、財政的全權。閻錫山考慮到山西經濟蕭條,接受中央援助政策有利無弊,決定出席南京全會。蔣介石對太原之行極爲滿意,“冀魯與華北之動搖與對倭之方略,皆得由此巡視豫晉之一行而定,頗以自慰”。15日,蔣介石致電熊斌,令其轉知宋哲元、商震,“閻主任態度光明,志意堅定,絕非已往之時可比,中可斷定晉綏決不爲日方威逼利誘所能屈,其對華北全局自甚關切,但彼決無領導華北之意。惟請明軒、啓予兄隨時與之切商,並推重之,俾得精誠一致,勿爲日方間言所動,而且彼多有獨到之見地也,只要華北各主官團結堅忍,則彼即無所用其技矣”。\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5年10月21日,晉系駐南京代表李子範向閻錫山報告,“日方對某公到晉頗多猜忌,近日此間報紙載有鈞座於開會時將來京一行,此言由何處造出,不得而知”,閻錫山仍決定飛赴南京,參加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於26日分電韓復榘、宋哲元、秦德純等,“山應蔣委員長之約,定於宥日乘機赴京,知關愛注,特電奉聞”。蔣介石對閻錫山赴南京參會,極爲重視,22日致電孔祥熙“代爲照拂”。國內輿論界聞悉閻氏南下,悉表歡迎,《大公報》發表社論:“閻爲北方重要負責之軍政領袖,際此華北阽危,特入京出席黨國幹部之會議,又儼然十七年共同負責處理國事之精神,凡渴望全國同心協力撐持危局者,當無不引以爲慰也”。26日,閻錫山抵達南京,蔣介石稱讚“百川到京表示共赴\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1\"\u003E國難\u003C\u002Fi\u003E之決心,其晚節自勵,殊爲可慰”。29日,蔣介石與閻錫山“談話兩次,研究外交問題,對倭應主動與之談判,及對國民宣佈方針,至最後不得已時,決心爲最後之犧牲,如此或可轉移倭寇外交之方針”。\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就在晉系與中央關係日趨緊密的同時,二十九軍卻因華北權力分配問題與蔣介石的矛盾日趨激化。隨着二十九軍勢力擴展至北平及河北,何應欽主張由宋哲元出任駐平綏靖主任,如此或可使得華北局勢趨於好轉,“職意認爲與其某方勾結漢奸及過去軍閥政客組織所謂華北新政權,毋寧即以明軒爲駐平綏靖主任,使負北平察省軍事治安之責”,“且明軒人尚忠誠,頗識大體,鈞座力加拔擢,崇其位置,必知感激圖報,較之吳佩孚或其他不相干之人出而維持,似爲利多害少”。蔣介石認爲此舉將使得中央對華北之影響更形式微,明確拒絕宋哲元出任駐平綏靖主任的提議,“故駐平綏靖主任之設置,不惟對內對外,皆無益處,且徒多糾紛,轉爲對方造一壓迫挾制之對象,以明軒性情之忠誠耿直,必不甘長期忍受外人之侮辱,則最後必仍蹈此次華北事態之故轍,而更形慘酷狼狽,當可想像而知,決難久安其位,故爲國家之利害得失,爲明軒個人及爲愛人以德之道義計,此舉似皆不相宜”。同樣,對於蕭振瀛覬覦北平市長,蔣介石亦有意阻止,明言“蕭事,當緩處之”。宋哲元因此“不免有怨望之聲”,高橋坦又極力挑撥蔣宋關係,聲言“明軒當日反抗日本,今漸知日本可恃,中央不可恃”,使得中央“疑宋哲元輸誠日本”。蔣介石爲避免二十九軍倒向日本,10月12日與宋哲元代表王式九密晤,向其保證中央必爲二十九軍後盾,“如明軒不能在河北佔住,則可退河南,我將河南給他,再不然可退陝西,必將陝西給他!”然而事與願違,蔣介石此舉非但未能起到安撫華北將領的作用,反而使二十九軍與中央關係更趨疏離。宋哲元聞悉王式九報告“大譁”,怒斥蔣介石毫無誠意:“蔣言大半爲詐,小半爲實,且似始終未以華北爲念者,且對事實問題皆未談及,看起來,我們只能自行救華北矣”。蕭振瀛與日方密謀合作,意欲使北平市市長袁良去職,由其執掌北平,局勢急劇惡化,待至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宋哲元、韓復榘明確拒絕南下,並通電要求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結束訓政。與此同時,30日,日本駐華使館參贊清水董三面見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出示天津日本總領事川越茂第226號公函,要求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實施如下三項要求:罷免北平市長袁良;裁撤北平軍分會;嚴格履行《何梅協定》、禁止排日活動。11月4日,天津駐屯軍參謀中井增太郎向商震代轉參謀長酒井隆口頭警告,要求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迅速落實川越公函各項要求,否則“我方取自由行動,其責任則應由貴\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負之,特此預爲通告,即請轉達貴\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華北自治情勢急迫,已到最後關頭。”\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閻錫山與中央旗幟鮮明的合作,使得晉系面臨的日軍壓力劇增。“土肥原到津策動北方獨立甚急,並稱將派機轟炸太原,以懲閻之南下。”閻錫山鑑於蔣介石對日態度日趨強硬,頗多疑慮,乃至“閻先生似悔南京之行”。爲消除閻錫山顧慮,11月24日,蔣閻再次會談。閻錫山表示:“彼對華北願負其責處理”,蔣介石認爲,“中央對華北既不能派兵鎮攝掌握,又爲倭寇藉此以威脅,使全國政局求久不定,則不如另派百川,交其全權,使之應付,以謀一時之相安,如能耐過明年,則困難可以渡過矣”。25日,殷汝耕、石友三率領便衣隊佔領津沽保安司令部、天津市市\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殷汝耕又自行宣佈成立冀東自治\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宋哲元部屬雷嗣尚致電何應欽,建議中央默許華北自治,蔣介石憂心如焚,“聞宋哲元由津回平,土肥原亦已到平,可慮也”,旋又打消由閻錫山主掌華北的念頭,改令何應欽北上出任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本日爲處理華北與人事問題甚費研究爲難,決心以華北全責交閻,但因事急,不能發表,甚歉也”。顯然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認爲,由中央\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親派大員在華北設置一個新的行政機關,要遠比在日軍壓力之下形成的反對中央\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指令的地方政權更可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此時晉系與宋哲元等其他華北地方實力派在對日問題上,均主張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閻錫山聲稱:“一個人犧牲可以,若以國家民族來犧牲則不可。”乃至馮玉祥直斥“此話實大有病在,即秦檜一流之話也”。晉系與宋哲元、韓復榘的歧異主要因中央與華北地方關係展開,閻錫山主張中央主導華北對日交涉,宋哲元、韓復榘試圖依靠華北自治謀求生存發展。晉系與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互動更趨積極,不僅因爲晉系內部徐永昌、傅作義等人強烈主張向中央靠攏,更緣於日本與華北地緣政治的複雜作用。日軍兵臨平津城下,宋哲元、韓復榘感觸到的日軍壓力遠較閻錫山爲烈。同時,受制於濟南慘案日本出兵山東的先例及《何梅協定》的苛刻限制,相較於河北、山東,中央軍進入山西的顧忌要少得多,而中共北上陝西,又成爲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以“剿共”爲由制約晉綏的重要砝碼。賈景德明言:“韓、宋等之醞釀,中央已有所聞,蔣令‘剿匪’軍追止於甘境,若閻主任出總華北軍政,蔣先生真能驅‘匪’於晉。”由此而言,閻錫山與華北其他各實力派立場迥異,也就有跡可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四、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935年11月3日,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宣佈實施幣制改革,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認爲法幣改革將威脅日本在華北的經濟利益,主張加速推進華北自治,“最好讓華北各省在經濟上與南京中央\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分離,除此之外別無良策”,12日,致電東京陸軍參謀總長,幣制改革“爲我方華北工作提供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我們對此深信不疑。事已至此,痛感日本陸軍中央及派出機構有必要齊心協力,盡最大努力”。在日軍加速策動之下,蕭振瀛與多田駿、土肥原密議,“發誓要和日本合作,但是需要駐屯軍給予指導”。18日,蕭振瀛在北平向報界表示,由於“日方要求立即實行,已商定展至號(20)日爲止,否則日軍當自由行動”,華北自治機關“暫定爲華北防共委員會,宋爲正委員長,韓副之,包括華北五省三市”。\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爲阻遏華北自治,迅即調兵北上河南,試圖向華北各地方實力派施加軍事壓力。在此背景下,不僅閻錫山倒向中央,韓復榘態度亦發生變化。據何思源密報,11月10日,日本武官花谷正攜帶蕭振瀛起草的“五省防共會議章程”前往濟南,要求韓復榘簽字贊同,“韓當時拒絕,經花谷再三要求,韓始允於‘五省防共’之條件下承認,但若缺少一省,或改變防共性質,則不受承認之拘束。當時韓與花谷及第三人某君均簽字作證,花谷滿意而歸,韓大罵蕭,謂不應聽此無賴人之言,妄爲舉動”。在經沈鴻烈勸說後,韓復榘向中央保證“決不聽日人之言前往平津,並不與彼簽定任何協定,請爲放心”。日本內閣命令駐華大使有吉明11月20日赴南京與蔣介石直接交涉,試圖以華北自治爲由,逼迫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在“廣田三原則”等問題上作出更多讓步,華北五省聯席會議無果而終。但有吉明與蔣介石會談未達日方預期,日本陸軍中央強烈反彈,認爲“蔣介石接受了此前由廣田外務大臣提出的三大原則,但是又以此作爲日方敦促華北實力派取消宣佈華北自治的條件,可謂居心叵測”,經與外務省、海軍省協商,決定命令關東軍、天津駐屯軍繼續推進華北自治運動,“應通過對華北實力派進行適當的指導,促進自治運動的實現。通過讓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加深對華北的認識,來促進其糾正對日態度”。宋哲元在日軍壓力之下,29日致電蔣介石,希望中央贊同華北自治,“近日徵詢多數意見,有主張如能在中央系統之下,\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予以適應環境辦法,既不喪失主權,亦可應付艱迫外交,是否可備採擇”。\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如何安撫二十九軍,實爲阻遏華北自治運動之關鍵。閻錫山深窺其間癥結,向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坦承:“年來華北情形,還價每比要價高,此次\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緊張\u003C\u002Fi\u003E,其焦點亦在內而不在外”。11月28日,宋哲元致電閻錫山,俾有所聯絡,“我公回並,華北有所依賴,北平環境困難,應付之術俱窮,請公指示一切,俾有遵循”。閻錫山當即轉告中央對日政策,“中央對日決照委員長之宣言辦理,提攜親善確具決心,我兄艱苦支撐,山在京時同人均表欽佩,此後對日希望在華北武官拋棄壓迫做法,走入協商途徑,刻正在交換意見中”。次日,閻錫山召集徐永昌、傅作義至太原會商,徐永昌“對最近河北時局及當局應付經過,均將有所報告”。30日,閻錫山決定派黃臚初親赴南京面見蔣介石,“對明軒務盡力於消除隔閡工作”。徐永昌向黃臚初強調此舉意義重大,“宋今時似走入不應付日本自治,即須與日拼,自治則中央不許,拼則恐失敗後中央亦不收容,是華北之危險不完全在外也,所以中央對宋極需要急做消除隔閡工作”。12月4日,黃臚初向蔣介石轉達閻錫山意願,蔣介石當即承諾“如與日人決裂,以後官職、地盤、軍餉毫不使其喫虧,並請閻先生擔保,今擬定如明軒被迫不能立足,當擔保以綏遠省畀之,其本人畀以察綏綏靖主任”,希望閻錫山“代爲表示,並言我不負閻,即不負宋,可作兩層保障”。閻錫山希望“先派妥人賚回委座親筆書及稟函”,7日,黃臚初電閻,“今已上車,但鈞座如感覺時局喫緊,可即照支酉電對明軒表示,委座意甚堅,盼速辦,不必候手書也”。\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二十九軍與晉系各成系統、互不統屬,並且張北事件之後,“宋哲元痛感到身前背後沒有靠山,十分寂寞,其所處的立場是將來不得不與日‘滿’合作,以尋找打開局面的良策。宋哲元察覺到華北形勢的變化,不失時機地就任平津衛戍司令。與此同時,宋哲元還通過收攬華北民衆的人心,企圖擴大和加強自己的勢力”。隨着蕭振瀛與日本勾結日趨緊密,宋哲元頗有騎虎難下之勢,況且綏遠本屬晉系勢力範圍,在視地盤如生命的邏輯之下,即便閻錫山書面承諾將綏遠劃爲二十九軍的後方基地,在宋哲元看來不過是虛妄之言。即如雷嗣尚向傅斯年所言:“你們不要拿宋哲元當聖人看,他是要地盤的,若非與日本勾搭,早調走了!”更不用說,宋哲元的權力訴求遠非一紙保證所能滿足,正如何應欽在致蔣介石的電文中所說,“此間一部分人(如蕭仙閣等)擬在北平設一仿西南成例之政務委員會,在此預定之政委會成立後,擬與日方訂三個協定”,以期遊走於中日之間,希冀最終在華北政局中佔據主導地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爲應對日軍策動的華北自治,1935年11月30日,蔣介石決定督促何應欽北上,出任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相較於此前廢除的北平軍分會、政整會,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的權限更爲廣泛,權力亦更加集中,其施政大綱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人事諸多方面。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希望其予以協助,“日來華北情勢尤急,中央現授權敬之部長體察情形負責處理,頃已登車北來,同行者有陳公俠、熊天翼、殷桐生諸兄,特電奉聞,並希隨時逕與電洽”。12月1日,閻錫山向何應欽表示將予以全力支持,已囑石華嚴“就近晉謁臺階,如有囑件,請即令其轉達爲荷”。此時,日本陸軍、海軍、外務三省已分別致電在華各機關,“值此之際,如果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派大員去華北的話,會使得事態更加糟糕,有害無益,最好終止派遣大員北上的計劃。當然,即便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的這些要人向我日方提出面談的要求,也要謝絕。對這些要人逗留華北期間提出的要求,決不能答應”。何應欽計劃依靠陳儀、殷同等“親日派”與日本交涉的企圖,無從着手。3日,日本陸軍省致電關東軍、天津駐屯軍,命令日軍阻止由何應欽等南京\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要人處理華北時局,避免與何應欽會談,同時要求華北地方各實力派與日方保持一致態度,最終令何應欽放棄北上執掌華北政局的想法。4日,高橋坦向北平軍分會代表周永業提出警告:“如何部長久在此地,恐生衝突,而成地方上之混亂狀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宋哲元認爲,如若他明確反對華北自治,日軍必然用武力將二十九軍從華北清除出去。同時鑑於何應欽北上並未攜帶任何具體計劃,無益於改善宋哲元的地位與境遇。故而,宋哲元對何應欽北上看似歡迎,實則抵制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的設立。12月5日,北平爆發市民自治請願遊行,“聞此亦宋系之平市府自治監理處長呂均等包辦,報界認爲系演雙簧,經密詢道揚,亦不否認”。何應欽在內外壓力之下,決定向日方妥協,放棄出任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的計劃,改由宋哲元組建冀察政務委員會,7日,蕭振瀛就冀察政務委員會籌設等問題赴津與日接洽。日方強調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是與政整會類似的機構,“設立上述機構無法適應華北的現狀,反而有可能增加事態的複雜性”,主張地方實力派組建在地政權,但礙於英美態度,希望華北自治“應儘量避免採取過於強硬的手段,如果迫不得已,目前實現類似西南地區的自治也是日方能夠忍受的”。蕭振瀛赴津與日軍溝通,日方並未予以否決,“首先應該承認這一委員會的成立,今後對其運營進行善意指導”。冀察政務委員會迅即成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伴隨着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籌設,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在華北政局內部被徹底邊緣化。因“宋商之間不甚融洽”,宋哲元堅決反對商震留冀,“只允商軍仍駐河北”。商震則針鋒相對,主張何應欽留駐北平,反對組建冀察政務委員會,12月7日致電蔣介石:“聞何部長到平後,蕭、秦等主張以冀察政委會代替僞自治,名義雖有不同,兩省仍同斷送,此種辦法震意竊不贊同。”與此同時,商震亦向閻錫山表示此時華北政局“最要關鍵,總望何部長勿急謀解決,輕離北平,以留迴旋之餘地”,請求閻錫山“速與蔣委員長電商,另謀解決方法,或電何部長加以指示”。閻錫山當即密電駐平代表石華嚴,“希密陳何部長,可否採納啓予之建議”。隨後,閻錫山又致電蔣介石,反對何應欽南下,認爲“如果回京,世人不察,必謂無辦法而歸,一則示弱,二則\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今後處置不易,華北事件善後更難”,強調“敬之兄南歸關係甚大,請鈞座注意及之。弟意對敬之兄在北平之困難,應極力設法援助,務期華北事件在敬之兄此去中,求解決之方”。爲安撫晉系,蔣介石向閻錫山表示,“中央社所發佈敬之日內南歸消息,原屬暫時和緩彼方,轉移目標之一種作用”。\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12月8日,閻錫山獲悉冀察政務委員會接洽已獲結果,由宋哲元擔任委員長,“範圍爲冀察兩省平津兩市,組織大綱約與黃膺白政整會情形相同,如有單行條例,仍須請準中央施行,商將辭冀主席,有以蕭繼任之說”。次日,何應欽致電閻錫山,將北上內情相告,“弟此次北上本先與委座約定不就駐平長官之職,只將冀察事件處理告一段落即行回京,到平後,連日與宋秦蕭諸人詳談,決遵委座指示之最後辦法:(一)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二)委員及組織由中央決定,人選以適宜於北方環境爲主,並任明軒爲委員長。(三)一切軍事、外交、政治、經濟保持正常狀態。(四)絕對避免自治名目及獨立狀態”。閻錫山仍勸何應欽“毅然就駐平長官之職,始可以穩定將來,善後已往也”。9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告知冀察政務委員會設置原則與組織大綱,“蓋應付目前環境,穩定內部爲先,對外顧慮尚屬其次,非先謀一下臺地步,亦殊難釜底抽薪”,“如日人壓迫,中央與地方一致行動”。閻錫山明白此時大勢已定,難以挽回,但特別就商震歸屬詢問蔣介石,“否則恐愛國者望而卻步”。11日,蔣介石致電閻錫山,告知華北人事安排,“啓予兄調河南主席,明軒接河北主席,張自忠任察省主席,蕭振瀛調天津市長,劉經扶(劉峙)改派豫皖綏靖主任,以上組織大綱及人事更動均擬於今夜發表”。商震既已改調河南省\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主席,閻錫山亦不再多言,表示“只好如此,請鈞座注意善後爲盼”。\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何應欽強烈反對商震南調,認爲鑑於《何梅協定》對中央軍北調的限制,如若商震南調河南,三十二軍“決難留河北,於將來國防上影響甚大”,“河北兵力單薄,一有事變,其他部隊又難調集,殊爲危險”;並且商震南調將加劇宋哲元與中央的矛盾,“宋部下每謂中央袒商抑宋,從前察省事件,中央免宋職後,兩月餘始予以衛戍司令之職。今若立即發表啓予爲豫主席,益予宋部下以口實,徒使其對中央發生不良印象”。蔣介石向何應欽坦言此舉重在安撫晉系,“啓予離冀而不以豫省主席位置,無論對內對外、爲公爲私,皆於理不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隨着商震及三十二軍南調,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受制於《何梅協定》,再難向河北增派軍事力量,宋哲元悉數掌握冀、察、平、津四地主導權。面對中日與蔣宋多重矛盾糾葛的現實,宋哲元利用《何梅協定》後華北“特殊化”的狀況,多方折衝,最終使得二十九軍迅速崛起爲華北舉足輕重的力量。12月12日,蔣介石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承認:“事實上華北已經不是受中央統治的地方”,並且“中央已經只能希望宋哲元幾個人聽命令,並不能命令他們!”閻錫山此前請蔣介石手書“對於明軒將來之實力與地位及官職等,必當確實爲之保證,決勿令其失望”,已屬毫無必要。當黃臚初派人至北平送來蔣介石函件時,閻錫山感嘆“事過境遷,能否說起”。 \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結 論\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華北自治運動是內政外交雙重因素交互影響的產物,不僅是日本有預謀地蠶食華北、實施其侵略中國計劃的重要步驟,亦是1935年6月《何梅協定》達成後,在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對日妥協的背景之下,華北政治失序、中央與地方矛盾衝突激化的結果。事實上,南京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自建立後,始終無法在華北實施全面有效的管轄,必須與地方實力派合作,方能維持中央在華北的政治權威。而地方實力\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4\"\u003E派對\u003C\u002Fi\u003E地盤與軍隊的\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2\"\u003E關注\u003C\u002Fi\u003E,與中央急於實現華北地方的中央化,形成華北地方政治的結構性矛盾。1935年華北危機的爆發,使得中央與地方的結構性矛盾在日軍侵略的外在壓力下,被急劇放大,難以調和。中日實力懸殊,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面對日軍蠶食華北,妥協退讓,毫無止境,特別是河北事件、張北事件爆發後,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在日軍壓力之下,被迫答允于學忠、宋哲元免職他調,不僅引發華北各地方實力派的生存焦慮,“北方軍隊之心理,深懼退過黃河,地盤一失,餉項無着,人各有心,何能持久!”更使得華北政治秩序紊亂,進而使得華北危機逐漸從外交傳導至內部的政治衝突。馮玉祥向蔣介石建言:華北事件的解決,重在收軍心、安地方,亦是此理。\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日方爲推動蠶食華北計劃的順利實施,有意挑撥中央與華北地方實力派的關係,使得彼此衝突日趨惡化。商震與宋哲元矛盾衝突、蕭振瀛與中央交惡,日方暗中策動,亦是重要原因。“蕭爲人粗暴,惟利是視,前欲爲北平市長未償,其願欲爲察省主席,而中央則發表張自忠代理,蕭認爲中央故意離間,又以高橋所造商氏請蔣公扣留蕭氏之僞電,遂變本加厲,詆譭中央無所不用其極。”中央與地方的結構性矛盾,成爲國民\u003Ci class=\"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 chrome-extension-mutihighlight-style-6\"\u003E政府\u003C\u002Fi\u003E控制華北難以克服的關鍵性因素,亦是管窺抗戰時期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重要路徑。\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者簡介:賀江楓,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來源:《歷史研究》2019年第1期\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17634869989474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