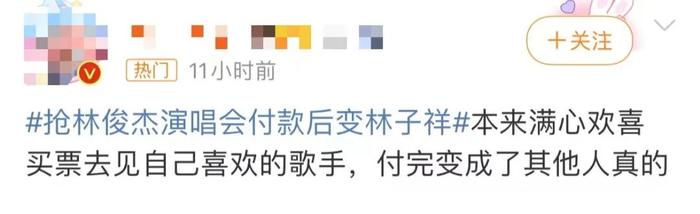這樣的侵權演出請少一點
摘要:\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不少中國當代作曲家創作的作品在創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上演,作曲家費盡心血創作出作品,能得到的版權費並不多。\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代作品常被“侵權演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說起自己的作品差點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上演的事,作曲家鮑元愷到現在都很氣憤。
"\u003Cp\u003E每當你坐在音樂廳中欣賞《紅旗頌》《炎黃風情》等當代作曲家的交響名作時,是否意識到樂團演奏這部作品前,需要先徵得作曲家的同意?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員、演出單位)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並支付報酬。\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事實上,不少中國當代作曲家創作的作品在創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上演,作曲家費盡心血創作出作品,能得到的版權費並不多。古典音樂領域版權保護意識有待加強。\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當代作品常被“侵權演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說起自己的作品差點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上演的事,作曲家鮑元愷到現在都很氣憤。那是去年年末,鮑元愷聽說上海民族樂團將與臺北市立國樂團在上海演出一場《臺灣音畫——上海臺北雙城樂展》的音樂會,演奏內容包括他創作的《臺灣音畫》,可演出方從沒向他透露過要演出這部作品的消息,鮑元愷也從未向演出方授權。而且,該音樂會的售票廣告頁上出現了《臺灣音畫》八個樂章的名稱,卻唯獨沒有出現作曲家的名字。\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發現這件事後,鮑元愷只得寫公開信詢問。對方看到公開信後發表聲明,稱上海民族樂團與臺北市立國樂團事先簽有協議,“雙方應各自保證擁有所演出曲目的合法權利或授權”,“但遺憾的是,雙方對於誰來落實版權相關問題有不同的認知”,隨後宣佈取消音樂會。“樂團雖然自行取消了演出,但不是自知理虧,反而覺得這個損失是我造成的。”這件事不了了之,鮑元愷依舊憤憤。\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公開商演作品卻不先徵得著作權人的同意,就已等同侵權,這樣的情況在國內並不少見。“就拿作曲家呂其明創作的《紅旗頌》來說,每年不知有多少個樂團會演出這部作品,逢年過節都會演,但很少有人會想到先徵得他的同意。”從事音樂會演出的資深行業人曾偉說,雖然呂其明本人並不介意樂團演奏他的作品,也不一定收取版權費,“但不意味着樂團可以隨便演,事先徵求同意是對作曲家起碼的尊重。”\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頂尖作曲家版權收入也不高\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演奏方不願意在事先聯繫作曲家並向其支付版權費,是因爲這項版權費很高嗎?答案並不是。\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作曲家郭文景介紹,按照國際慣例,想演奏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或是徵求本人同意,或是向正規出版樂譜的出版社尋求有償租賃樂譜。音樂作品版權分爲大版權和小版權,歌劇作品屬於大版權,音樂會作品是小版權,價格其實並不高,“一首二三十分鐘的作品,演一場一般都在2000元以下”,最終以演奏的場次爲單位結算。“收入的多少與被演出的數量有關。”郭文景說。\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不過,即便是中國目前最著名的這一批作曲家,他們得到的版權收入也不高。鮑元愷創作的《炎黃風情》《臺灣音畫》等作品在國內演出次數極多,在這種情況下,他每年能通過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得到演出方支付的幾萬元費用,“演出次數太多了,確實單次版權費不高。”而作曲家陳其鋼在近日舉辦的2019中國樂團藝術管理論壇上透露,自2011年至2019年上半年,他的作品在全世界範圍內演出共收到版權費摺合人民幣約81萬元,其中在中國收到的只有1.3萬元。\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對於那些沒有事先徵求同意就上演的“漏網之魚”,作曲家也很少去主動維權。用鮑元愷的話說,“作曲家都很忙,尤其是處於探索中的中國作曲家,沒有精力打官司。”曾偉透露,打官司維權需要的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很高,最後獲得的賠付也就只有幾萬元,作曲家也就不願多這個麻煩。\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規範使用樂譜靠行業自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侵犯著作權的行爲之所以還存在,不少業內人士表示,這是個“歷史遺留問題”,想改變需要全行業自律。\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早年間,由於樂譜出版較少或溝通不便等原因,一個樂團想演奏某一部作品卻拿不到譜子,就有人根據唱片裏的旋律把它轉化成樂譜,再供演奏員演奏,被業內稱爲“扒譜子”,其實就是盜版。“當時幾乎每個團體都有專業扒譜子的,不同的人扒出來的譜子不同,有些作品就出現了各種版本,其實都不規範。”曾偉說,現在演出市場上不少名爲宮崎駿、久石讓作品的音樂會,演奏的譜子很有可能是“扒”來的,包括演出時大屏幕上播放的電影、動畫畫面,可能都未經過授權。\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在國內,這樣的侵權行爲多數處於“民不舉,官不究”的狀態,但指揮家譚利華指出,國外對不規範樂譜的管理非常嚴格,甚至不能使用複印或手抄的樂譜登臺。“我帶團在國外演出時,會有當地工作人員上臺檢查樂譜。”譚利華說,演奏員有時覺得原版樂譜字太小不方便看,如果用了複印樂譜,那也一定要帶着原版的譜子,向對方證明自己的譜子是正規出版物或已得到授權,“否則樂團會受到嚴厲處罰,甚至終止演出。”\u003C\u002Fp\u003E\u003Cp\u003E業內人士也表示,可喜的是,古典音樂圈兒的版權意識近年有日漸加強的趨勢。各院團在向作曲家委約創作作品時,版權保護條款往往明確寫在委約合同中。“比如委約作品的版權如何歸屬;在作品誕生多少年內,約稿的樂團擁有優先演奏權;在經過一定年限後,其他樂團想演奏這部作品時該向誰取得同意,這些都會寫明。”譚利華說,雖然不是所有樂團和作曲家在委約時都能做到簽約細緻,“但這是個時間問題,當大家都自覺做這件事了,版權意識也就建立起來了。”\u003C\u002Fp\u003E"'.slice(6, -6), groupId: '6720195570616500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