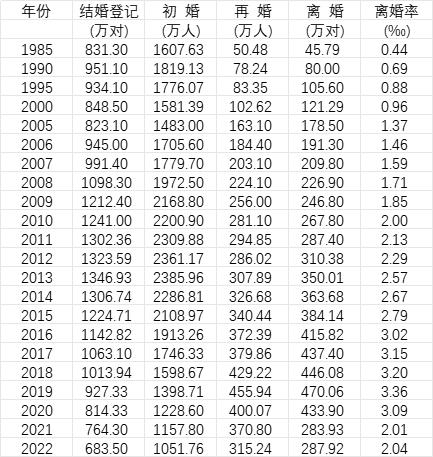官宣!比起明星結婚刷屏,這纔是最該登上熱搜的愛情!
原標題:官宣!比起明星結婚刷屏,這纔是最該登上熱搜的愛情!
九九重陽,因爲與“久久”同音
有長久長壽的含意
自古以來
我們對重陽節就有着特殊的感情
今天是重陽節
是全國第6個法定“老年節”
也是上海市第31個“敬老日”
今年
普陀區桃浦鎮開展了“尋找金婚老人”行動
經過各居、村委排摸
全鎮共找到100對金婚老人
其中有一對金婚老人的故事特別有意思
今天就讓我們在這個特殊的日子
聽一聽他們五十年來相濡以沫的故事吧
這對金婚夫婦
當年“處朋友”兩個月就“閃婚”了
而且還是女方先開的口
在結婚登記處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一眼相中,兩個多月“閃婚”
賀瑞起和李玉珍夫婦年輕時響應國家號召支援邊疆,同在新疆兵團農業師三團機關工作。賀瑞起在組織科擔任內勤,李玉珍則在保密室當保密員兼管各科室文件。兩人之間常常因工作關係互相傳遞文件,一來二去漸漸熟稔起來。
老夫婦回憶,真正確認戀愛關係,多虧組織科於大姐牽橋搭線。說起這一切,李玉珍還有些羞澀:
李玉珍
那時候,我愛人在於大姐手下工作,不知道爲啥她越看越覺得我倆有戲,1967年元旦,就主動來問我有沒有對象。
當時不能將戀愛處在明面上,如果拉拉手、多說幾句話,都會被說成作風問題。
於是,性格爽朗的李玉珍開始和賀瑞起試着相處。經過兩個多月接觸,她感覺賀瑞起這個人值得託付,竟主動提出結婚。
當時,男方貧農出身,女方工人階級出身,兩人又是黨員,政治背景沒問題。
李玉珍
當時也沒像現在這樣,處對象要很久,感覺對眼,就定下來了。
他人比較悶,當時我直接找到他說:賀助理員,我們領結婚證吧!
1967年7月1日,賀瑞起與李玉珍登記結婚,這件事還成了當時被口口相傳的“熱點新聞”呢。有趣的是,“處朋友”時他們都不知道對方年紀多大、生日是哪一天,後來到結婚登記處鬧出大笑話。他們竟是 同年同月同日生!這讓結婚登記處的所有人都記住了他們。
李玉珍
當時登記員首先問了他的出生信息。當我聽到他口中報出1942年12月27日時,我驚訝得捂住了嘴,心裏感嘆道也真是太巧了吧。我們倆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兩位老人也說,當時由於新疆物質匱乏,婚禮操辦十分簡陋,也沒啥親朋好友可以邀請。但他們兩人婚禮當天,卻有無數人前來圍觀,就是爲了看一眼這對同一天生的小夫妻。
直到現在,這對老夫妻都深信,他們之間緣分深厚。賀瑞起還清楚記得,他自己是在1961年那年從河北來到上海報名援疆招生,9月12日和上海援疆學生一起坐火車到了阿克蘇。愛人是兩年後的1963年從上海來到新疆,一個北方人、一個南方人,不遠千里都到一起找到了對方,“這就是千里姻緣嘛!”
歷經辛酸,攜手同行苦也甜
就算戀愛、結婚的記憶是甜蜜的,但支援新疆的那段記憶依然很“苦”。他們剛去兵團時還沒啥房子,只能住在‘地窩子’裏過渡。
李玉珍
當時條件太艱難了,小娃娃沒有糖喫,女的沒有衛生紙,男的沒有煙抽,放眼望去就是一片荒蕪,遇到發洪水時,就是一片汪洋。
“地窩子”是什麼?老人說,那是在沙漠化地區簡陋的居住方式——在地面以下挖約一米深的坑,形狀四方,面積約兩三米,四周用土坯或磚瓦壘起約半米的矮牆,頂上放幾根椽子,再搭上樹枝編成的筏子,再用草葉、泥巴蓋頂。“地窩子”可以抵禦沙漠化地區常見的風沙,並且冬暖夏涼,但通風較差。
李玉珍
後來我們被下放到18連,這個連隊全團最差,人員最爲複雜。但沒辦法,上頭給命令,只能硬着頭皮上。
由於開荒,勞動力大,又沒有葷腥,連隊菜園也種不了啥菜,肚子一直喫不飽。1968年12月,大兒子的出生使得家庭的負擔更加承重。
李玉珍
當時餓了,就找當地的沙棗喫,將沙棗從樹上打下來,曬一下,去皮去殼,與玉米粉、苞穀粉揉在一起,做麪食。雖然有一絲絲甜味,但喫口又沙又粗,難以下嚥,但在當時靠這個頂了好多年。
讓李玉珍最開心的事,是每次回上海探親。雖然要經歷軍車幾天的路上顛簸和火車的人擠人,如同“難民逃難”一樣灰頭土臉,但能看到家人,並多帶一些生活用品、喫食回去,再苦再累都覺得值。
李玉珍
大到衣物,小到鹽巴、火柴,都要一併帶回新疆,每次都要六七個大紙箱。到兵團門口,就有一大堆人翹首企盼,就爲了能得到一顆大白兔、話梅之類的解解饞,太苦了。
1971年6月,李玉珍與丈夫賀瑞起調回機關。李玉珍在團部中心小學當老師,愛人重回組織部工作,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如今,兩個兒子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二老也在2002年回到了上海,頤養天年。過去經歷的辛酸苦辣,如今卻成爲了二老攜手度過的滿滿回憶。
又是一年重陽節
祝願天下老人幸福安康!
來源:@上觀新聞
編輯:吳國華、王雨思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