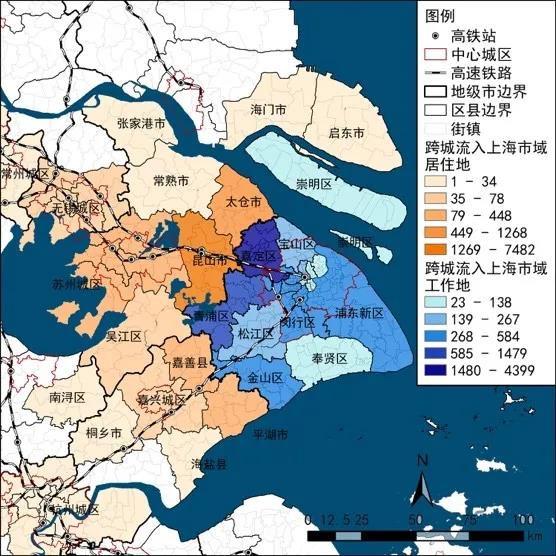戰爭與革命中的大學:東北大學的創辦流亡與復員
原標題:戰爭與革命中的流亡大學:東北大學的創辦、流亡與復員
在民國大學裏,東北大學是特殊的存在,在短短九年時間內,流亡多地,堪稱世界第一的流亡大學。近期出版的《地域與使命: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詳細研究了東北大學從創辦、流亡與復原的歷史過程,也展現了地方勢力、黨派鬥爭的嬗變態勢。
作者丨王春林
在中國近代史上,軍閥創辦的學校爲數不少,但大多無疾而終,因爲軍閥當政時間大多不長。而如東北大學這種獲得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長期支持而迅猛發展的大學更爲異數。奉系的支持與薰染使該校的衙門色彩與地域觀念十分濃厚,這成爲該校發展初期的另一個基調。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大學隨張學良的東北地方勢力流亡北平,這期間飽受流亡之苦,“流亡”的境遇與身份使東北大學對救亡和黨派活動極爲熱心,並因政治主張的差異而發生分流。抗戰時期,內遷四川的東北大學的“收復東北”訴求與地域觀念仍十分厚重,並與彼時的國共校園鬥爭糾纏在一起。
戰後的國共內戰時期,東北大學動盪不安,並深深捲入學生運動中,最終在中共解放北平後被接收。校長或代理人、地域觀念、學風演變與黨派力量共同影響着東北大學的發展,東大的發展軌跡是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地域與使命: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王春林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校長或代理人
從1923年創立到1949年爲中共接管,東北大學經歷了奉系軍閥時期、東北易幟時期、中日戰爭時期和國共內戰時期,其間東北學人對建設東北、抗日戰爭等時代主題都做了積極的回應。東大的第一屆畢業生並且曾任教員的蒼寶忠在建校四十週年時一方面感嘆“校運坎坷”,一方面又直言這是“人謀不臧”所致。
在1923~1949年的27年內,東北大學經歷了王永江、劉尚清、張學良、臧啓芳和劉樹勳5任校長、6位校長代理人
(見下表)
。而多數代理人都出現在奉系軍閥及張學良時期。其中僅在張學良長校的1928~1937年,他就先後任命了劉鳳竹、寧恩承、王卓然、周鯨文等4人代理校務,平均每人任期爲兩年半。
這對一所大學的長期發展是很不利的。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傑在日記中曾指出:“教育因工作必經長期,始能爲相當效益,而吾國任中央或地方教育之□者,往往□□即去,彼爲教育效能不易提高之一因。”
資料來源:王振乾、丘琴、姜剋夫編著《東北大學史稿》;臧啓芳《回憶》;《王卓然史料集》。
在王永江和劉尚清時期,兩人分別通過代理人吳家象、馮廣民掌握校務。這使得奉系軍閥時期的東北大學被打上了濃厚的“軍閥教育”烙印。奉系官場氛圍的薰陶使學校趨於衙門化,奉系內奉天與吉林間的省籍矛盾亦充分展現。張學良長校時期與其前任有些差異,但其大學理念仍然較爲狹隘。張學良的長校,將“軍閥教育”的特點發揮到極致。一方面,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大學發展迅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東北大學的教職員流動甚大。這彰顯了新興大學的吸引力及其發展瓶頸。其原因較多,但最主要的應是“軍閥教育”的屬性。
九一八事變後,流亡北平的東北大學在辦學環境、經費和師資等方面都大爲惡化。但張學良及其代理人的主持校務,仍得到教育部的默認。寧恩承、王卓然、周鯨文三人皆爲東北籍人士,並奉張學良之命管理該校,實際上是張的幕僚。
東北大學雖爲國家之大學,並且早經教育部備案規劃,但該校在相當程度上仍爲東北地方勢力所有。彼時該校雖在經費上呈現國立化傾向,但大部分師生仍奉張學良爲領袖。因而這時的東北大學在“流亡教育”的表象之下,實質上仍延續了奉系時期“軍閥教育”的一些特點。但流亡的境遇使此種“軍閥教育”的基礎遭到嚴重削弱,學生的思想亦呈現多樣化。而西安事變後的國立改組則是教育部主導的旨在消除該校“軍閥教育”色彩的一場角力。
據1934年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在國立暨部立獨立學院、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校長、院長中,除暨南大學和其他四所財政部等部門設立學校的校長無教育背景記錄,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畢業於專門學校外,全部具有留學背景。
在21名校長或院長中,有博士學位者9人,有碩士學位者3人,在著名大學有研究經歷者2人,其餘則具有大學或專科學校學歷。而在12所省立獨立學院、大學和專科學校校長、院長中,有留學經歷者10人,有大學以上學歷者10人(此外尚有1人爲法國留學生),僅張學良1人畢業於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從校長的教育背景看,張學良明顯落後於省立大學的校長,更遑論國立大學了。
張學良主政東北時期,東大的發展宗旨是“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應社會之需要,謀文化之發展”。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視東北大學爲“東北流亡勢力”復土還鄉的人才培養機構,是東北軍之外最重要的團體。張學良的大學理念,明顯是將東北大學辦成一所爲東北地方勢力服務的“地方”大學。
西安事變後,東北大學進入臧啓芳主持校務時期。臧啓芳雖與東北地方勢力淵源甚深,卻更傾向於國民政府。他對東北大學在抗戰時期的恢復、發展,乃至抗戰後的復員都貢獻巨大。而從臧啓芳個人的教育背景看,他也較張學良等人更適合東北大學校長的職務。改組國立後,臧啓芳僅對教育部負責,對校務也有完全的施政權,其大學理念亦能更好地付諸實踐。
國立東北大學校長任命狀
因而,在臧啓芳時期,東北大學在教學環境、教員層次和學術成果等方面,都得到穩步提升。東北大學校風較之北平時期大爲好轉,其學術地位也達到了流亡時期的最高水平,學生人數至抗戰勝利前也已近千人。但在地域觀念濃厚的東北流亡人士中,很多人並不認同臧啓芳的付出。在一般學生眼中,“校長臧啓芳是一位留學美國的老學人,但不是張學良的人,與教育部關係密切”。反而是高而公做出了帶有較濃色彩的認定:“臧啓芳有意拉攏東北籍學生作爲自己的後盾,所以對學生……採取‘寬容’的政策。”
臧啓芳之後的繼任校長劉樹勳,其長校適逢國共內戰最激烈的時期,東北大學深受影響。在這種情勢下,劉樹勳僅能勉力維持學校的運行,其他都無從談起。
地域觀念的消長
蔣永敬曾指出:“中國自晚清以降,‘地方主義’隨着地方勢力的興起而抬頭。表面看來,似乎造成國家統一的障礙,實際則爲歷史的趨勢,非人爲所能抗拒。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地方主義’對於民族的復興,政治的民主,國家的統一,也有其正面效應。”蔣進而指出:“所謂愛鄉愛國,推己及人,此乃中國傳統的精神。”
蔣之論述一反此前各界對地方主義的批評,而指出其合理性與正面作用。事實上,中國各地的地方主義思想確實根深蒂固,在近代民族國家思想大張之際,地方主義儘管有所退卻,但仍然保持着頑強的生命力。民國時期,地方與中央或國家的矛盾糾葛從未停息,但地方主義在時代變局下似亦經歷着嬗變,地方主義對內憂外患的應對雖不及民族主義的號召力與影響力,但亦有相當作用。以東大學生爲例,他們自發地對國難做出回應,儘管效用有限,但大多與民族主義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東北是民國時期地域觀念較爲濃厚的地區,東北大學由奉系地方勢力創辦,雖幾經流轉,仍充滿濃重的地域觀念。《東北大學史稿》曾指出:“東大和東北是同命運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使東北地方勢力與東北民衆遭受沉重打擊,在其後形成的“東北流亡勢力”中,東北大學成爲被寄予厚望的團體。
金毓黻曾撰文論述東北精神:“蓋東北人所負之使命即爲東北大學所負之使命,凡東北大學之師長、同學,無論其爲東北人與否,皆應負完成東北大學使命之責。東北土地雖已淪陷,而東北精神依然存在,未來之東北人物應由東北大學造成,凡研東北問題之學者亦應出身於東北大學。所謂抗戰建國,所謂復土還鄉,皆爲完成東北大學使命之條件,能由此點努力,始終不懈,而後可由東北局部之精神以造成中國整個之精神,此即愚所附論之東北大學精神。”可見,東北大學凝聚着“東北流亡勢力”與東北民衆復土還鄉的使命與期望,因而得到鄉人與國民政府方面的關注,並培育了大量人才。
由瀋陽輾轉遷到四川三臺的國立東北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在校門前合影
流亡關內後,東北大學雖仍充斥着地域觀念,但復土還鄉的志願與抗日復土的國人訴求在相當程度上是契合的。因此,1931~1945年,以東北大學爲陣地,地方勢力既肩負收復失地的使命,又頑強地與國民政府的力量相博弈。1931~1937年以鬥爭爲主;1937~1945年則以合作爲主。1946~1949年,東北大學復員瀋陽,但地域觀念似乎重新膨脹。民國時期東北大學地域觀念的嬗變表明,地方勢力雖然日漸衰落,但地域觀念是深入骨髓的。雖然在表象上東北大學逐漸被納入教育部的管轄,國家權力在地方勢力原有團體中得到強化,但亦不得不與地方勢力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國家權力的延伸必然需要地方勢力的配合,地域觀念亦因而得以保存或變異。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學在奉系地方勢力的羽翼下創建發展,奉系集團內的省籍糾葛與政治文化亦投射到該校中。是時的東北完全處於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爲首的奉系地方勢力統治下,“既支持又控制”的模式似是地方勢力創辦高等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時東北大學中所折射之地域觀念是東北地方省籍觀念增長後的自然結果。
另一方面,是時國共兩黨力量在東北顯然尚處於弱勢,對東大尚無甚大影響,而國民政府之政令更是鮮有能及於東北者。因此,當時亦是東北地域觀念最爲鮮明之時期。1931~1937年,流亡北平的東大一方面處在“東北流亡勢力”與國民政府的潛在爭奪下;另一方面,中共亦在該校師生中發展了力量,並影響該校校風與教學等。
因此,東北大學改組國立風潮實質上是地方與中央的衝突,中共力量則出於其發展考量亦參與其間,併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1938~1946年,內遷三臺的東北大學的地域觀念似有所削弱,而代之以一種地方關懷。這期間,中央與地方關係較爲緩和,而中共與國民黨各派系的學生組織的鬥爭卻日益激烈,並與省籍矛盾糾纏在一起。國共內戰期間,地域觀念在東北學生七五事件中雖然表現得較爲激進,但在內戰形勢惡劣與東北勢力衰弱的情勢下只能做些道義上的聲討,最終無奈地接受中央政府的措置。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學的學生中絕大多數是奉天
(遼寧)
籍,而在流亡關內後的東北大學學生中,除抗戰後期外,遼寧籍學生亦始終佔絕對多數。這反映了奉天以及其後的遼寧在東北地區(乃至全國)的富庶和先進,而奉系軍閥以“奉”命名並非憑空而來。這種現象在東北軍中亦普遍存在,以東北軍一〇五師爲例,“因他們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深,所以自連長以上的官佐沒有一個不是遼寧人”。
這種奉天以及遼寧的“首省”意識或優越感,既是一種始終存在的不平衡現象,又通過地方勢力與國家的支持維持着其正當性。東北籍與四川籍學生的消長以及糾葛是抗戰時期方出現的特殊問題。此時,省籍問題背後蘊含着地域觀念、黨派糾葛、抗戰前途等諸多問題。教育部最後只能在地域觀念與抗戰前途兩者間做些平衡,在復員東北後這一問題旋即迎刃而解。

東北大學辦公樓
學風的演變
九一八事變前,儘管有地方勢力的制約,東北大學還是形成了勤奮、踏實的學風。該校亦表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流亡關內的惡劣的內外環境使該校學生難以安心讀書,轉而熱心於救亡圖存的政治活動和黨派組織,進而發展爲北平學運的中心之一。這種轉變有全國各界抗日救亡運動影響的因素,有東北流亡勢力尋求復土還鄉的內在驅動,亦有平津地區學運組織與黨派活動的外在吸引作用。東北大學的學風在流亡北平後的激變,反映了東北流亡學生對“國破家亡、流亡關內”的切膚之痛,也反映了他們抗日救亡、復土還鄉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筆者感到東北大學流亡關內後發生了明顯的“關內化”傾向。東北大學與“東北流亡勢力”、關內其他大學、國民政府、地方社會及民衆聯繫之密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東北大學逐漸融入關內高等教育的氛圍中,其學風、日常生活、黨派活動等皆深受影響。前述這種現象,筆者姑且稱之爲“關內化”。東北大學的關內化,代表着整個東北地方勢力靠近國民政府的趨向,反映了國家的進一步團結鞏固。
對比入關前的東北大學與關內大學
(可以平津地區爲例)
的不同之處,我們更能體會到入關後的東北大學的“關內化”傾向。這種傾向是民族國家構建的表現形式,以“關內化”命名,更能直接和具體反映東北地方勢力向國民政府靠攏這種統一趨勢中的融合和互動態勢。其後,東北大學的學風大體與關內大學趨於一致,這或許表明,東北大學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國內大學發展的整體環境當中。
“東北流亡勢力”的救亡、宣傳及其對關內的衝擊影響甚大,這個羣體的現實存在對關內民衆的國難意識、救亡運動亦是一種推動力量。其間,“東北流亡勢力”主觀上試圖保存地方的相對獨立,客觀上卻依賴中央。東北地方勢力的地方性在外力下削弱,因而加強了國家統一化趨勢。“東北流亡勢力”的關內活動密切了其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加強了這一地方勢力對國家的認同程度,無形中成爲民國時期國家統一運動的一部分。
北平時期,東北大學緊密關注中日關係發展態勢。在中日關係緊張、學運此起彼伏的情勢下,東北大學亦只能勉力維持,學校規模略有恢復。但在華北嚴峻的政治環境下,東北大學很難獲得正常發展。內遷四川三臺初期,東北大學遠離了學運中心的北平,校內的地方意識亦有所削弱,教學環境相對安定。東北大學再次恢復勤奮務實的學風。但其後因校內國共黨組織的發展及對立,四川與東北等省籍師生間的矛盾亦逐漸凸顯,校園環境再度惡化。這一時期東北大學的校園環境與關內大學校園環境是相近的。彼時中共學生組織在大學中已具有一定優勢,這爲戰後第二條陣線發揮作用奠定了基礎。
而在東北大學復員瀋陽後,校園環境延續了抗戰後期的氛圍,加之國共內戰的影響,學生很難安心治學。這種全國時局的動盪使得整個大學教育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中共政權定鼎,對於行將崩潰的各大學亦是一件好事。這意味着可以結束戰後數年的內外動盪,讓教育迴歸它應有的軌道。
在學風演變的同時,東大也由最初被譏爲“野雞大學”發展爲東北最高學府。蒼寶忠感慨道:“展閱校史,聘請過多少有名先生,造就出多少有用同學,對國家人民暨地方社會,直接間接,均不無若干貢獻和裨益。”
黨派力量的增長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大學完全爲東北地方勢力控制,校內國共兩黨組織仍處在祕密活動階段。1929年和1931年兩次校內風潮表明,彼時臧啓芳等國民黨背景師生的勢力與影響雖然有所增強,但根本無法撼動地方以及學校當局的權威。
流亡北平時期,張學良的東北地方勢力在華北仍具有一定實力,國民政府亦有借重之處,東北大學因而得以在地方勢力的羽翼下維持。但彼時地方勢力對東北大學的掌控已經有所鬆動,國民黨、中共等黨派的滲透,使東北大學表現出一定的離心傾向。這在“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前後表現得尤爲明顯。這期間,東北大學當局已難以控制學生。在這一時期,東北大學形成依附東北地方勢力,同時也爲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共等勢力或黨派吸引的局面。
西安事變後,東北大學改組爲國立大學,東北地方勢力基本退出學校。在內遷初期,國民黨組織在東北大學居於較強勢地位,中共的力量則較爲薄弱,該校“國家”觀念有所提升。隨着中共力量在國統區的發展壯大,中共學生組織亦逐漸在東大發展起來,而該校國民黨組織則形成CC系與三青團等派系的對立。伴隨着國民政府的腐敗等問題,一般學生的“黨國”觀念似乎亦有所下降。抗戰勝利時,“我們當時都很苦悶,主要是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不滿。我已看過趙超構同志的《延安一月》,我認爲中國的希望在那裏。儘管生活上十分艱苦,但那裏的生產自救,官兵平等,上下齊心非常吸引我”。
東北大學當局對學校的控制力有所削弱。這一時期,東北經歷了從國民政府(國民黨)強勢掌控東北大學,到國共兩黨學生組織在學校內對峙的嬗變。其間,“東北流亡勢力”多扮演着長輩、鄉賢等角色,對該校的影響變得較爲溫和。
抗戰後期以及復員瀋陽後,校內生態急劇惡化。這使得學校的復員與校務運轉都困難重重,復員後的校長更易也是國共各黨派以及其他反臧勢力推動的結果。但在國共內戰的大環境下,該校國共兩黨學生組織的鬥爭已趨於白熱化,學校當局對校務的控制力更加削弱。至七五事件後,南京政府進退失據,東北地方勢力反應激烈,中共學生組織亦積極參與其間。與中共軍事上的勝利相對應,東北大學爲中共接收,東北地方勢力走向新政權。
在東北大學的發展過程中,黨派力量表現出很強的寄生能力。1923~1949年東北大學的遭遇折射了東北地方勢力的衰落態勢。這期間,中央政府表現出向地方擴張和延伸的態勢,而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態勢亦日益嚴峻,中共力量則逐步發展壯大。1931年九一八事變使東北地方勢力深受打擊而淪爲流亡勢力,在應對國難的過程中這一勢力逐漸融入國家,其自身的地域觀念則相對削弱。
另一方面,中共在與國民黨的較量中,地方勢力成爲其發展的溫牀與土壤。在這幾種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東北地方勢力日漸式微。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的侵略直接打擊了東北地方勢力,國民黨因勢利導地強化了對這一“流亡勢力”的控制,中共亦從中汲取了能量。當抗戰勝利後的國共決戰時,東北地方勢力已經被邊緣化;當中共建立新中國政權的時候,東北則成爲其穩固的解放區。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東北地方勢力無力阻止其本身的衰落,而國民黨與中共則扮演了推手的角色。
本文選自《地域與使命:民國時期東北大學的創辦與流亡》(王春林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系該書“結論”部門,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摘編丨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