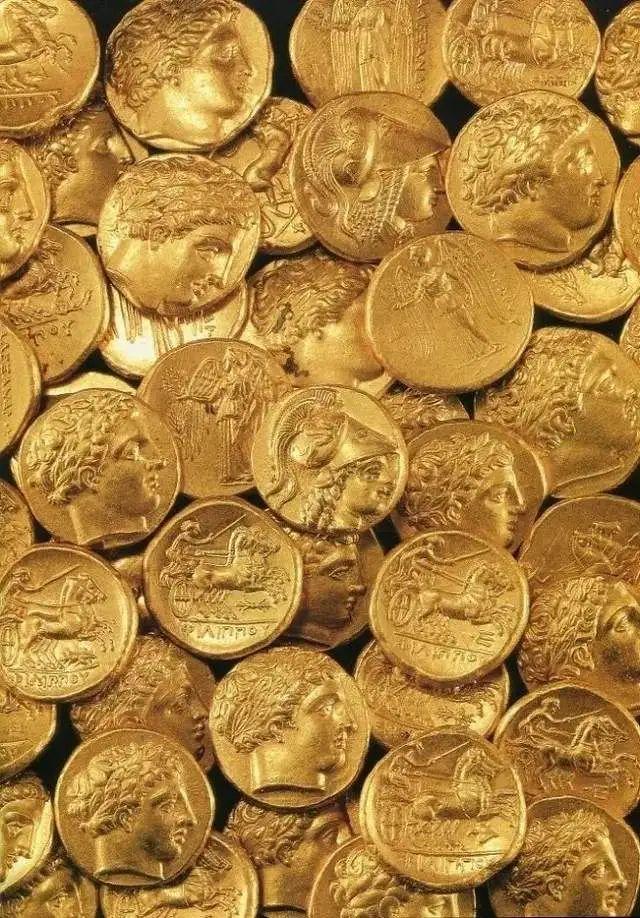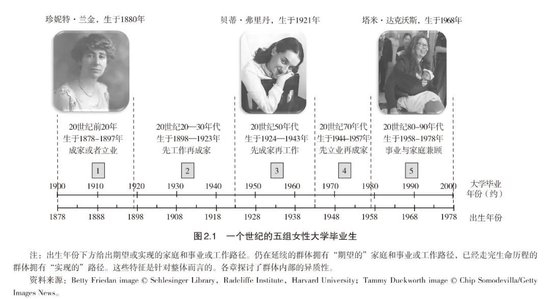如何认识“历史周期律”与“李约瑟难题”
(本文节选自《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后附全书内容提要)
有数千年灿烂的古代文明积淀的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时代来临之后,明显落伍,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痛楚之中,一百多年间无数志士仁人寻求救亡图存,富强振兴之道。上世纪,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摆脱内战局面,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三件大事”依次发生,终使我们这个近代灾难深重的古国,站在了“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愿景”的历史新起点之上。回顾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格局之后两千年的历史,并展望2049年将使现代化大功初成的“中国梦”战略目标,在本章前面的多角度简要分析考察之后,有两个沉重的话题不可回避:一是“历史周期律”;二是“李约瑟难题”。
一、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当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际,到延安考察的爱国人士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一番非常著名的谈话,史称“窑洞对”。7月4日下午,应邀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做客的黄炎培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点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后人关于“周期律”的文字表述有过多年探讨,我们认同此处“率”字实指规律性的“律”当为准确用字?)——显然,黄炎培隐含了他没有直接说出的问题:已看得出共产党有可能得天下而改朝换代,中国共产党今后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
对于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七十年前这番话,似余音仍在,而历史沧桑风云变化之中,研究者已有多少感慨:如以学理语言作最简要的概括,“窑洞对”所说的“民主的新路”,即应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共和”二字所涵盖的“民主法治”之路的简称,属人类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现代文明”的前沿性基本概念。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近七十年,在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以1954年制定第一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等为突出代表),也走过了曲折坎坷之路而发生过严重失误(以“文革十年浩劫”中以人治践踏民主法治为突出代表),终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政方针,正指引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轨之路上,去追求以基础性制度建设保障的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
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自秦始皇“大一统”之后的公共事务领域(政治与社会领域)的解决机制,属于“非规范的公共选择”(“非规范的”,即价值取向上为“不应该的”和社会代价沉重的),在大大小小“其兴也勃(通浡),其亡也忽”的几十次改朝换代的循环中,矛盾冲突总是不能很好从内部消化解决,总是要使矛盾积累到采取暴烈的外部冲突的方式来个了结,表现为二百多次农民起义,以及频繁发生于政治权力配置“宫廷解决”和“广场解决”、“战场解决”中的血腥残暴,哀鸿遍野,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经历多少牺牲奋斗、多少血泪歌哭之中,国人终于站到了展望2049“中国梦”现代化愿景的门槛之上,但在“黄金发展”的同时又受到“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风险制约与威胁,我们当然要紧紧抓住实现这一“从未如此接近”愿景的唯一出路,即“规范的公共选择”(“规范的”,也就是指“应该的”、社会代价较小的)之路,以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的改革攻坚克难,来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把权力和人性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以民主法治的规则体系,全面覆盖社会生活,使公共事务决策走现代化文明方式的“法治民主的会场解决”之途,这样才能有把握地防范依“个人功业欲”而走偏的人治化灾难,以及民粹主义“求荣取辱”的极端化弊病,改变“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周期律式不良循环重演而长治久安,造福人民。
这正是重温延安“窑洞对”的巨大现实意义所在,亦是以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而作为考虑2049现代化战略目标如何实现的坚实依据的历史经验来源。
二、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
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首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科学知识以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明显优胜于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一著名的问题也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经久不衰地引发了多轮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
从不胜枚举的具体案例来看,“李约瑟难题”所指的事实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在谷登堡将印刷术引进德国前600年,中国人业已掌握这项技术;中国建造出第一个利用链条传送动力的装备,领先欧洲人700年;中国人首先使用了指南针,至少一个世纪后世界其它地方才出现相关信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中还包括火药,但在中国人主要用它来制造烟花爆竹以营造节日气氛和驱赶臆想中的鬼怪魑魅多少年后,却在鸦片战争中,遭遇了“坚船利炮”的英国人发射过来的从未遇到的猛烈炮火而归于惨败……那么,15世纪中期之后,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突然止步不前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李约瑟等中外研究者有提供了一些解释:一是中国迟迟没有具备适宜近现代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太讲究实用和保密,很多发现、发明滞留在经验阶段和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选拔的是文科人才,特别是明以后的约500年间主要就是以“八股文”选精英,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中国传统中对于经商阶层的蔑视与抑制、大一统帝国的专制,使经济活动中无法充分激发竞争和自我改进意识,等等。这些见仁见智的原因分析,固然无法定于一尊,还远不能穷尽对此难题的破解努力,但无疑对于中国追求现代化而讨论如何展望2049而成功走通“创新型国家”之路,极具启发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强调指出了科学技术在人类进步历史中所表现为“革命性力量”的重大意义;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主要决策人(“总设计师”)也早在“十年动乱”中他复出时,就把科技摆在了“第一生产力”的高位。邓小平的这一认识具有严谨的学理依据:学者的分析指明,科技对于传统的社会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认识框架,不是做加法即加上个第四要素,而是做乘法,是形成乘数、放大效应,即革命性的,可引出“颠覆性创新”式效应、迅速改变局面,引领发展潮流的功能,所以它是“第一”。经济学研究揭示的“全要素”生产中所称的“索洛余值”,主要指的首先就是在经济增长中较易量化计算的劳动力、资本等的贡献之上多出来的那部分不易量化的贡献,肯定与科技有关。而充分调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正是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三十余年后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对冲下行压力因素而打造经济增长质量在“中高速”特征下的“升级版”的关键。
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主流经济成果所做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反思与深化研究,已引出了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并紧密地内在契合于中央决策层关于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我们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强调了科技创新的进展和成功,需要得到供给侧另一重要因素即制度供给的支持与呼应,在中国于工业革命后落伍,而必须完成的经济社会转轨和发展的追赶—赶超中,首先必须抓住制度建设即改革这个龙头,以制度创新充分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以解放生产力,贯彻落实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去实现“中国梦”。相关制度条件、制度环境的打造,必须针对违背科研创新、科技发展规律和科研领导人才培养教育规律的官本位、行政化、论资排辈、思想钳制等弊病而除旧布新,实质性深化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和配套改革,积极借鉴吸收硅谷等国际科技创新的有益经验,营造中国迎接2049的良好科研生态,对于产学研一线创新者给予符合科研规律的物质利益激励与人文关怀,并在基础科研、成果孵化、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施与市场机制接轨、兼容的理性的供给管理。
温故而知新,鉴古以开来。在面对2049愿景推进现代化的研究中,“李约瑟难题”的破解与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追求一样,首先必须抓住有效制度供给这个龙头,这是应明确强调的深入进行本项课题研究的逻辑主线。
内容提要
本书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组成的研究群体,秉承经世济民的中国经济学人“天下家国”情怀,践行“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理念,弘扬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莫干山精神”,以“长焦距+广视野+量化分析”为研究方法,历经四年集体创作的“中国2049战略”研究课题的核心成果。根据邓小平同志70年眼界“三步走”的伟大战略构想,以及新供给经济学在创立初期就确立并向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委建议的“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以及前所未有的长期概念之下超越30年时间段而对接到实现“中国梦”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贯穿全书的主线是“改革开放”——以新制度供给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包括10章,约53万字。以新供给经济学核心理念和认识框架为研究基石和立论依据,归纳中国的国情特征,回顾与反思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比较了近500年来全球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主要经济体发展道路,量化对比分析了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金砖国家”等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中国未来35年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发展目标、增长空间、动力机制,并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就2020年前、2021至2035年、2036至2049年三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重点及改革开放、创新驱动提出了具体举措方面的意见建议。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