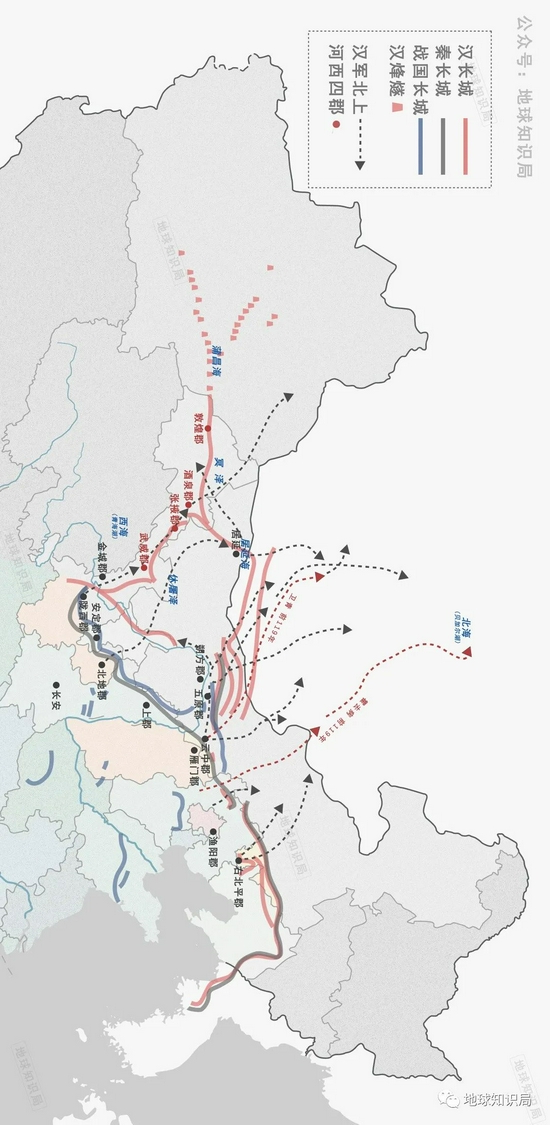西漢琉璃葬具與海昏侯的琉璃席
海昏侯墓是近年中國考古界的重大發現,因墓主身份特殊、園陵完整且未被盜,從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故對於漢代歷史、典章制度、文物研究等都極有意義。衆多文物中,一牀出土於內棺、由金箔包裹絲線編綴成的琉璃席頗引人注目。一般認爲漢代琉璃極爲珍貴,因此有報導指出,雖然海昏侯的人生以遷居偏遠之地的侯位告終,但畢竟曾貴爲皇帝,或因此使用珍貴的琉璃葬具以彰顯其人生歷程。事實上,海昏侯這牀琉璃席並非考古發現中的孤例,在其嗣子劉充國墓、江蘇尹灣漢墓、揚州西湖蠶桑廠與2017年才發掘的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中也各出了一牀,且漢代的考古發現中,更有不少琉璃質葬具出土,可見海昏侯的琉璃席在當時並非珍貴的葬具。相反的,在梳理其他琉璃葬具之後,我們發現這牀琉璃席甚至比列侯身份可用的葬具更爲低等。
本文將從三個方向來探討西漢琉璃葬具與海昏侯的琉璃席。首先將先論述西漢時期的琉璃製作工藝發展發展情形,窺知琉璃在西漢時期的價值之後,再梳理西漢時期出土的琉璃葬具,探討琉璃在西漢“玉斂葬”制度裏的地位,確認琉璃質葬具的社會與禮制意義。最後,再回到這件琉璃席的主人—海昏侯的一生,借文獻來探討海昏侯何以經歷嗣諸侯王、廢帝、侯等奇絕的一生,最終只能以琉璃席裹身的原因。
一、西漢時期的琉璃製作工藝發展情形
琉璃又稱玻璃,文獻中最早見於西漢桓寬《鹽鐵論》,文中將琉璃與璧玉、珊瑚並稱爲國寶。又因《後漢書》中的《南蠻西南夷列傳》《西域傳》中曾經提及,因而常被認爲屬於外國輸入的珍寶之一。事實上,中國自產的琉璃屬於鉛鋇玻璃系統,與西方的鈉鈣玻璃不同。鉛鋇玻璃易碎,加上中國並未發展出“退熱”的程序,所以不宜做爲食器;而這正是從西方傳來的鈉鈣玻璃被珍視的原因。早在西周時期陝西寶雞
國墓地出土的大量琉璃管珠中,就因成分、外貌特徵與國外不同而能確定是中國自制產品。最遲至戰國時期,中國就已發展出很好的鑄造(或壓制,以人工技術製成固定形狀)玻璃技術,例如1965年出土於湖北江陵望山楚墓中的“越王勾踐劍”,在劍格兩面凹槽部份中分別鑲嵌着多塊綠松石和玻璃。出土時,綠松石完好無缺,玻璃僅餘兩塊。這兩塊玻璃都是淺藍色、半透明狀,內部有較大的橢圓形氣孔;中國古代玻璃專家後德俊先生認爲,這兩塊玻璃屬於中國自產自制。
戰國晚期所出土的琉璃以湖南省最多。據湖南省博物館前館長傅舉有先生於2010年的統計,戰國至秦漢時期湖南所出土的琉璃璧共有201件,佔全國233件的87%;其中出土於長沙楚墓的就有97件,幾乎佔全國出土的半數,顯示出當時湖南的琉璃製作工藝已非常發達。“璧”爲圓圜形平板器物,《說文·玉部》提到:“璧,瑞玉,圜也”,主要用於各種禮儀場所,目前出土的實物中,可見玉質、石質、琉璃質等。一般琉璃璧的製作是將石英砂、方鉛礦、重晶石、硝石等原料混合加熱至攝氏1050度,使其熔化之後再倒入已制好的泥模或陶模中,最後趁液態玻璃尚未凝固前壓制成形。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璧形制與當時的玉璧十分相似,依照傅舉有先生的分類,有谷紋、芽谷紋、齒紋谷紋複合紋、蒲紋、方格紋等五類,其中出土最早、延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多的是以小乳丁紋爲主的谷紋璧。這些玉璧色彩豐富,其中碧綠色、乳白色者與玉器的色澤十分相似,但大多數的琉璃璧都只有一面有紋飾,另一面則素面無紋,且邊緣粗糙尖利,似專爲喪葬所用。
湖南出土琉璃璧的墓葬均爲士級與庶民階級,不見於高級貴族墓葬中,且墓主男女兼有,使用十分普遍,這顯示當時玻璃璧的價值並不高。這些琉璃璧大多置於死者頭部和足部,部分出土時仍呈現側立情形,可見原來可能鑲嵌於棺檔上。有鑑於滿城漢墓、南越王墓中的玉璧曾出於整件玉衣頭頂部分,許多漢代鑲玉棺、漆棺的兩檔也鑲或繪有玉璧,可見這些琉璃璧的作用與玉璧相當,一樣具有保護屍身、引魂昇天的作用。至於湖南出土的琉璃璧數量特別多的原因,傅舉有先生認爲可能有:1.湖南不產玉,但在禮制上卻有使用的需要,因此以琉璃代替;2.湖南有豐富的玻璃原料。此外我們也察覺到其中的等級差異:高級貴族用玉,而士、庶民則以類玉的琉璃代之。
西漢以後,廣西出土的琉璃器數量增加,似乎形成了另一個玻璃產地。廣西的玻璃成分與我國傳統的鉛鋇玻璃、西方的鈉鈣玻璃均不同,以K20-SiO2(氧化鉀—二氧化硅)爲主,器型則有珠、耳璫、璧、碗、杯、料飾等。另一方面,平板玻璃的發展也持續進步,透光度、透明度均更上一層樓。1983年發現的南越王墓中出土數十枚藍色的平板玻璃,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史美光先生認爲,這種玻璃在當時是可以作爲玻璃窗的採光玻璃來使用的。這正符合了文獻中“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雲母屏風、琉璃屏風”等的記載。
從上可知,戰國時期開始出現的平板琉璃,到了漢代已十分常見。戰國時期的湖南地區是琉璃的主要產地,此時的琉璃不論是在色澤與使用上均仍處於“仿玉”的階段,在楚地大多爲下級貴族與平民百姓於喪葬中使用。到了西漢以後,由於製作工藝已能依照需求控制成品的透光度,鑄模、拋光技術上也已達到極高的標準,因此琉璃也能成爲窗扉、屏風的材料了。這也說明了西漢中、晚期以後出現的片狀平板琉璃葬具,在製作上並無高貴、難得的理由。
二、西漢時期出土的琉璃葬具
西漢墓葬中的琉璃璧數量降低,且大多出在身份較高的墓葬內,但是其他的琉璃製品則不少,尤以片狀琉璃、琉璃質的琀蟬、琉璃質玉握等較多,此外還有耳璫、帶鉤、珠飾等。其中與本文相關的則應屬片狀琉璃製品。
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以小型的片狀琉璃組合作爲貼身葬具,大約始於西漢中、晚期。西漢至新莽時期,片狀琉璃製成的葬具可分爲三大類,分別是琉璃玉衣與面罩(或玉衣套)、琉璃溫明以及海昏侯墓所出土的琉璃席。由於這三種葬具都貼近屍身,從外形、製作方式與使用方式等跡象來看,可能與“玉衣”相似,其形成與使用也或許與玉衣制度相關。以下先分類論述。
1.琉璃玉衣與面罩
目前確定出土琉璃玉衣與面罩(或琉璃玉衣套)的墓葬有西漢中晚期的山東五蓮張家仲崮漢墓、河北邢臺南郊西漢墓、揚州妾莫書墓、新莽時期的揚州寶女墩新莽墓M104,新莽時期的西安財政幹部培訓中心漢墓M33等。此外,大英博物館、香港的關善明博士、加拿大多倫多的波爾·辛格博士、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等也藏有疑似琉璃玉衣或面罩的片狀玻璃。
這些琉璃片的形狀多樣,矩形最多,其次有三角形、梯形、圓形等,與目前出土的玉面罩、玉衣類似。矩形琉璃片又可分大小兩種,尺寸多在5釐米×4.5釐米之間,厚度則在0.3釐米至0.5釐米之間。以科學發掘的五座墓葬來看,這些墓葬出土的琉璃片從19片至600片不等,似可分爲數量較多的琉璃玉衣與數量較少的琉璃玉面罩(或琉璃玉衣套)兩類。可能屬於玉衣者,目前僅有出土600多片琉璃片的揚州妾莫書墓。此墓屬西漢晚期大型木槨墓,出土龜紐銀印,墓主身份可能爲大貴人、長公主一級,是山陽王陵的陪葬墓之一。可能屬於琉璃面罩或玉衣套者,有山東五蓮張家仲崮M4、揚州寶女墩M104、河北邢臺南郊西漢墓、西安財政幹部培訓中心漢墓M33等。這些墓葬出土的琉璃片數量從19片到200多片不等,應無法構成玉衣。
圖1 西漢墓葬琉璃片與紋飾:a.山東五蓮張家仲崮M4 b.河北邢臺南郊西漢墓(劉遷墓)c.揚州寶女墩漢墓M104 d.大英博物館藏。前三者引自發掘報告。d.引自Han Dynasty Chinese Glass Plaques in British Museum,筆者製圖
表1 西漢出土的琉璃玉衣與面罩
2.琉璃溫明
“溫明”在文獻中僅見於《漢書·霍光傳》:“(霍光葬)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服虔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並蓋之。”20世紀80年代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專家孫機先生率先辨識出考古出土的溫明。2017年發現的青島土山屯漢墓中不僅出土一具琉璃溫明,還在遣冊上列有“玉溫明”一項,其外形確如服虔所注。
圖2 西安財幹中心M33出土的琉璃片與紋飾,引自張全民:《西安M33漢代玻璃研究》
目前已發現的琉璃溫明共有四具,分別出土於: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M6、連雲港浦南九鳳墩漢墓、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M147、山西陽高古城堡漢墓等。其中,尹灣漢墓M6出土者正面中央內嵌琉璃玉璧一枚,周圍配有四枚小玉璧形和四枚水滴形琉璃,最外圍則由八枚半圓形琉璃片圍成方形;漆板四坡內部可見方格,應是用來鑲嵌矩形琉璃片。青島土山屯漢墓M147的溫明罩於墓主頭部,盒狀盝頂,南側沒有壁板,截面爲正方形,邊長40釐米。漆板內部中央嵌琉璃璧,璧中央放置一包金箔木雕小龜,盝頂斜坡四角附有四隻木雕包金箔螭虎,盒身內外側均鑲有琉璃片,北、東、西三面側版內均鑲嵌一面素面銅鏡。鑲嵌琉璃片和銅鏡的槽內有墨書編號,琉璃片和銅鏡上也有相應的編號,可應對嵌入。盒外側有木質包金箔彩繪的伏羲女媧木偶,盒下底版置有一木雕虎頭枕。
這些出土溫明的墓葬中,九鳳墩漢墓與山西陽高古城堡漢墓無發掘報告,其他二例墓主都曾任地方官員:尹灣漢墓M6墓主師饒,曾任東海郡卒吏、五官掾、功曹史等,青島土山屯漢墓劉賜則曾任堂邑令,報導稱可能是低階貴族。海昏侯墓內也出一具溫明,內鑲有玉璧(確認爲玉質),已被壓毀;嗣子劉充國墓“頭部被漆器疊壓”,可能也有一具,但材質不明。這兩具溫明的材質與本文關注的琉璃不同,在此暫不討論。
表2 西漢出土的琉璃溫明
3.琉璃席
目前考古發現的琉璃席有五牀:江西海昏侯劉賀墓、海昏侯嗣子劉充國墓、山東青島土山屯M147、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M9北棺、江蘇揚州西湖蠶桑廠西漢董漢夫婦墓南棺等。其中,山東青島土山屯M147出土的琉璃席,在遣冊中寫作“玉席”。
圖3 尹灣漢墓M6出土的琉璃溫明木胎與琉璃片,筆者製圖
圖4 青島土山屯墓羣M147出土的琉璃溫明,引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33485028
以上文物中,目前僅出土於尹灣漢墓M9與山東青島土山屯M147者有比較清晰的圖像。這兩牀琉璃席均平鋪於棺底。尹灣漢墓M9這牀長180、寬60釐米,頭端及兩側以圓形—菱形—圓形的順序排列,中央則由小矩形以長33片、寬10片的方式排列。部分矩形片有模鑄的陰文紋飾,可以看出有大片者爲翼龍,小片則不詳,都根據圖形貼上金箔;其餘的圓形片無紋,菱形片則爲X紋。這些琉璃片均有穿孔,孔中皆有細小中空的金管,可見能以線材穿過加以編綴。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的琉璃席中央長31片、寬8片,每片琉璃厚約0.3釐米至0.5釐米。頭尾兩端爲玉璧形、菱形琉璃,兩邊則以矩形、玉璧形、菱形琉璃片綴成。外圍及中央部分琉璃有貼金箔的紋飾,計有柿蒂紋、龍紋與虎紋。琉璃片四周皆有小孔以供編綴。以上資料顯示,這兩牀琉璃席十分相似,組成的琉璃片形狀種類也很一致,只是編綴方式略有不同。兩座墓葬的時代相近,雖然距離較遠,但仍出現外型十分相似、圖像風格也相近的文物,顯示此物並不獨特,也已有一定的規制。
缺乏圖像的有海昏侯劉賀墓、嗣子劉充國墓以及江蘇揚州西湖蠶桑廠西漢董漢夫婦墓等。海昏侯墓的琉璃席尚在修復中,紀錄片報導此琉璃席長約180、寬約0.45釐米,共有384片,每片四角都有鑽孔,以包有金片的絲縷串成席面,周圍以附有云母片與金箔的漆皮包邊,並由64枚席鎮固定。海昏侯劉賀的遺骸上,有七枚玉璧覆蓋着墓主面部、口部、胸部、腹部和襠部,琉璃席下方還有60枚金餅鋪墊。嗣子劉充國墓的琉璃席報導較少,僅知以絲縷編綴、貼金片的雲母包邊。這兩牀琉璃席的琉璃片上是否有紋飾?目前仍未有更進一步的資料。江蘇揚州西湖蠶桑廠西漢董漢夫婦墓南棺(女棺)內,有大小十塊琉璃璧鑲嵌於楠木板上,琉璃片部分有紋飾,並鑲有金箔。周圍還放置了16個琉璃人(席鎮)。此墓爲夫婦合葬,北棺爲男性,出土“董漢”印章;南棺爲女性,規格較高,據考古人員推測,女墓主身份較男墓主高,可能爲諸侯王女。
以上幾座墓葬的墓主,除了尹灣漢墓墓主身份不詳之外,其餘的是海昏侯劉賀、侯嗣子劉充國、低階貴族縣令與疑似諸侯王女。
圖5 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琉璃席,引自楊軍、徐長青等:《南昌市海昏候墓》,《考古》2017年第7期,第25頁
4.西漢琉璃葬具特點
根據以上資料,琉璃質玉衣、面罩、溫明、席等葬具最早出現在西漢中期偏晚的山東,較多出現在西漢晚期,新莽以後則不再出現。出土區域十分廣泛,現今江蘇揚州一帶最多,但河北、山東、陝西、山西、江西等地都有發現,可見並非一地之俗。從這些琉璃片的造型與紋飾來看,外型以圓形、矩形、菱形等最多;紋飾除素面者之外,其餘都是模鑄的陰文龍、虎、柿蒂紋、回字紋,陰文凹槽中填上金箔、編綴用的鑽孔中留有金絲痕跡。《西京雜記》卷一《送葬用珠襦玉匣》篇:“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縷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我們也知道,古代文獻與當時實情、現今考古發現之間多少有落差。至今出土許多兩漢玉衣,卻未發現任何鏤刻有龍鳳紋飾的玉衣片,反而可見於琉璃葬具上,我們或可推測,《西京雜記》中所謂的“玉匣”很可能就是指這些模鑄之後再貼金箔的琉璃片,而“武帝匣”的原型則可能是當時某位身着琉璃葬具下葬的貴族身影。
表3 西漢出土的琉璃席
圖6 江蘇尹灣漢墓M9北棺出土的琉璃席線繪圖,引自朱磊、王冕:《漢代貼金琉璃棺席修復報告》
西漢自中期(前128—前87)之後,玉斂葬的材質、形式等級受到嚴格控制,晚期以後則較爲混亂,制度受到挑戰。等級方面,使用玉衣墓主的等級最高,其次是玉面罩、玉衣套一類,且諸侯王與西漢後期的墓葬中是不使用玉衣套的。將此結論與琉璃葬具相比較,可以看到,出土琉璃玉衣與玉面罩(或玉衣套)的五座墓中,出土600多片琉璃、疑是琉璃質玉衣的揚州妾莫書墓等級最高,因其中出土龜紐銀印,可能具有大貴人、長公主的身份。另外兩座墓主身份明確的墓葬中,山東五蓮張家仲崮M4所出的琉璃片數量僅150片,墓主劉祖曾封侯;河北邢臺南郊南曲煬侯劉遷墓所出的琉璃片數量約200片,從劉遷諡號‘煬’字中可窺知其生前德性有虧,有可能遭降級使用。可見若將琉璃質葬具納入玉斂葬系統,琉璃玉衣的等級也一樣高於玉面罩。
使用琉璃溫明的墓主身份似乎不高。尹灣漢墓M6墓主師饒曾任東海郡卒吏、五官掾、功曹史等,最多僅秩百石,然而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執掌吏員賞罰任免事宜,在諸曹掾中地位最高,甚至權逾秩六百石、由中央任免的郡丞與長史。山東青島土山屯M147的墓主劉賜則略高,爲堂邑縣令,簡報中稱其爲“低階貴族”。兩者雖在地方都屬握有實權的官吏,但從整個社會結構看來,只能算地方權貴,稱不上高級貴族。雖然如此,文獻中位至三公的霍光也使用溫明(材質不明),故目前尚不能說明琉璃溫明與墓主身份間的關係。
使用琉璃席的墓主人中,身份較確定者有堂邑縣令劉賜與揚州西湖蠶桑廠董漢的夫人,以及兩代海昏侯。堂邑縣令劉賜的身份前段已論述過,而揚州西湖蠶桑廠的墓主雖與“妾莫書”同樣爲諸侯王女眷,但已降嫁董漢,葬具又顯然比“妾莫書”低,身份應不到長公主、大貴人等級。兩代海昏侯中,劉賀已是罪臣之身;嗣子劉充國早夭,且葬禮需比始封列侯(也就是劉賀)再降一級。種種跡象顯示,琉璃席的使用層級其實更低於列侯、長公主、大貴人。回頭再來看文獻,其中從未記載琉璃席,或可能因爲其使用資格不高之故。
《後漢書·禮儀志下》:皇帝大喪“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其餘高級貴族“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另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雖然西漢晚期的禮制並不如東漢時期嚴格,但劉賀曾經身爲諸侯王,且曾登大寶,雖經廢位之巨大打擊,但仍保有昌邑王舊家財產,且墓中出土大量珍寶,顯示生活也頗優渥。後又得宣帝重封爲海昏侯,並傳位給兩嗣子,直至次子劉奉親去世後才國除,爲何他與嗣子劉充國的葬具居然連“列侯”一級可用的玉衣都沒有,更與地方縣令、諸侯王降嫁之女用同一等級的琉璃席呢?或許這可從當時漢宣帝對他的態度得到一點啓示。
三、海昏侯劉賀的琉璃席
海昏侯擁有中國歷史上最奇絕的一生。劉賀生於漢武帝徵和元年(前92),五歲襲昌邑王,十八歲即帝位,然在位二十七日,旋即被廢。之後雖仍保有故王家財產,但朝廷並未立刻恢復其諸侯王身份。直到十一年之後(宣帝元康三年,前63)三月,宣帝才又下詔封授爲海昏侯,移居豫章郡。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劉賀薨,終年約34歲。短期內,子劉充國、劉奉親相繼離世,朝野議皆以爲“不宜爲立嗣”,因此海昏侯國除。一直到元帝即位,才又封劉賀子代宗爲海昏侯。
圖7 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出土的琉璃席,引自彭峪:《漢代縣令家族的身後事 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羣》,《大衆考古》2018年第2期,第57頁
劉賀廢位之後,一直受到嚴密的監控。起初,宣帝對其有所忌憚,交付山陽郡太守張敞就近監看,雖然衣食無缺,但昌邑故宮門禁森嚴,宛如監獄。後遷居豫章郡海昏縣,封海昏侯的同時,宣帝下詔其“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完全剝奪了劉賀身爲宗室參與祭祀的權利。因此,這個封授並非表示獲得赦免,只表示宣帝對他不再顧忌而已。即便如此,劉賀起居受監視的情形依舊,因而有與卒史孫萬世交通而被“削戶三千”的記載。雖然如此悲慘,從考古出土的金餅、馬蹄金、麟趾金、簡牘等文物看來,劉賀仍然不死心的準備着諸侯王陪祭中央所應獻的“酎金”,仍然不放棄一絲回到長安的機會,無奈這個夢想並未實現,這些酎金最後只能隨他長埋地下。這前後因果關係正表現出早年張敞在昌邑故宮探望劉賀後,回奏宣帝“(賀)輕狂不惠”的一面,雖早已被皇帝列爲“天之所棄”“囂頑放廢之人”,他卻以爲自己只是“留校察看”而已。廢位的嚴重打擊,再次封授所帶來的希望,之後又因失言而削去大部分食邑,劉賀的心中隨時交織着恐懼、希望與失望,如此的情況下,相信他與家屬並無膽量製作逾制的葬具。再者,從前文論述可知,琉璃席很可能是玉斂葬系統中較低等者,但屬於玉斂葬系統,就更可能受到中央的掌控。文獻記載,漢代列侯喪事中央須遣使祭悼,一來以示哀思,二來立嗣,但實則也具有監視之舉。這牀琉璃席,很有可能是中央在劉賀故去之後,令其降級使用,也有可能是家屬因懼怕逾制再受處罰的保守之舉。
海昏侯墓雖然出土各樣令人歎爲觀止的珍寶,顯示出大量地財富,但將其出土的琉璃席與西漢琉璃葬具比較之後,我們看到,這些財富並不能支持他逾越皇權與當時的喪葬禮儀。漢代琉璃並非珍品,尤其與天然珍貴、能助墓主成仙的玉料不能相比。琉璃片具有類玉的美麗光澤,貼上金箔後更是美觀大方,但終不是玉,製成葬具也只能屈居於玉器之下。在漢代盛行玉斂葬且階級制度分明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玉質與琉璃質各類葬具間的區別透露了許多細節,且與墓主生前身份、地位甚至性格等問題有所關聯。而海昏侯的這牀琉璃席,也正是他人生晚年的寫照。
本文省略參考文獻,可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
(作者單位: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
圖文來源:《中國美術研究》2018年02期
責任編輯:楊尚禹
審覈:郝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