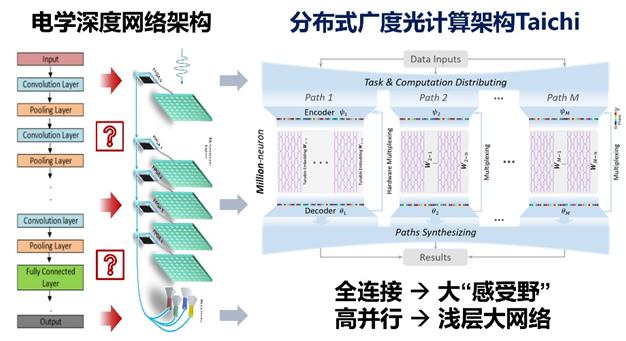“非升即走”在中国高校
资料图
从清华大学部分院系试点“非升即走”,内地高校的这项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断断续续走了二十余年,其间争议不断
法治周末记者高原
是去一所省级高校做一个有编制的讲师,还是去一所985高校做一名承受非升即走压力的副研究员,这个问题摆在程瑶面前,让这个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生物学博士犯了难。
尽管很多人都在劝他去985高校,但是该校从2014年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程瑶的师姐也在这所高校任职,看看师姐的朋友圈常常吐槽自己为了升职“身心俱疲”,程瑶有点望洋兴叹。
让程瑶恐惧的“非升即走”制度,是内地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举措,即新聘任的教师(一般是助教或讲师)在试用的期限内,达不到晋升副教授等更高级别的考核标准,将遭到淘汰解雇,或者调至非教研岗位。
“压力太大,危机感很强。”这是程瑶询问师姐的意见后,师姐给他的回复。
在“非升即走”政策成为许多高校改革的通行做法时,如何让这个改革真正焕发出优胜劣汰的导向作用,而不是唯科研成果论英雄的又一出口,是政策制定者最需要着力的地方。
舶来品的二十余年
陈芒在2017年刚刚评上副教授。
和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一样,陈芒所在的东南大学实行“非升即走”的政策——讲师有“3+3”聘期,聘期内评不上副教授,就不会再续聘。
“非升即走”(up-or-out)一词源起于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这一规则在美国高校得到普遍使用,是指给予新进教师若干年试用期,签订短期合同,试用期满接受考核,通过考核者获终身教职,反之必须离职。
这类包括“分级流动”和“末位淘汰”的人事制度已在欧美高校通行半个世纪以上,旨在鼓励竞争、促进流动,保证最优秀的师资力量。
从1993年清华大学部分院系试点“非升即走”,内地高校的这项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断断续续走了二十余年。
清华大学规定,在为期3年的合同期内,初级职务最多两个聘期,中级职务最多3个聘期,如不能向上一级晋升则不予续聘。副教授以上经过一定期限后可长期聘任。
而这种竞争淘汰机制,来源于企业的员工管理和激励制度。20世纪40年代,北美高校借鉴企业经验实行“非升即走”制度。
目前,实行或部分实行“非升即走”的院校,在国内已小有规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名牌大学,青岛大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等发达地区的院校,均已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
陈芒介绍,“非升即走”,就是不能升职就走人,而对符合标准留下来的教研人员,则可获得长期教职。
不同高校的标准各有不同,考核标准包括科研成果、论文发表数量和同行评议结果等,而试用期限在3年到9年不等;而有的高校甚至还有针对整个学科教师集体的“非升即走”。
“压力山大。”回忆起评副教授的日子,陈芒依旧心有余悸。
“除非学术实力非常突出,影响投票的因素还有人情、利益、行政需要等。”陈芒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教授专门撰文指出,我国的人情关系比较复杂,同行评议,往往流于形式的多,送人情的多,难以作为可靠依据。因此,能否获得晋升,主要是学院或者系评审委员会委员起决定性作用。
而同一学院或者同一系内部,往往是不同专业的人来竞争有限的指标,不同专业的人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结果,评审过程经常成为不同专业之间的平衡。晋升标准的把握比较难。
对此,陈芒感同身受,评审教授来自各个专业,无论他们对陈芒的研究领域懂不懂,都有权投票。“让搞理论研究的教授评搞工程研究的老师,感觉不公平,要不怎么说隔行如隔山。”陈芒说。
为了争取人情,陈芒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还会挤出时间帮教授写书,带学生。“因为这些都是投票的教授。”陈芒很无奈。
陈芒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评上副教授,因为一旦评上,按照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将“非升即走”和长期聘任的年薪制结合起来,形成“预聘-长聘”(tenure-track)制,也称“常任轨”制度。
这实际上也是北美国家高校较为常见的人事制度。
争议不断
这个初衷良好的改革设计,在过去的推动进程中却争议不断。
支持者认为,把竞争和淘汰引入大学,是一次为中国大学寻找新路的尝试。
随着“双一流”系列配套政策和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政策的出台,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鼓励高校教师打破“铁饭碗”、在财力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开“绿灯”,成为近两年政策的主要倾向。
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在描述这次改革时曾表示,北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北大每个终身教授都是一流学者。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赞成“非升即走”的制度。他表示:“从大的方面看,这是治庸的方法,不养庸人,优化教师队伍。”
但质疑的声音也屡见不鲜,很多遭到解雇的高校教师认为遭遇不公正待遇,与校方大闹公堂。
2004年7月12日,清华大学教师刘求生将清华大学告上法庭。
此前,刘求生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6年,2003年,清华不再与他续约。刘求生自称是“清华人事改革赶走的第一位副教授”。
2014年,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在外文系通过述职答辩,但因为之前签订合同中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因此,从2004年起任讲师的方艳华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
清华大学决定不再续聘方艳华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50多封、4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
一名学生留言说:“一个老师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越多,自然会在学术科研上投入的精力变少。对学生来说,我们更渴望的是像方老师一样的老师,带领我们走入真正的英语写作。学校的‘非升即走’政策能否将学生的意愿考虑进去呢?”
最后,方艳华与校方达成一致,转岗为职员。然而,因“辞方事件”产生的“教学与科研孰重孰轻”成为争论的核心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搞教学不搞科研在研究型大学是混不下去的,但国外大学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与我国存在诸多根本的不同。”
他介绍,国外对大学教师的管理和考核由独立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进行,看重的是教师的学术能力与贡献,而不是看论文的数量和是否发表。
熊丙奇认为:“如果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就不会有清晰的办学定位,而‘非升即走’将更加营造急功近利的大学学术氛围。”
难点在评价体系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曾表示,问题并不在“非升即走”制度本身,而在于许多高校目前还未建成完善的教师评估体系。
教师升与不升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评价,遇到不公正评价如何申诉,流动的渠道是否通畅等,都需要明确。而评估标准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当前许多高校的年薪制不是给教师“减负”,而是“加负”。
实际操作中,不乏一些“无厘头”的考核方式。
陈芒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某些学校涉及“非升即走”的考核标准,要求被考核者3年内甚至1年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这种考核方法,实际上是违背科研规律的,科研成果的生产一般是波动的,而非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平均“产出”。
而关于“谁升谁走”,国外大学普遍采用“评审制”,对“升”没有名额限制,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国内高校则多采用“名额制”,指标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而关于近些年围绕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争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早前曾撰文论及。
他的总结是,此项改革的难点在于,一方面,改革者在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理念和方案方面存在差异——大学与企业的差别、学术标准与行政程序之间的矛盾等,都是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如何落地的实际问题。全国各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试验大多数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引入一些“新人新办法”的增量尝试,很少有系统性的整体改革。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