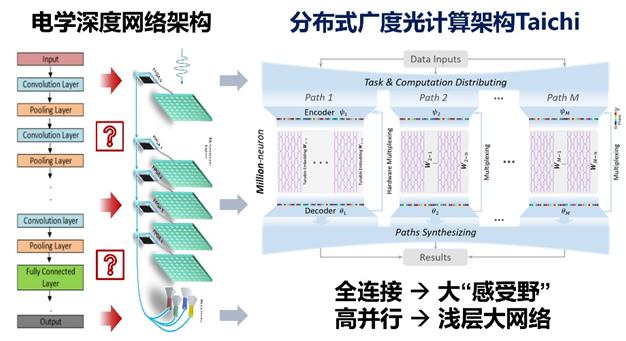“非升即走”在中國高校
資料圖
從清華大學部分院系試點“非升即走”,內地高校的這項人事制度改革,已經斷斷續續走了二十餘年,其間爭議不斷
法治週末記者高原
是去一所省級高校做一個有編制的講師,還是去一所985高校做一名承受非升即走壓力的副研究員,這個問題擺在程瑤面前,讓這個剛剛從美國回來的生物學博士犯了難。
儘管很多人都在勸他去985高校,但是該校從2014年開始實行“非升即走”制度,程瑤的師姐也在這所高校任職,看看師姐的朋友圈常常吐槽自己爲了升職“身心俱疲”,程瑤有點望洋興嘆。
讓程瑤恐懼的“非升即走”制度,是內地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項舉措,即新聘任的教師(一般是助教或講師)在試用的期限內,達不到晉升副教授等更高級別的考覈標準,將遭到淘汰解僱,或者調至非教研崗位。
“壓力太大,危機感很強。”這是程瑤詢問師姐的意見後,師姐給他的回覆。
在“非升即走”政策成爲許多高校改革的通行做法時,如何讓這個改革真正煥發出優勝劣汰的導向作用,而不是唯科研成果論英雄的又一出口,是政策制定者最需要着力的地方。
舶來品的二十餘年
陳芒在2017年剛剛評上副教授。
和國內多所知名大學一樣,陳芒所在的東南大學實行“非升即走”的政策——講師有“3+3”聘期,聘期內評不上副教授,就不會再續聘。
“非升即走”(up-or-out)一詞源起於美國高校的終身教職制度,這一規則在美國高校得到普遍使用,是指給予新進教師若干年試用期,簽訂短期合同,試用期滿接受考覈,通過考覈者獲終身教職,反之必須離職。
這類包括“分級流動”和“末位淘汰”的人事制度已在歐美高校通行半個世紀以上,旨在鼓勵競爭、促進流動,保證最優秀的師資力量。
從1993年清華大學部分院系試點“非升即走”,內地高校的這項人事制度改革,已經斷斷續續走了二十餘年。
清華大學規定,在爲期3年的合同期內,初級職務最多兩個聘期,中級職務最多3個聘期,如不能向上一級晉升則不予續聘。副教授以上經過一定期限後可長期聘任。
而這種競爭淘汰機制,來源於企業的員工管理和激勵制度。20世紀40年代,北美高校借鑑企業經驗實行“非升即走”制度。
目前,實行或部分實行“非升即走”的院校,在國內已小有規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名牌大學,青島大學、深圳大學、汕頭大學等發達地區的院校,均已開始實行“非升即走”制度。
陳芒介紹,“非升即走”,就是不能升職就走人,而對符合標準留下來的教研人員,則可獲得長期教職。
不同高校的標準各有不同,考覈標準包括科研成果、論文發表數量和同行評議結果等,而試用期限在3年到9年不等;而有的高校甚至還有針對整個學科教師集體的“非升即走”。
“壓力山大。”回憶起評副教授的日子,陳芒依舊心有餘悸。
“除非學術實力非常突出,影響投票的因素還有人情、利益、行政需要等。”陳芒告訴法治週末記者。
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柯炳生教授專門撰文指出,我國的人情關係比較複雜,同行評議,往往流於形式的多,送人情的多,難以作爲可靠依據。因此,能否獲得晉升,主要是學院或者系評審委員會委員起決定性作用。
而同一學院或者同一系內部,往往是不同專業的人來競爭有限的指標,不同專業的人很難用一把尺子衡量,結果,評審過程經常成爲不同專業之間的平衡。晉升標準的把握比較難。
對此,陳芒感同身受,評審教授來自各個專業,無論他們對陳芒的研究領域懂不懂,都有權投票。“讓搞理論研究的教授評搞工程研究的老師,感覺不公平,要不怎麼說隔行如隔山。”陳芒說。
爲了爭取人情,陳芒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學和科研任務,還會擠出時間幫教授寫書,帶學生。“因爲這些都是投票的教授。”陳芒很無奈。
陳芒告訴法治週末記者,所有的努力都是爲了評上副教授,因爲一旦評上,按照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將“非升即走”和長期聘任的年薪制結合起來,形成“預聘-長聘”(tenure-track)制,也稱“常任軌”制度。
這實際上也是北美國家高校較爲常見的人事制度。
爭議不斷
這個初衷良好的改革設計,在過去的推動進程中卻爭議不斷。
支持者認爲,把競爭和淘汰引入大學,是一次爲中國大學尋找新路的嘗試。
隨着“雙一流”系列配套政策和高等教育領域“放管服”政策的出臺,賦予高校更大自主權、鼓勵高校教師打破“鐵飯碗”、在財力支持、科研成果轉化等方面開“綠燈”,成爲近兩年政策的主要傾向。
北京大學前黨委書記在描述這次改革時曾表示,北大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北大每個終身教授都是一流學者。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吳江贊成“非升即走”的制度。他表示:“從大的方面看,這是治庸的方法,不養庸人,優化教師隊伍。”
但質疑的聲音也屢見不鮮,很多遭到解僱的高校教師認爲遭遇不公正待遇,與校方大鬧公堂。
2004年7月12日,清華大學教師劉求生將清華大學告上法庭。
此前,劉求生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任教6年,2003年,清華不再與他續約。劉求生自稱是“清華人事改革趕走的第一位副教授”。
2014年,清華大學外文系講師方豔華在外文系通過述職答辯,但因爲之前簽訂合同中規定“就職9年未評職稱的老師必須離職”,因此,從2004年起任講師的方豔華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後期限。
清華大學決定不再續聘方豔華後,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畢業生共計50多封、4萬餘字的請願書,希望將這位“因全身心投入課堂教學導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師留在教學崗位。
一名學生留言說:“一個老師在教學上投入的精力越多,自然會在學術科研上投入的精力變少。對學生來說,我們更渴望的是像方老師一樣的老師,帶領我們走入真正的英語寫作。學校的‘非升即走’政策能否將學生的意願考慮進去呢?”
最後,方豔華與校方達成一致,轉崗爲職員。然而,因“辭方事件”產生的“教學與科研孰重孰輕”成爲爭論的核心問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只搞教學不搞科研在研究型大學是混不下去的,但國外大學對教師的管理和評價與我國存在諸多根本的不同。”
他介紹,國外對大學教師的管理和考覈由獨立運行的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進行,看重的是教師的學術能力與貢獻,而不是看論文的數量和是否發表。
熊丙奇認爲:“如果不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大學就不會有清晰的辦學定位,而‘非升即走’將更加營造急功近利的大學學術氛圍。”
難點在評價體系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陳武元曾表示,問題並不在“非升即走”制度本身,而在於許多高校目前還未建成完善的教師評估體系。
教師升與不升的標準是什麼,由誰來評價,遇到不公正評價如何申訴,流動的渠道是否通暢等,都需要明確。而評估標準的不完善,也造成了當前許多高校的年薪制不是給教師“減負”,而是“加負”。
實際操作中,不乏一些“無厘頭”的考覈方式。
陳芒向法治週末記者介紹,某些學校涉及“非升即走”的考覈標準,要求被考覈者3年內甚至1年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和完成一定數量的科研成果。這種考覈方法,實際上是違背科研規律的,科研成果的生產一般是波動的,而非每年或者每隔幾年平均“產出”。
而關於“誰升誰走”,國外大學普遍採用“評審制”,對“升”沒有名額限制,只要達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國內高校則多采用“名額制”,指標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
而關於近些年圍繞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爭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早前曾撰文論及。
他的總結是,此項改革的難點在於,一方面,改革者在大學人事制度改革的理念和方案方面存在差異——大學與企業的差別、學術標準與行政程序之間的矛盾等,都是爭論的焦點;另一方面,實施過程中,存在大量的如何落地的實際問題。全國各大學的人事制度改革試驗大多數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引入一些“新人新辦法”的增量嘗試,很少有系統性的整體改革。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