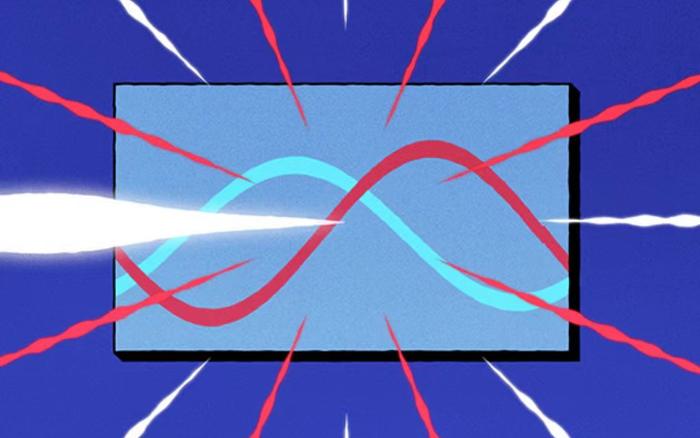300年前的哲學問題,腦科學回答上了?

封面:由包子爲神經現實設計
歡迎關注“創事記”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天生盲人復明帶來的哲學問題,科學能解決嗎?
文/曹安潔
來源:神經現實(ID:neureality)
莫利紐克斯問題上的爭鋒
“假設一個人天生失明,現在已經成年。他能通過觸摸來分辨材質相同、大小相同的立方體和球體。”愛爾蘭作家威廉·莫利紐克斯(William Molyneux)在致友人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信中寫道,“然後,如果我們將立方體和球體放在桌子上,讓這個盲人突然復明:問,在觸摸這兩個物體之前,剛剛恢復視力的盲人是否能辨別出哪個是立方體,哪個是球體?”
這個在一定程度上由他的盲人妻子所啓發的問題,在後來成爲世世代代哲學家們交鋒的戰場。哲學家們以見微知著聞名,對於那些正在探究人類知識的起源、心靈的本質的哲學家們來說,這看似無足輕重的思想實驗——如今也被稱作莫利紐克斯問題(Molyneux's Problem)——是一個極爲關鍵而迷人的問題。
作爲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他的《人類理解論》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是堅定的“否”。他認爲,儘管這位盲人已經擁有關於立方體和球體對他觸覺影響的經驗,但是他尚未獲得這些物體對他視覺影響的經驗,從而也無法建立觸覺與視覺間的關聯。換句話說,洛克相信,我們所有的知識都必須通過感官體驗獲得,這個立場也稱爲經驗主義。

— Alejandro Guipzot
與此相對的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認爲並非所有知識都來源於經驗,而這一派傾向於對莫利紐克斯問題給出肯定的回答。理性主義的代表哲學家萊布尼茲認爲,人類出生時就擁有形狀的心理表徵。這樣的表徵由不同的感官模式共享,無論是觸覺還是視覺,它們觸發的都是相同的心理表徵。因此,如果人可以通過觸摸來區分立方體和球體,那麼,他自然也能通過視覺區分二者。
幾個世紀以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不斷交鋒,雙方都爲自己的觀點進行了激烈的辯護。但是就如同大多數的哲學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也始終沒有定論,直到腦科學進入人們的視野。
“光計劃”給出的答案
2005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組研究人員,在帕萬·辛哈(Pawan Sinha)的帶領下,發起了致力於幫助印度盲童的“光計劃”(Project Prakesh,“Prakesh”在梵語裏是光的意思)。他們幫扶的目標是先天患有可治癒眼疾的盲童。可治癒的眼疾主要有兩類:白內障和角膜混濁。在發達國家,這類異常通常是在嬰兒期被發現的,孩子們在很早的時候就能得到治療。然而不幸的是,由於醫療條件不佳,很多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孩子無法得到及時的治療。
而光計劃的目標就是幫助這些孩子。與此同時,研究人員也獲得一個理解人類大腦的獨特機會。在團隊幫助盲童恢復視力的過程中,他們偶然發現可以藉此探索莫利紐克斯問題:他們所治療的許多患者在青春期末期都保持着失明的狀態,那麼,在復明之後,這些人是否可以區分立方體和球體呢?

光計劃宣傳照 圖片來源:projectprakash.org
五名光計劃的受益者參加了這項實驗。在他們當中,年齡最小的孩子只有8歲,而年齡最大的已經16歲。這五個孩子全都患有先天性角膜混濁。在手術之前,他們的視覺能力都不足以支持他們辨別形狀。這些孩子們在手術前接受了一些觸覺上的訓練。研究人員保證他們可以通過觸摸的方式來區分二十對三維物體。而在他們的第一隻眼睛接受手術之後的48小時內,研究人員們立即對他們進行了“匹配樣本”(match-to-sample)測試。這些孩子們會首先通過視覺或觸覺來熟悉一個物體,之後,他們需要在給定的兩個選項中,挑出與他們熟悉的物體所匹配的那個選項。根據測試的分組,這些孩子們接觸選項的方式是用眼睛看,有的時候則是用手摸。
這些孩子們在用觸覺熟悉過一個物體之後,能準確地用視覺辨認出那個物體嗎?莫利紐克斯問題的答案,似乎近在咫尺。
實驗的結果或許會讓經驗主義者們歡欣鼓舞。這些僅獲得48小時視覺經驗的參與者們,並不能很好地用視覺辨認出剛剛用觸覺熟悉過的物體。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能力的確不能全然歸於視覺能力。如果這些孩子們在一開始就是通過視覺來熟悉物體,那麼他們在測試階段,也能準確無誤地用視覺辨認出那個物體。這樣的視覺辨識能力與觸覺相當。也就是說,問題或許只存在於在於視覺和觸覺之間的對應關係上。
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令人感到驚奇的。在除了慶祝四個孩子恢復視力之外,我們是否也應該趁機慶祝一番莫利紐克斯問題的落幕呢?而我們也是否應當恭喜經驗主義者,他們在三百年前就已經掌握了正確答案呢?
是辨認不出,還是立體感缺失?
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簡單。
在哲學家約翰·史威克勒(John Schwenkler)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如果想完成光計劃的研究團隊所設計的任務,被試們不僅僅需要擁有視覺與觸覺之間的對應關係。視覺和觸覺之間的差異,不光在於兩種感官信息的 “現象學”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兩種感官系統中包含的空間信息也不同。這些被試在通過觸覺熟悉物體時,往往可以通過多種角度觸摸這個物體。然而,當被試在使用視覺來接觸物體的時候,他們僅僅能面向物體的一面。儘管研究人們允許這些被試調整自己的視角,但他們從未規定過這些被試調整視角的頻率。在這種情況下,用視覺和觸覺進行比較似乎有所不公。

— Mete Kaplan Eker
無獨有偶,哲學家邁克爾·布魯諾(Michael Bruno)和埃裏克·曼德爾鮑姆(Eric Mandelbaum)也強調了莫利紐克斯問題中的模糊性。這個問題可以被拆解成兩個小問題:第一,這些復明的人是否能將二維的正方形和圓形與觸覺上的刺激相關聯。而第二個問題,纔是三維物體在觸覺與視覺上的聯繫。早在洛克寫作的十七世紀,光學家們就已發現我們收到的視覺信息其實是二維的。洛克本人就曾寫道,當人們看到一個凸面的時候,人們看到的其實是 “一個有各種陰影的扁平圓”。我們之所以能感知三維物體,是因爲我們擁有足夠的視覺經驗,能夠即時地進行一些“判斷”,從二維的視覺信息中構建出一個三維物體。
而在光計劃進行的一項較早的研究中,研究小組發現,這些復明的患者們即使在數週和數月的康復後,仍然難以辨識三維物體。比如說,當看到三維物體時,這些患者會告訴研究人員他們看到了多個物體。他們報告的物體數量正好對應於他們可以能看到物體的多少面。這樣的證據表明,這些患者們的視覺系統很難利用陰影線索,將同一個物體的不同幾面整合成一個個體。
因此,光計劃的孩子們不能通過視覺辨認出觸覺上所熟悉的物體,也許是因爲視覺上的立體感缺失,而並不一定源於視覺和觸覺兩種感官經驗間缺乏對應關係。
大腦可塑性的暗示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莫利紐克斯問題之所以還不能落下帷幕,也許與大腦的可塑性有關。也許,這些被試者在人生早期沒有得到所必需的視覺刺激,他們的視覺皮層的功能已異於常人。除非光計劃能將這些患者的大腦皮層也重新排布,否則,將他們視爲莫利紐克斯問題中那個“復明人”只能是答非所問。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兩位傑出的神經科學家,託斯坦·維厄瑟爾(Torsten Wiesel)和大衛·休伯爾(David Hubel)曾做過一系列開創先河的工作。他們發現,如果剝脫了小貓剛出生兩個月時的視覺經驗,這些小貓的外側膝狀體中的細胞會出現明顯萎縮的症狀,而這恰好是視覺通路中的關鍵組成部分。這一發現與之後的許多研究一起,表明大腦的發育也許有一個“關鍵時期”。在此期間,外部環境的變化會對大腦的功能型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儘管我們的大腦在一生中都保持可塑性,但這種隨着經驗而變化的能力唯在“關鍵時期”達到頂峯。在這期間,突觸的可塑性,神經元彼此形成連結、改變連接的能力,都達到頂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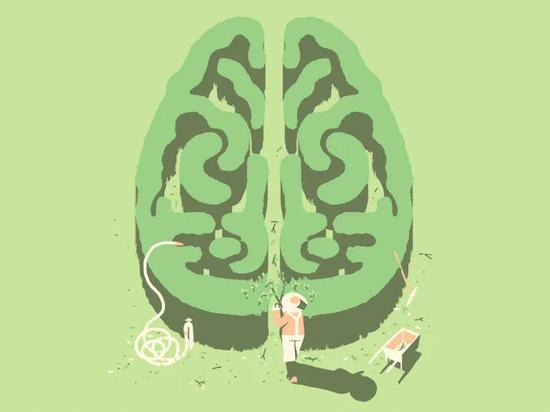
— FM Illustration
有大量證據表明,失明會如何改變大腦的功能組織。九十年代末期,就有研究表示盲人在閱讀盲文時,會出現從中枕葉到雙側紋狀皮層的增強激活。而這些區域在正常人中,通常被認爲是主要負責加工視覺信息。不僅如此,研究人員還發現,當盲人從事語音處理任務,或者聽覺定位任務的時候,視覺皮層中都會出現激活增強。顯然,失明帶來的影響超出了“看不見”的範圍。也許,這些患者沒有像光計劃或經驗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完全康復”。
光計劃的研究雖然有趣且意義深遠,但它提供的證據,仍然不能給莫利紐克斯問題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
科學可以回答哲學問題嗎?
歸根結底,莫利紐克斯問題只是一首序曲。它背後,是一個更宏大的問題: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隨着科學的發展,有朝一日,我們是否能夠通過科學回答哲學問題?
奎因(W.V. Quine)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創造了“自然化認識論”(naturalized epistemology)一詞。他曾經寫道:“認識論,或類似的東西,應當作爲心理學的一章,被歸入自然科學之中。心理學研究一種自然現象:即一個自然人類主體。”在他後期的學說中,他還補充道,自然化認識論並不僅僅依託於心理學。認識論也應當從神經學、物理學中尋求答案,在最後,它應當被視爲工程學的一個分支:“規範化認識論是工程學的一個分支,它是一項尋求真理的技術。”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認同這樣的“自然化認識論”,認爲認識論應當從自然科學中尋找答案。很多人提出了反對意見。一些人批評它循環論證,而另一些人則認爲這種方法遺漏了認識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規範性。心智哲學家金在權曾經論證過規範性的重要性。“……很難相信,當認識論缺失了規範性的時候,當它缺乏適當的規範性證明或證據的概念的時候,”金在他的書中評論道,“(這樣的自然化認識)與傳統認識論還有什麼樣的共同點。除非,自然化認識論與古典認識論涉及一些相同的問題,否則,很難看到一種流派如何能取代另外一種,或者放棄(一種更好的方式)選擇另外一種方式。”
科學可以回答哲學嗎?這個問題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也許,我們應當採取的策略,不是去猜測“最終答案”花落誰家,哪個學科笑到最後,也不是去猜測哪個學科應該被另一個學科取代。在理想的情況下,哲學應當能從經驗科學中受益,反之亦然。
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被問及他對科學哲學在心理學、人工智能和神經科學的作用時,他幽默地回答:“當然是討人厭了。”這位傑出的哲學家、邏輯學家隨後解釋說:“ ……科學哲學最激動人心的任務,是將科學概念的澄清和科學理論中可能的影響相結合——其中包括已經提出的理論和尚未得到證實的理論相結合——從而解決重大的形而上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