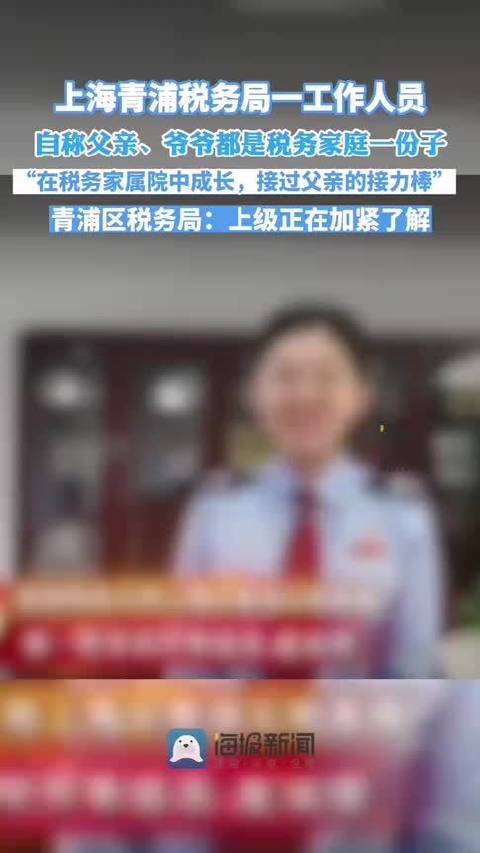野生動物養殖有何生態風險?伴侶動物是否立法禁食?
摘要:在判斷哪些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可以歸入家畜家禽的時候,僅依據“是否人工養殖利用時間長、技術成熟、已被廣泛接受”這類經濟技術指標可能還不夠,若能再增加以下標準更好:看符合前述指標的人工養殖動物是否發生顯著的遺傳變異而去除了野性,是否有利於野外種羣的生存,以及是否可以制定屠宰檢疫規程。野生動物人工養殖與動物保護究竟應該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原標題:野生動物養殖有何生態風險?伴侶動物是否可以立法禁食?)
野生動物人工養殖與動物保護究竟應該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從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羣衆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後文簡稱《決定》)至今,仍是很多人困惑的問題。
2月25日,我們推送了一篇與野生動物保護相關的圓桌採訪(《食用野生動物,終於全面禁止了》),根據後臺留言反饋,有讀者對人工養殖爲何無助於野生動物保護、生態倫理與經濟利益孰輕孰重等問題表示不解。此外,人們也關心,與人類關係親密的伴侶動物,是否也能夠立法禁食?動物表演,是否也會侵害動物的權益?
爲此,我們再度採訪了法學、動物研究和動物保護相關的學者與一線動物保護工作者。其實已經有很多鮮活的例子表明,商業性人工養殖會導致野生動物保護陷入困境。
全文要點
關於野生動物養殖的生態風險:
(1)沒有任何研究證據顯示,現存的野生動物可以再被馴化。
(2)“以養代保”的商業性繁育利用不利於野生動物保護。
(3)目前南非的許多繁育場,已成爲洗白野捕非洲灰鸚鵡的最大中轉站。
關於《野生動物保護法》:
(1)如何定義“野生動物”?
(2)《野生動物保護法》有哪些改進空間?
(3)伴侶動物(貓、狗)可否立法禁食?
關於野生動物展示展演:
(1)野生動物展演,動物投餵、合影、表演互動等零距離接觸,皆存在公共衛生風險。
(2)商業性動物表演損害動物福利。
沒有任何研究證據顯示
現存的野生動物可以再被馴化
孫全輝
博士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家
新京報:近日通過的《決定》中,野生動物非法交易得到禁止。對此,你怎麼看?
孫全輝:《決定》主要針對疫情防控,通過擴大範圍,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有助於從源頭上防範和控制重大公共衛生安全風險。因爲近年來全球各地暴發的重大疫情,主要源自陸生野生動物,且和人類食用行爲密切相關。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野生動物的其他利用?
孫全輝:科學研究和教育展示如果是非營利性的,要保證動物福利(動物生存的基本需求),避免給動物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和虐待,應該加快制定相應的保護配套措施,並給予支持和鼓勵。但是,把野生動物用於娛樂表演、保健治療、異域寵物等目的,會給野生動物造成嚴重的傷害和虐待,並且同樣存在公共衛生安全隱患,若能出臺引導政策,支持相關企業逐步轉產轉型,將有助於更好地保護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展演(動物表演)是一種嚴重傷害動物的商業娛樂活動,目前已被許多國家和城市明令禁止。如今更應該禁止人與野生動物近距離接觸,禁止馴獸、動物展演(動物表演)以及近距離拍照、觸摸、騎乘等活動。其實早在2011年1月,我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動物園管理的意見》就要求“停止所有動物表演項目。”動物展示要服務於公衆教育目的,禁止用於商業娛樂。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重點任務分工方案的通知中提出,要加強珍稀瀕危野生藥用動物保護,支持珍稀瀕危中藥材替代品的研究和開發利用,給中藥行業未來發展指明瞭方向。事實上,中藥自古就不主張使用動物,有“藥王”美譽的唐代醫學大家孫思邈就曾說過,“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我國使用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入藥不到30年,也非中藥的傳統。此外,對藥用野生動物的獵捕、養殖、運輸和交易也同樣存在公共衛生安全隱患,並且已經嚴重威脅穿山甲等瀕危野生動物的生存和保護。在中藥當中,草藥和礦物藥的比例接近90%,野生動物佔比很小。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推薦在治療新冠肺炎使用的“清肺排毒湯”,全部是草藥和礦物藥。因此,緊要關頭,治病救人往往是草藥,而野生動物藥的功效和作用則往往被商業誇大。有關部門若能順應中藥的未來發展趨勢,早日出臺時間表,引導和支持相關企業轉產轉型,將會有助於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新京報:此前野生動物養殖有哪些潛在的疫病風險和生態安全風險?對野生動物保護造成了哪些破壞?
孫全輝:我國大規模圈養繁殖和經營利用野生動物的歷史只有幾十年,而畜禽被人類馴化的歷史少則數千年,多則上萬年。沒有任何研究證據顯示,現存的野生動物可以再被馴化,因爲動物能否成功馴化是多種歷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個過程在現代無法複製。雖然技術上存在改造野生動物基因的可能性,但這將極大挑戰科技倫理和生物倫理,需要格外謹慎。
物種的基因差別是造成物種差異的根本原因。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的基因跟野生個體沒有顯著差別,也沒有產生適應人工圈養環境所需的遺傳特性的改變,因此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依然還是野生動物。在人工飼養條件下,圈養的野生動物的行爲有可能表現得馴服
(tame)
,不是馴化
(domestication)
。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同樣需要法律保護,特別是動物福利方面的保護。在進化上,野生動物就是爲了適應自然環境,也正因爲如此,人類跟野生動物才能“保持安全距離”,我們跟野生動物才能相安無事。
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若澤·格拉齊亞諾·達席爾瓦
(José Graziano da Silva)
曾表示,影響人類的現有和新出現的病原體中,有超過60%來源於動物,其中75%來自野生動物。野生動物常常是各種病毒、細菌和寄生蟲的宿主,如果人類違背自然規律,把野生動物(不論是否爲人工圈養繁育)用於娛樂、當作寵物、用於藥物,就可能增加這些病毒、細菌和寄生蟲向人類傳播擴散的風險,並危及人類的健康。有些病毒甚至對於人類是致命的,目前還沒有特效藥。例如,蝙蝠身上可能攜帶數百種病毒,穿山甲、刺蝟、蛇等身上都有着大量寄生蟲,浣熊還是狂犬病的自然宿主。
但野生動物不是罪魁禍首,是人類利用野生動物的方式出了問題。在利益的驅動下,大量的野生動物被捕捉、飼養和販賣,淪爲交易的犧牲品。如果人們違背自然規律,把野生動物殘忍地用於娛樂、當作寵物、用於藥物,就會增加這些病原微生物向人類傳播擴散的風險,不僅威脅生態安全,也危及人類的健康和生命。
紀錄片《刺蝟的一年》截圖。
新京報:不少人認爲,通過人工馴養繁育是可以保護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野生動物和養殖場並不衝突。你怎樣看待這種觀點?
孫全輝: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要看服務於什麼目的。對於少數極度瀕危的野生動物,爲了拯救野外隨時可能滅絕的種羣,有時的確需要藉助人工繁育手段,擴大其人工種羣,然後通過野化訓練,再把人工種羣重新引入野外。在科學上,這種做法叫作“物種保育”
(species conservation)
或“重引入”
(reintroduction)
。
不過,人工繁育手段不是野生動物保護的常規手段,往往是在其他保護措施和努力均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應用。從以往國內外大量保護實踐來看,通過人工繁育手段在野外成功重建種羣的瀕危物種屈指可數。我國對麋鹿、朱䴉、大熊貓、老虎、野馬、揚子鱷等瀕危物種開展人工繁育幾十年,雖然部分動物被嘗試引入野外,但離重建野外種羣的最終目標還相去甚遠。
《我們誕生在中國》劇照。
拯救瀕危野生動物固然重要,但棲息地是野生動物的生存之本,只有保護好現存野生動物的棲息地,減少影響野生動物生存的各種威脅,纔是最有效的保護野生動物的手段。實踐證明,“以養代保”的商業性繁育利用缺乏科學依據,也無助於野生動物保護。很多打着“保護”旗號的人工繁育項目,其實是爲了獲取商業利益。
在貿易和需求的持續威脅下,野生動物的整體生存狀況並不樂觀,繼續允許野生動物繁育經營的商業化利用,會加劇瀕危物種的生存危機,甚至削弱國家和國際社會在野生動物上付諸的努力。此外,允許商業繁育利用野生動物還誤導公衆對野生動物保護的科學認知,打擊公衆參與野生動物保護的積極性。更嚴重的是,養殖、運輸和利用過程中,人跟野生動物必須頻繁接觸,這給原本依附在野生動物上的病毒創造了跨界傳播的機會,也給公衆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帶來嚴重隱患。
新京報:也有一部分觀點認爲,現在的野生動物保護需要機構來承擔,而保護機構又絕大部分依靠在特種養殖場上,從某些層面來講,這是最容易管理的。你怎麼看?
孫全輝:目前已有的救護中心和動物園確實無法妥善安置所有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至於具體如何處理,還需要根據養殖動物的情況進一步研究。
野生動物保護是一項公益事業,就好比我們保護大氣、水源和我們的環境,受益的是每一個人。但是如果保護不好,每個人都可能成爲受害者。把野生動物保護跟養殖掛鉤是以往“爲了利用而保護”的錯誤觀念的遺毒。例如,不少地方成立的野生動物救護機構使用的是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名稱裏也有“繁育”二字,但救助的野生動物未必需要繁育,也未必能夠繁育,即便可以繁育,後代也未必能夠放回野外。野生動物保護如果一味逐利,很難做好。
BBC紀錄片《地平線:我們該關了動物園嗎?》海報
新京報:野生動物檢疫的作用是什麼?此前野生動物是否存在盜獵洗白的問題?
孫全輝:野生動物監管是一項複雜而系統的工作,檢疫非常關鍵,它如同一道紅線,將不符合檢疫標準的產品阻擋在市場之外。《動物防疫法》、《食品安全法》以及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中都有這方面的內容。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如果缺乏相應的檢疫規程,那麼這些以肉食爲養殖目的的野生動物,作爲食物只能非法流入市場。
以現有的技術和管理,很難區分某個物種的野外種羣和人工飼養種羣。人工繁育的成本遠高於野捕,消費者也更加青睞,導致此前大量非法制品以“洗白”的方式進入合法貿易,而且有些養殖場經常到野外捕捉野生動物,然後與圈養的野生動物交配,防止圈養的種羣退化。在需求的驅使下,偷獵和走私加劇,一些野生動物的生存狀況也雪上加霜。
最典型的例子是非洲灰鸚鵡,它以高智商及超羣的語言天賦受到市場的青睞。在野外,非洲灰鸚鵡主要以羣居生活。被囚禁在牢籠或室內的灰鸚鵡會承受巨大的壓力,因爲缺乏社交且無聊,它們用喙撕扯自己的羽毛。過去40年中,200萬~300萬隻非洲灰鸚鵡遭到偷獵,每年遭到捕獵用於國際貿易的灰鸚鵡數量佔其野生種羣的21%。野外偷獵的非洲灰鸚鵡,有30%-66%會在交易前死亡。其種羣數量在過去50年中下降了79%,加納境內99%的野生種羣已經消失。非洲灰鸚鵡被認爲在多哥區域性滅絕。目前南非的許多繁育場,已成爲洗白野捕非洲灰鸚鵡的最大中轉站。
非洲灰鸚鵡。
此前的種種問題,人工繁育許可管理混亂、缺乏有效監管是問題的表象,深層原因是把野生動物當作資源利用的觀念在作祟。功利的保護觀已經過時,如不盡快摒棄,將繼續阻礙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從野生動物保護的公益屬性出發,應該將野生動物的利用和繁育嚴格限定在科學研究、公衆教育和拯救極度瀕危物種等公益目的,讓商業利益讓位於公共利益,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伴侶動物
可以立法禁食嗎?
錢葉芳
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教授
新京報:《決定》中規定了陸生的野生動物(包括養殖的)禁止食用, “野生動物”該如何與家畜家禽進行區分?
錢葉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對《決定》的解答中認爲,除常見的家畜家禽外,還有一些動物(如兔、鴿等)的人工養殖利用時間長、技術成熟,人民羣衆已廣泛接受,所形成的產值、從業人員具有一定規模,有些在脫貧攻堅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這些動物列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也屬於家畜家禽。
在判斷哪些人工養殖的野生動物可以歸入家畜家禽的時候,僅依據“是否人工養殖利用時間長、技術成熟、已被廣泛接受”這類經濟技術指標可能還不夠,若能再增加以下標準更好:看符合前述指標的人工養殖動物是否發生顯著的遺傳變異而去除了野性,是否有利於野外種羣的生存,以及是否可以制定屠宰檢疫規程。
以梅花鹿爲例,我國人工飼養梅花鹿已有200年曆史,但基本生物學特徵依然未變,野性十足,與野外種羣之間沒有明顯差異,一般人難以區分。因爲包括盜獵、野外取種在內的各種原因,野生梅花鹿已經成爲高度瀕危的物種。這說明梅花鹿並不符合家畜的特性,將“人工馴養梅花鹿從野生動物保護名錄中解除”只有經濟價值,而無生態意義。而且,養鹿業迄今都沒有建立起一套全鏈條完善的檢疫規範體系。
故宮慈寧宮花園鹿舍中的梅花鹿。(圖片來自2018年6月5日新京報報道《故宮梅花鹿誕下“鹿寶寶”》)
新京報:我們該如何看待野生動物養殖業與皮草行業的經濟損失?
錢葉芳:靠養殖野生動物獲取的經濟效益在重大疫情面前微不足道。據《中國野生動物養殖產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2017年),2016年,我國食用、藥用、毛皮、觀賞、寵物、實驗用等野生動物養殖產業的專兼職從業者有1409萬多人,創造產值5200多億元人民幣。據光明網3月3日報道,自武漢疫情暴發,各級財政疫情防控補助資金已經超過1087.5億元。中國每天損失3000億元,間接損失、長期損失難以計數,逝去的生命、破碎的家庭、精神創傷等更是難以計價。
此外,毛皮、藥用在內的野生動物養殖企業大多是散戶,對環境造成了較爲嚴重的污染。至於藥用,傳統中醫藥多以草藥爲主,動物入藥可由草藥或西藥替代,現代技術也足以研發出人工替代品。人工麝香、人工牛黃、人工虎骨,上世紀90年代末都紛紛投產。在法律上做出修訂,將有助於野生動物養殖業轉型。
在這個問題上,亟待我們反思的是,在公共衛生安全、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三大社會價值和基本國策面前,如何看待少數人的經濟利益和奢侈需求?法律是一種利益平衡機制,然而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必須是正當的,不得有損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對於野生動物養殖產業,我們完全可以設計合理的退出機制,以其他致富途徑、就業渠道和人工藥物替代。
林麝。林麝、馬麝、原麝三種動物雄體香囊中的乾燥分泌物爲麝香。傳統方法爲殺麝取香,現在已能製造人工麝香。
新京報:人們還關心狗肉食用是否能夠立法禁止?
錢葉芳:《決定》將動物分爲野外生活的野生動物和人類飼養的家畜家禽兩大類。首先需要釐清的一個問題是,犬和貓到底是野生動物還是家畜?目前貓未被列入《中國畜禽遺傳資源目錄》,部分地方名犬被列入。未被列入的貓類和一般田園犬,如果被定位爲野生動物,當然不可食用。但是,從長久以來犬貓與人之間形成的親密關係來看,應當將其納入家畜。這就有必要將畜禽進一步分爲可食用的、屠宰必須檢疫的經濟動物,不可食用的伴侶動物。
《爲什麼貓都叫不來》劇照。
2月26日發佈的《深圳經濟特區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擬禁食寵物,理由是:“人類長期以來有餵養貓狗等動物作爲寵物的習慣,寵物與人類建立起比其他動物更爲親近的關係,禁止食用寵物動物是人類文明的共識,寵物也應當列入禁止食用的範圍。”其實寵物一詞用得不夠恰當,建議將“寵物”改爲“伴侶動物”。因爲,任何動物都有可能被當作寵物飼養,但人類伴侶動物只有犬、貓兩類。
在《動物防疫法》上,伴侶動物只有產地檢疫規程,沒有屠宰檢疫規程,這與其他食用性家畜不一樣。國務院食品安全辦《關於犬類屠宰許可和監管問題的覆函》
(食安辦函〔2015〕25號)
明確給出了國家不能制定犬類屠宰規程的理由:目前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絕大多數國家均沒有犬類屠宰檢疫的相關規定或要求;我國尚無明確的肉用犬品種,市場上銷售的犬以個人散養爲主,來源複雜,且存在毒殺和偷盜犬類現象,食用狗肉存在較大潛在風險;犬類屠宰和食用狗肉涉及動物福利等問題,國際國內廣泛關注,一旦處理不當,將會產生負面效應。
在犬、貓的處理問題上,《深圳市市場監管局關於狗肉安全監管的處理意見》
(深市監食[2014]8號)
認爲:“國家尚未出臺貓、狗屠宰檢疫規程以及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對屠宰後的貓肉、狗肉不簽發《動物檢疫合格證明》,不能成爲貓肉、狗肉等肉類無須檢疫的依據。因此,在國家法律法規對此已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當依法履行職責。”
《一條狗的使命》劇照。
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決定》出臺後,犬、貓是應當被歸於禁食的野生動物還是可食用的家畜?顯然這種非黑即白的劃分是以動物的生存環境爲標準的,對伴侶動物來說非常不合適。我們也不至於說,爲了滿足這種劃分,強行將犬、貓都納入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制定屠宰檢疫規程,使之成爲可食用的動物。爲了解決這個難題,建議迴歸《動物防疫法》,以防疫爲標準,將動物劃分爲可食用的動物(農場經濟動物)、不可食用的動物(野生動物、伴侶動物、實驗動物)兩大類。其中,伴侶動物歸於家畜,也即,確認歸入《中國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家畜家禽可再分爲“食用”與“非食用”兩類。
拯救表演動物
應當從法律層面全面禁止動物表演
胡春梅
“拯救表演動物”項目發起人
新京報:野生動物展示是否伴隨着隱蔽的公共安全風險?
胡春梅:在《決定》的第四條,“展示”二字,相比《野生動物保護法》第27條寫入的“展示展演”,讓我們看到一些可能有所變化的信號。國家林草局、農業農村部已經相繼發佈了落實該《決定》的通知,林草局提到“防止濫用、虐待等不當方式”。
人畜共患病會對人和動物均造成傷害。例如2014年12月開始,陝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養中心的四隻大熊貓相繼感染犬瘟熱病死亡,隨後,國家林草局發佈通知“嚴禁遊客與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近距離接觸”。鯨豚類水生動物攜帶的人畜共患病病原,包括布魯氏菌、丹毒絲菌、鉤端螺旋體、杯狀病毒、流感病毒、痘病毒等。一些飼養員被痘病毒感染造成皮膚疾病的也有報道。感染結核病的大象對人類同樣具有潛在健康風險。但是現在動物投餵、合影、表演互動等零距離接觸的活動依舊氾濫,存在公共衛生的風險。
表演的動物在嘈雜複雜的環境下,處於應激狀態,可能逃逸或者傷人。自2014年以來,與野生動物展演相關的安全事件發生18起,造成3人死亡、11人受傷。2019年9月,一隻老虎在馬戲團表演時逃出,第二天才被抓獲。
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人工種羣的食用、藥用、商業性的標本也並不合理。例如大鯢、中華鱉、穿山甲、虎骨、豹骨、犀牛角等。
紀錄片《海豚灣》劇照。
新京報:爲了保護動物,你發起了“拯救表演動物”項目,可否簡單介紹一下動物表演行業的現狀,以及這個項目目前取得的進展?
胡春梅:我們初步統計大陸地區的動物園約有580個,其中240個(41%)有動物表演,此外,還有一些臨時性表演未納入統計,流動性太大。除了動物表演本身的虐待外,背後的標本、非法食用、盜獵等問題也需要關注,例如廣東的雷州案,動物園、馬戲團將活老虎非法交易食用,還有耍猴人非法盜獵收購野生獼猴等。
好的進展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反思動物表演問題,一些動物表演取消或有所改善。很多城市的動物園在逐步取消動物表演,比如天津、杭州、廣州、福州、上海等。中國國際馬戲節自第四屆也取消了動物表演。珠海長隆馬戲場館的填海項目未獲批准。雲南民族村、南寧動物園減少了象鉤的使用。
新京報:在“動物表演”行業,是否也存在着商業性人工繁育養殖、野捕進口的現象?這對野生動物、對自然生態造成了哪些危害?
胡春梅:存在,動物表演行業本身就是商業性的。幾乎所有的鯨豚、黑猩猩、非洲象、海獅來自野捕進口。野捕會給動物造成巨大壓力,甚至帶來致命的威脅。
有研究對瓶鼻海豚和虎鯨社羣進行建模,發現鯨豚族羣裏某些個體在團結社羣上起到關鍵的作用。如果這些個體被抓走了,鯨羣很可能失去凝聚力而四分五裂。許多動物很可能在野捕過程中死亡,或由於捕獲的壓力而在被野捕後很快死亡。
國內在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老虎、黑熊等商業性繁育也威脅着野外種羣,增加盜獵。有研究指明1986-2010年,我國黑熊的野外種羣減少了93.4%。一個數量銳減的轉折點是在1986年,也就是我國活熊取膽開始興起的時候。一些馬戲團也與東北的養熊場有動物交換。
紀錄片《我和黑熊一家》劇照。
新京報:“拯救表演動物”項目反對馬戲團的動物表演,呼籲國家立法禁止流動性的動物表演,主要原因是流動演出過程中野生動物的生存狀況和“福利待遇”很難得到保證。但很多人也提出,許多正規的馴獸專家對動物非常保護。馬戲團是不是基本都存在虐待動物的問題?馬戲表演是否應該全面廢止?
胡春梅:動物表演場的喧鬧、人羣密集,就已經有違動物福利,存在公共安全隱患。而且動物表演項目大多是擬人化的雜耍、非自然行爲,想要訓練以讓動物形成條件反射,是不可能僅通過正向的食物刺激等方式完成的,必然會使用負面的飢餓、鞭打、捆綁等訓練方式,在我們以往的調查中也能看出這一點。
此外,動物飼養條件、技術、人員、醫療等差異很大,無強制執行的標準,對人畜共患病也缺乏基本的檢疫與研究。除了野捕,很多表演動物的標識不清,未在監管之下,也會流入非法貿易,例如老虎。
在一定程度上,動物表演就是對野生動物的濫用與虐待,住建部幾次發文要求動物園杜絕一切動物表演。應當從法律層面全面禁止馬戲表演。
新京報:2018年3月,全國300家馬戲團團長聯名發佈了一封公開信,請求恢復動物園的動物表演,給馬戲團和表演動物們“重開生路”。對於馬戲團的聯名投訴和聲討,可否談談你的想法?
胡春梅:拯救表演動物項目是以調查事實爲依據,提出建議;以法律爲準繩,開展社會監督;以動物福利爲標準,倡導更爲科學仁善的娛樂方式。此前,數百家馬戲團聯名投訴信中的很多內容是捏造的不實內容。其中部分馬戲團違法違規利用野生動物,對民間保護打擊報復。
新京報:在貫徹現代動物保護理唸的過程中有不少困難,尤其難以貫徹的是“觀念”——傳統的動物表演理念與現代動物保護理念是相悖的。很多馬戲從業人員認爲,動物表演是保護動物的一種方式。你怎樣看待人類馴化動物表演的傳統?我們如今應該擁有怎樣的動物保護觀念?
胡春梅:我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關於動物保護、尊重自然的內容,應當保持優良傳統,去除糟粕。馴獸在以往的歷史中只是零星的記載,絕大多數是猴戲、馬術,並不是像現在大規模的產業形態。
隨着文明的發展和科學研究的深入,野生動物人工繁育與保護的觀念和管理方式等也相應轉變。比如住建部發布的《全國動物園發展綱要》裏,兩次提到嚴禁動物表演。越來越多的城市動物園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保障動物福利,提供形式多樣的科普宣傳,服務於野外種羣的保護。而一些馬戲團從業人員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學習,保護理念落後,對動物缺乏正確的認識,對動物更多的是當作財產去保護與利用,而非是一個有生態意義的動物與生命,無法傳遞出符合現代要求的科普宣傳。
對於野生動物,我們應該關注野外種羣及其生態環境,保護不同生態位的野生動物,與動物保持安全距離。
《我們誕生在中國》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