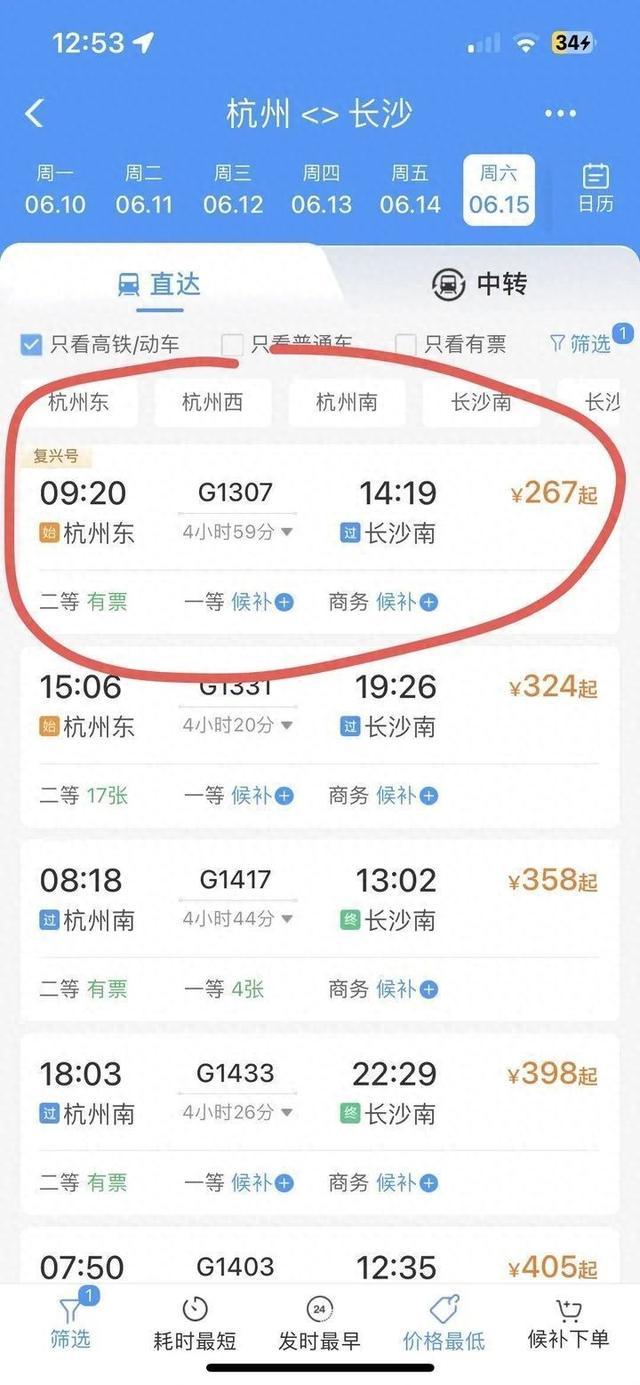薛嶽“天爐戰法”取勝的祕訣
天爐戰法是一種“後退決戰”的戰術。“天爐”是將兵力在作戰帶,布成網狀的據點,以伏擊、誘擊、側擊、尾擊等方式,分段消耗敵軍的兵力與士氣,最後,把敵軍“拖”到決戰地區,再狠狠的圍殲之。它因薛嶽保長沙,敗日軍而成名。當年的中國戰史出版局還曾專門出版了薛嶽撰寫的《天爐戰》一書。書的前言有這樣一段文字介紹:“他(指薛嶽)的戰略戰術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窮宇宙之奧祕,爲鬼神所驚泣,人事所難測,無以名之,故曰《天爐戰》。”
所謂天爐戰法,和“武漢會戰”時所用的倒八字口袋戰法不同之處,在於“袋”只是誘敵深入,然後予以包圍殲滅之。其實是一種“後退決戰”的戰術,誘敵深入,然後予以包圍殲滅之。而“天爐”則是將兵力在作戰地帶,布成網狀的據點,以伏擊、誘擊、側擊、尾擊等方式,分段消耗敵軍的兵力與士氣,最後,把敵軍“拖”到決戰地區,再狠狠的圍殲之。從岳陽下來,近150公里的鐵路沿線,卻有4條河流橫跨其間。薛嶽便以此地形着棋佈陣,由北而南,先是新牆河,這條河的南岸便是防衛長沙的第一線陣地,它的正面從鹿角到麥市,寬達100餘公里,在這裏擺了7個師的重兵,加上幕阜山上的游擊隊,足有10萬人之多。此戰術造成日軍成軍以來大規模會戰的慘敗記錄。經此三戰,指揮長沙大捷的薛嶽被日本人稱爲“長沙之虎”,日寇幾年之內不敢再向長沙發起進攻。它因薛嶽保長沙,敗日軍而成名。
第三次長沙會戰開始後,楊森一面令第20軍向斜後移動,一面令第58軍進入陣地,與第20軍互相配合,協力迎擊日軍,雙方在汨羅江北岸又一次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
當時,雪越下越大,氣溫也越來越低,而守軍許多士兵連棉褲都沒有,有的竟被凍死在戰壕內。但活着的士兵,仍堅守陣地,沒有貪生怕死之輩。
守衛傅家橋據點的第20軍第398團第2營營長王超奎少校及其部屬,面對日軍猛烈的炮火,毫不畏懼,打退了日軍一次次的衝鋒。后王超奎爲掩護部屬突圍,在與日軍肉搏中不幸殉國。守衛洪橋據點的第398團第3營一部,在副營長、連長相繼陣亡的情況下,仍堅守陣地。
第397團全團官兵在黃沙街硬是頂住了日軍第6師團整個師團的進攻,並迫使其繞道而行。激戰至27日晚,第20軍完成了阻敵任務,薛嶽令第27集團軍全線撤退。隨後,第20軍向梅仙、平江方面轉進,隱蔽休整,隨時騷擾日軍後方,待機襲擊其側翼;第58軍向汨羅江東南部轉移,靠近向家、金井,準備切斷進攻長沙的日軍的後路。
豐島和神田指望青木師團快速開到長沙增援,可是青木師團的先頭部隊進抵金井時,被中國守軍的外圍部隊從東、西、北三方合圍,無法突出。等到增援部隊趕來,四百名日軍只剩下二十名,幾乎是全軍覆滅,大隊長和兩名中隊長都被擊斃。
日軍池之上旅團,更是沒有消息。豐島和神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到了晚上,前方的槍聲由緊密而稀疏,最後沉寂。半夜,守軍收到長官部的通報:“第四軍、第七十九軍、第七十八軍、第二十六軍、第三十七軍、第二十軍和第五十八軍已經到達指定位置,開始行動,日軍後路已斷。”
這樣的局面,阿南惟幾在軍伍生涯中還是第一次面對。他不甘心,但他不得不發佈撤退的命令。
1月7日,日軍青木師團好不容易現了蹤影,他們一路留下屍體,艱難地到達春華山一帶,企圖接應北撤的豐島師團和神田師團。
這時,中國第九戰區的部隊,從東南面、東面、東北面、西北面和西面對長沙的日軍發起向心攻擊,實施合圍。前有兵堵,後有尾追,側面也有打擊。第三次長沙會戰,終於到了熔爐升到最高溫度的時候——聚殲日軍。
日軍飢疲交加,傷亡慘重。到15日,日軍退過新牆河,固守原地。第九戰區擔任尾追的各軍追到新牆河以南,還有一支部隊向新牆河以北追擊。湘北地區也成了燒烤侵略軍的熔爐。中國軍隊的激情,洋溢在湘北戰場。
長沙會戰勝利後,蔣介石在黃山別墅周圍的陰霾中感到了暖意。他輕鬆地笑着說:“此次長沙會戰,實爲‘七七’事變以來最確實而得意之作。”薛嶽得到了蔣介石給予他的最高獎賞——青天白日勳章。羅斯福總統也獎給他一枚獨立勳章。 英國《泰晤士報》評價道:“12月7日以來,同盟軍唯一的決定性勝利就是華軍之長沙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