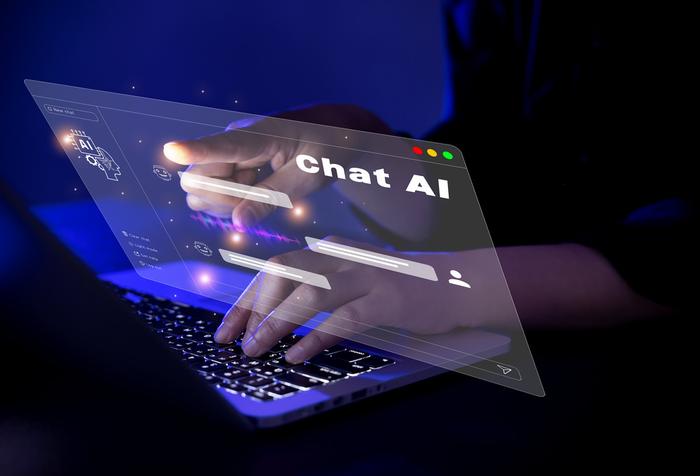安永全的高考
本文是山西省運城市委原副書記安永全對自己高考歷程的回憶,安永全原是一名搬運公司工,經過刻苦努力,兩次高考後終於得以在山西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習,後又做過記者,最後成爲運城市政協主席。安永全成功通過高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這是一個非常真實的現實的寫照,在即將高考的日子裏,希望可以幫到莘莘學子!
《我的高考》
安永全
晚來有閒,到康傑中學高三的文科班看了看。面對就要高考的同學們, 或者說是備受磨難的孩子們。三十八年前靠自修兩次高考之事湧上心頭,多少年來我羞於談的這些事,真的發生過嗎?不提也罷,但幾天下來卻又恍恍惚惚、神不守舍,終於還是按捺不住把它寫了出來。如果這篇並不優秀,當時的心理也不健全,但確是真實的東西,能爲一些同學們增加一點勇氣,我將是非常高興的。
我願把我經歷了失敗的成功獻給你,希望你能用避免了失敗的成功回贈我。
沒上高中,我也要考大學
我沒有上過高中。
我至今都爲此感到遺憾。
我於一九六零年在霍縣初中畢業,學習成績屬於前五名,那一年開學並不考試,而是分配,我自然是要被分配上高中的,但我知道不行——家裏的情況不行。
當時我家住在縣城,八口人,弟兄六人我爲長,父親是售貨員工資三十四元,母親早就對我說,上完初中就別上啦,不然邊底下的小學也上不成,能認得錢就行啦……
我總是說不出來話來。
畢業離校的那一天,我把臉貼在霍縣中學的匾牌上,淚流滿面。
以後,我當過小商販,小工區裝卸工,什麼樣賺錢就幹什麼。那時的工作很好找,但學徒工賺錢又很少,我的年齡也不到。後來,我終於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就是拉人力車,主要是從離城十里路的副食品加工廠給霍縣四個副食品店送醬油、醋,活少時就從大溝煤礦拉煤上街賣,一天大概能賺四元。
那年,我十五歲。
當時,霍縣的東大街是一條長坡,用磚石和碎石鋪的,坑坑窪窪,而第四副食品店又在坡頂上。拉車時,我狠低着頭,伸長脖子,腰弓得幾乎貼住地面,兩手緊抓着轅軒,拼力向前,汗水常把眼睛打溼,前路一片迷茫。到最陡的地段,我簡直懷疑自己是否長着腿,不然,怎麼麻木得一點感覺都會沒有呢?
不管寒暑,不管風雨,我每天都要在這條長坡似的大街頭上,展覽一兩回自己的狼狽。一九六一年的端午節,我多拉了一百斤,在東大街最陡的地方,由於用力過猛,掙斷了肩上的拉繩,臉撞向了地面,開了紅花,失控的平車向後驟滑,穿過路邊的行人和小攤。遇阻而翻過來,車上拉的醬油和醋滿街亂流,驚叫聲和責罵聲混爲一片。
當我終於糊里糊塗地弄清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承受着被撞傷的行人無情的責罵和拳打腳踢,面對着圍觀的人羣中冷淡的目光,看着從臉上抹下的雙手鮮血,特別是發現圍觀的人羣裏竟然有我初中時的同學,我脆弱的自尊心終於被撕破了,竟橫躺在地上號啕大哭!
古云:男兒有淚不輕彈,我從小就不是一個好男兒。
但我終於明白了,生活不相信眼淚。
窮,真是太可怕了,太殘酷了。
因爲窮,你就要忍受痛苦和屈辱;因爲窮,一樣的胳膊一樣的腿,人家能上高中,你就要天天拉平板車。人家能上大學、高中,而你的青春就只能這樣被消磨。
大學,那時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樣。在想象裏大學裏的一切都放光芒,大學裏的人都偉大高尚,前途無量,出來就能當教授、科學家、作家、將軍、首長、更別說讓全家喫飽穿暖!大學啊,那是我從小如癡如迷、如飢如渴的想往,爲什麼就和我無緣呢?
什麼上帝,什麼神仙,什麼沉沉大地,什麼朗朗蒼天,蒼天啊!你究竟有沒有長眼?
蒼天有眼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給澡堂送煤時,認識了高中學生謝俊傑(曾任臨紛市文聯主席,現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閒淡中,他說:高考招生簡章中有一句話,招生對象是高中畢業和具有同等學力的社會青年,後一類對象大概就是指你這號沒有上過高中的人,你可以考文科,文科只考語文、政治、歷史、地理和俄語,不考數理化。
天啊!真是這樣嗎?我問。
我到教育局再給你問問,他說。
第三天,他拿給我一份去年的招生簡章,並告訴我教育局肯定的回答,但又告訴我,教育局的人說,沒上高中考大學,在霍縣可是沒有先例。
我驚喜異常,暗暗下決心,我決不能這樣活,我要自修考大學,什麼先例不先例,我就爲什麼不能成爲先例呢?
陰暗的心靈的天空透出了一絲亮光。
我給你磕個頭,求你給我報上名吧。
我很快就找齊了文科的全部課目,堆起來像座小山,又把家裏放雜物的小房開闢成學習間。 我訂了學習計劃和時間表,早上六點起牀學到八點,喫飯後去幹活,下午六點再學習到十二點,除了拉車就是學習,什麼都有不幹,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想,一本書一本書地啃,一段一段地念,一道題一道題地攻,一個詞一個詞地過,雷打不動,軍令如山,三年課程兩年半學完。
但是,沒多久,我就發現,當初實在是意氣用事,可謂不以其事,不知其難呀!
最難學的是俄語,我以前就根本沒有接觸過任何外語,翻開一看,哎呀!世界上怎麼還有這樣古怪的字呢?我越看越犯愁,越看越沮喪,好幾夜,我就對着天書般的俄語課本在發愣,聽着院裏的雞叫聲,看着窗外越來越亮,一籌莫展,心情壞到極點,就拿起根棍子,又敲桌子,又打幹牆,胡喊亂罵,大罵俄國人,大罵教育部長。
中國人爲什麼要學習外國語言呢?人家蘇聯高考又不考咱漢語,咱們爲什麼要考俄語呢?真他X的!
可是頂什麼用呢?我越罵越感到絕望,後來只好到霍中去找我曾經的化學老師,那時他也教俄語。
張老師非常同情我,但又說,外語不是其他課,在家自修根本不可能,可他還是答應利用晚自習後在他家教我,然而去了幾次後,我就覺得不行。張老師家四口人,房子很小,母親臥病在牀,愛人上班,孩子上學,第三次去時,他愛人的臉色很不好看,學習中間,他愛人還和他吵起來,使我非常難堪。
我已記不清,我是怎樣走出張老師家的,只是覺得怎麼也不能來了,誰想張老師又半路上追上我來賠情道歉,弄得我更加尷尬。他又告訴我不如讓我上初中的弟弟雙全在家教我(那時的霍縣中學也開了俄語課),學起來方便一點。根據前幾年高考俄語試題的情況,初中俄語知識要佔60%的量,如果把初中課程學懂了,能考40分左右,其他四門考得特別好,補上俄語的失分,也許會有機會達到分數線,但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是很難很難,不是一般的難。
親愛的張老師啊!我將永遠永遠記住你的恩情,在那時,只有你把我當人看,當你的學生看。
以後,我就以我弟弟爲俄語之師了,他現學現賣,雖然他水平有限,他的進度也完全制約着我的進度,但比此前有較大的改觀。每天早上,我外出拉車前,我在兩個胳膊上寫五個單詞,一邊拉車一邊念,念一遍俄語再念一遍俄譯文,到第二天早晨再複習一遍,對了,擦掉再換十個單詞寫上,好幾次,念着、念着,把車撞到了人身上,好幾次過往汽車幾乎撞在我身上。我已經顧不了這些了,一定要搬動俄語這座大山,全搬不動,也要搬它一少半。
其他幾門課,我除了地理課輔之以畫圖的方法外,基本上都用中國最傳統的學習方法——背課文。背呀背……背呀背……
在家學習的時候背,拉車時邊拉邊背,平時走路背,喫飯時心裏背。有時集中一門背,有時五門課文叉着背,沒人時大聲背,有人時小聲背,能背下去就繼續往下背,背不下去就查隨身帶,再背。新學的要十遍八遍地背,已經背過的也要反覆地背,背得人暈頭轉向,背得人心煩意亂,背得人腦袋好像要爆炸,嘴也快要說不出來話,古今中外,政、史、文、理內容那麼多,跨度那麼大,一個人的腦袋無非那樣點,但要在很有限的時間,裝進那麼多東西。還要不間斷地一門一門、一層一層、一句一句理清楚,背出來那種感覺不親自經歷,決難想象;而一旦經歷,便終身難忘。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花開花落,暑來寒往背書聲給我換來一個又一個太陽,又把我帶入一個又一個夢鄉。
一九六三年夏天。
我雖然覺得我自學的時間不短,按計劃還要學一年,學得很不紮實,很不條理,明顯存在着很多的空當,但又覺得還不是一塌糊塗,還是掌握了許多東西,特別是覺得應該體驗一下高考的滋味,摸一摸各科試題的深淺。當然又想——也許啊,也許、也許一僥倖會有奇蹟出現。
報名遇上大麻煩
那一天,帶上居委會的介紹信和招生簡章我戰戰兢兢地到了霍縣招生辦,我知道本縣高三應屆的畢業生和複習班的往屆學生都是學校統一報名的,而我這種情況,只有我一個,總擔心不會很順當。
進門後,招辦的人在打撲克,我恭恭敬敬地每人叫了聲老師,把居委會的證明雙手交給一個看上去像領導的人,說:“我想報個名。”誰想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就一下子扔到地上。他問,小夥子你知道什麼叫癩蛤蟆想喫天鵝肉嗎?我說:你說我是蛤蟆我承認,但我不是癩蛤蟆,我說我是好蛤蟆,誰想他一下子就發了火,大聲責問我,好蛤蟆就能喫上天鵝肉嗎?蛤蟆就是蛤蟆!他們又去打撲克去了,我站着等呀等,真不知道該怎麼辦。等他們打完了,我又低聲下氣地說了不知多少好話,還是沒人搭理我,我實在忍不住了,就說,老師,我給你磕個頭,求你行行好,給我報上名,讓我試一試吧……
在霍縣報名、體檢領上准考證後,我就去了臨汾。當時霍縣的考場設在臨汾一中,高考前一天我就坐火車到了臨汾,我是第一次到臨汾,又無親無故,四處打聽才找到考場,我不敢在外面住宿,怕睡過頭了誤了考試的時間,只好就睡在臨汾一中的操場邊上。
兩天考完,又生氣,又悲傷。
有些問題就沒學過,只能看着試卷乾瞪眼,有些是學得不紮實,影影糊糊知道,卻答不上,有些題是時間沒有掌握好,本來能答上,但還沒有答完就被撤了卷,特別是心理素質不強,有的問題過去明明記得很牢,在考場卻怎麼也想不起,越想不起就越着急,越着急就越想不起來。最糟糕的是在考我自認爲最強項的語文時,竟把作文題目“當我唱起國際歌的時候”看成“當我唱起國歌的時候”,一字之差,四十五分就全丟啦,至於我費了千辛萬苦的俄語,下來和別人一對答案,最多隻能得到五分。
唉,第一次高考就這樣收場了。
雖然我本來就是把它當作一次試驗,但還是使我想起了阿Q。
又想起了蛤蟆。
我終於站在了一個新的水平線上鍾
第一次失敗使我成爲了別人的笑料。
第一次高考,引發了我對高考的思考。
高考究竟考什麼?
好像通過答卷考文化知識,其實高考在考決心、考你對高考的認識、考你是否知道高考是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假如你能闖過高考的煉獄,對大多數人來講,纔算具備了走向理想的起碼條件;考你有沒有信心做個有用的人,做個你所羨慕的那種人;考你有沒有決心回報愛着你的人、關心着你的人、期盼着你的人,有沒有決心爲中華民族乃至人類做點事情;貧家的子女有沒有決心改變命運,條件優越家的子女有沒有決心開闢更美好的人生,決心是成功的母親。
高考是考能力,考喫苦精神,考自信心。是啊!美好世界,花季少年,卻沒有了消閒、沒有了浪漫、沒有了歡唱,看到的就是那些冰冷的公式、單詞、試題、還有哪些也許除了應試而毫無用處的東西,它充斥着你、壓抑着你、戲弄着你、折磨着你。而且不是一天、一月、不是一年、二年,如果你能一刻也不減弱自己的努力,如果你能不間斷,是把苦喫下、把苦嚼爛、把苦消化,能感到這是一種幸福,如果你能衝滿自信去面對難關,成功也許並不太難。
有人說高考是科舉制度的翻版,但過去科舉,每年全國只錄取幾百名舉人、二三十名進士,其中一名狀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而如今,雖然有人說高考是獨木橋,但這個獨木橋上每年通過的隊伍畢竟是幾十萬、幾百萬,浩浩蕩蕩……
高考也是考學習的方法。雖然前人已歸納出不少基本方法,但理性的原則對個體來講,都不可能完全適用。世界上沒有兩粒完全相同的沙子,每個人都必須摸索具有個人特色的方法。高考即是戰場,戰場上就是講究戰術,只有冠軍,絕不允許有亞軍,亞軍那就意味着死亡。正確的戰術可以死而後生,正確的方法可以事半功倍。
高考啊,高考,你可以詛罵它是殘酷的、可怕的、沉重的、不公道的,充滿弊病的,但在更完美的制度取代它之前,你還是要面對現實,戰勝自己,戰勝自己的懶惰、脆弱、得過且過;戰勝自己的遲鈍、死板,粗枝大葉,以戰勝高考來武裝自己,武裝到每一個細胞,武裝到每一分每一秒。
我爲自己重新制訂了學習計劃,調整了外語和其他課的投入比例,只學初中外語,放棄高中外語,以達到45分爲目標,以90分的時間和精力使其他四門課均達到85分以上,以強補弱,強項讓它更強。
不就是三十幾本書?
不就是兩千多道題嗎?
爲了加深記憶,不僅要把記住、背會,而且要能基本寫出來,歷史課要做到,把課本書放在一邊,拿兩本稿紙把一個世紀一個世紀、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重大事情,重大人物,重要時間,統統寫出,要做到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差地寫出來,寫不下去就查書,再寫時就容易記住了。
爲了鍛鍊思維敏捷和臨場應變能力,我將各門課的試題,分別寫在紙條上,捲成紙捻子,大題是長捻子,小題是短捻子,放在五個小盒子裏,每次先擺好鬧鐘,抽出五道大題,二十道小題,在兩個小時做完,而後對照課本閱卷打分。
爲了把作文的時間合理化,就自己出了各種體裁和類別的五十道作文題,隨時抽出一道練習在50分鐘內完成,各種試題都如此反覆練習。
我覺得我盡了最大的努力,想盡了能想出的辦法,做到了紮紮實實,步步爲營,我實在不敢拿我的未來去賭博,去僥倖。
然而,人還是無法預料命運。
一九六四年六月,居民小組通知我上山下鄉到西張村,這將意味着我將喪失自修的條件,使考大學成爲泡影。我只能改變再學一年,明年再去高考的計劃,準備第二次倉促上陣。這時距離高考只有十七天。
我又一次來到縣城招辦樓,碰見了又是去年那個人,他說縣上的報名體檢已經結束,地區也只有明天一天時間,看着辦吧。
我已經沒有了選擇。
我趕回家拿了錢,背上書,換了證明,跑到火車站,想坐三點半的車,到臨汾報名,到售票口一看,只見貼着一張公告,因介休至靈石區間被洪水沖斷,列車暫停,預計兩天。
我也被命運激怒了,沒有火車還有兩條腿,乾脆破罐子破摔了,我沿着鐵路線一直朝前走,一百五十華里路走了十二個小時,第二天凌晨到達臨汾,報名體驗結束後,又由臨汾沿鐵路回霍縣,回到家倒頭便睡,睡了一天,醒來後,兩腿腫得水桶一般,腳底像撕爛的紅布片。
我一切都無從顧及了,除了不敢停止拉車,怕大學考不上又丟了飯碗,學得已近乎於瘋狂,除了試題,除了答案,像是一切都不存在,沒有了自己,也沒有了世界,沒有了月亮,也沒有了太陽。
我實施了“頭懸樑錐刺骨”的實踐。
我不知道戰國時的蘇秦和西漢的孫致辭,當年是如何運用這種辦法戰勝疲勞的,而我卻難以奏效。
當我把頭髮紮緊,用繩子吊在屋頂上,不一會兒又沉沉入睡,那種程度的疼痛根本就無法戰勝昏迷似的疲倦。
錐刺骨吧,錐了,刺不出血,不疼就等於不刺,刺得厲害了,倒是有效,三四個小時再也不會睡着,一邊壓着出血的地方,一邊學習,但刺不上幾次,傷口便發生了感染,潰爛。
我想了一個辦法。
我想起了我媽。
我媽是個嚴厲的人,就屬於電視連續劇“大宅門”中二奶奶那種類型的人,記得小時候逃學時被發現,父親把我吊到樹上,拿一根木棍,訓斥聲和動作雖很大,但棍子落在身上並不疼,於是我們繼續逃學,第二次父親又打我時,我媽在一邊看着,並不說話,拿一把鉗子在腿上狠一擰,轉身就走,我大聲一呼,腿上雖沒有出血卻再也不敢逃學,我最愛我媽,也最怕我媽,一見我媽手裏拿着鉗子腿就發抖。
我需要我媽的鉗子,就把這想法告訴我媽。
我媽問我,不考就不行嗎?
我說,不考不行,讓我再試一回。
我媽點了點頭。
那一夜,我又瞌睡了。當然我猛然被大腿的劇疼喚醒時,看見我媽手裏拿着鉗子卻滿臉淚水就再也睡不着了……
在以後的十幾天裏,我媽就守着我學習,雖然她再也沒有用過手裏的鉗子,但我也沒有在學習時再瞌睡過,堅持每天學到凌晨三點。
那一段,是我生命裏的極限。
那一段,是我媽對我的再生。
高考終於來到了,考試終於結束了,政、史、文、理我感覺很好,一想到俄語又十分煩惱。 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度日如年,漸漸地聽說,霍縣中學生的錄取通知書下來了,又聽說文科三十七個人只有一個人考上了“山西大學”,就覺得這一次又完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號,這是我畢生難忘的一天。中午,我正在給家門口附近的商店卸貨,忽見郵遞員拿着一封信,打聽我的名字。那以前,我和外界從沒有信件聯繫,突發的預感使我飛跑過去,接過信,我手顫抖了,好久都不敢去拆,我簡直沒有勇氣去聆聽命運對我控制,當我終於咬着牙打開它時,一張高等院校錄取通知書出現在我的眼前:安永全同學,你被錄取爲山西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請於九月十日前來報到,師院就師院嘛,高興得簡直要瘋狂,竟像范進中舉一樣,在大街上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我終於站在一個新的地平線上。
雖然,我不知道以後將要走向什麼地方。
安永全同志簡介
安永全,男,漢族,1945年8月生,山西省霍州市人,1961年8月輟學打工1974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本科學歷,高級記者。
1961年8月霍縣搬運公司工人;經過刻苦努力,兩次高考後於1964年9月在山西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習;1968年12月任霍縣礦務局宣傳部幹事;1971年1月任省電臺駐臨汾記者站記者、站長;1983年10月任鄉寧縣委副書記、縣長;1987年7月任臨汾地委副祕書長;1988年12月任浮山縣委書記;1993年3月任晉城市副市長;1995年7月任臨汾行署副專員;2000年6月任運城地委副書記;2000年9月任中共運城市委副書記;2003年7月兼任中共運城市委黨校校長;2005年4月任中共運城市政協黨組第一副書記,在政協第一屆運城市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被選舉爲運城市政協主席;2006年2月任中共運城市政協黨組書記;2006年5月在政協第二屆運城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爲運城市政協主席。2010年安永全同志當選爲運城市市慈善總會第二屆理事會會長。
安永全於1970年開始發表作品,200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明天》,散文《遊雲邱山》、《悠悠長街》、《夜宿獨家村》、《琢磨日本》、《我看美國》、《我的高考》、散文集《我的高考》。《遊雲邱山》1985年獲全國優秀遊記散文獎,《夜宿獨家村》1992年獲山西省模範散文獎,《河東文化叢書》(主編)2008年獲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 其中散文集《我的高考》被潘引來導演拍攝爲一段催人奮進的視頻短片,是無數高考學子執筆奮進的動力!
一位原市委副書記的高考,看了之後爲啥都哭了......
來源:公衆號公務員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