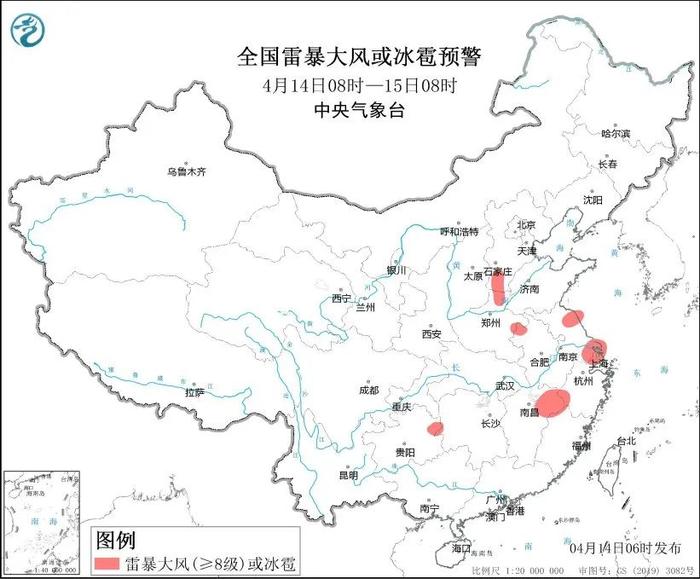遭“跨省”污染的鄉村:村民投訴遭多方“踢皮球”
原標題:再遭“跨省”污染的小壕兔鄉 | 深度報道
記者/韓謙

▷守在垃圾傾倒現場的村民們
地處陝西榆林的北端,與內蒙古烏審旗接壤,小壕兔鄉不只名字來自於蒙語,連污染也來自“隔壁”。
去年5月,行爲藝術家堅果兄弟將來自小壕兔鄉的一萬瓶生活用水,拿到北京和西安展覽,引發廣泛關注。在榆林環保部門對小壕兔鄉多個村莊進行的水質檢測中,多份水樣鐵、錳等指標不合格。
事後,內蒙古的多家煤礦企業,因礦井水存放、外滲等問題,遭到了罰款查處。但內蒙古烏審旗一位副旗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小壕兔鄉的水污染問題與三家煤礦無關,根據當地監測,礦井水鐵和錳的含量小於國家生態環境部制定的相關標準。
時隔水污染事件一年多,小壕兔鄉掌高兔村村民再次舉報,稱有來自內蒙古的建築垃圾傾倒在村裏,混着水管、鋼筋的垃圾陸續運來,最後形成了一片佔地約3000平米的巨大“垃圾場”。
連番因環境污染與內蒙古產生紛爭,小壕兔村民和幹部能想到的原因有很多:兩地界線不清的“歷史遺留問題”,豐富礦產資源背後帶來的排污隱患,以及內蒙古與陝西由高到低的地勢導致礦井水外漫……
據掌高兔村幾位曾去鄉政府反映問題的村民轉述,他們得到的回應是:“跨省排污只有中央才能處理。”
但在接受深一度記者採訪時,一位環境法律專家表示,對於跨界污染的問題,兩地相關管理部門在取證、檢測,以及信息提交等方面的渠道,並非不暢。“不存在管不管得住的問題,關鍵還是管不管的問題。”

▷傾倒在掌高兔村的建築垃圾
邊界上的垃圾
10月17日晚11時左右,掌高兔村的村民注意到,3輛卡車和1臺挖機駛向了村北的那片荒地。自去年9月開始,陸續有水管、鋼筋等建築垃圾被傾倒在這裏,形成了一片佔地約3000平米的巨大“垃圾場”。
當晚,六七位村民聽到消息後趕了過去,他們攔下準備清運垃圾的卡車。“要是偷偷把垃圾運走,那不就沒有證據了,之後不承認這事咋整?”一位村民表示,在賠償談攏之前,不會允許對垃圾進行清運。從那天開始,村民們自發24小時輪班,值守在垃圾旁。
讓掌高兔村民想討個說法的垃圾堆,來自他們的“隔壁”。10月20日,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烏審旗圖克鎮人大主席徐峯向深一度記者介紹,建築垃圾爲該旗所轄呼吉爾特村超藝運輸服務有限公司傾倒,目前已對該勞務公司處以3萬元罰款。
針對垃圾的來源,掌高兔村民認定,來自1公里外內蒙古某煤礦塌陷區的移民拆遷,小壕兔鄉政府人大主席程勇也確認了這一說法。但烏審旗圖克鎮人大主席徐峯則稱,這是內蒙古當地村民建造新房時產生的建築垃圾。
無論垃圾究竟來自哪裏,榆林和烏審旗的政府工作人員都認爲,此次紛爭的根源,是兩地界線劃分不清的“歷史遺留問題”。
在掌高兔村7組一位村民看來,傾倒垃圾的地點本就在他們村子的地界內,冬天時,每家每戶都會去那兒砍植物的枯條,用來燒火取暖、做飯。“這要是內蒙古的地,怎麼能讓我們這麼幹?”
小壕兔鄉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掌高兔村駐村幹部郭廣峯向深一度記者解釋,如果是同屬一個省份,相鄰兩村在進行界線劃分時較易達成共識,而呼吉爾特村和掌高兔村分屬內蒙古和陝西,兩村村民互不承認對方的林權界線。“在涉及兩省交界的地方,這一問題普遍存在。”
據駐村幹部郭廣峯介紹,18日上午,交界雙方民政局勘界辦、國土和林業部門來到現場對省界進行認定,確認傾倒垃圾的地點屬於陝西境內。在傾倒地點20米外,就是榆林和鄂爾多斯的交界處。
但單純界線的明晰,並不能解決小壕兔鄉村民們所有的煩惱,在此次垃圾傾倒事件之前,他們就已經因爲污染問題,與“隔壁”的內蒙古產生過多次紛爭。

▷小壕兔鄉附近有多個煤礦
煤礦旁的村子
無論榆林還是鄂爾多斯,都因豐富的礦產資源聞名,根據兩地政府官網的數據,2018年鄂爾多斯產煤6.16億噸,榆林產煤4.56億噸,兩市產煤之和佔全國總產煤量的約30%。
據此前媒體報道,2011年到2014年間,在鄂爾多斯烏審旗與榆林小壕兔鄉交界處,先後有門克慶煤礦、母杜柴登煤礦以及巴彥高勒煤礦興建投產。其中,母杜柴登煤礦、巴彥高勒煤礦分別靠近小壕兔鄉的掌高兔村和特拉採當村,距離最近處均爲一公里左右。
2015年開始,3家煤礦陸續投產,兩條運煤專線忙碌起來,拉煤的大卡車日夜不停地在兩地交界處駛過,掌高兔村村民陳長峯那時覺得:“咱這地兒說不準能富裕起來”。
慢慢地,陳長峯發現,“煤礦不在陝西,得不到什麼益處,煤礦的污水卻來了。”
多位村民向記者描述,自煤礦投產,小壕兔鄉里開始出現了一系列“怪事”。先是耕地被煤礦排放的疏幹水淹沒無法耕種,十幾米深的井壓上來的水變得渾濁,並帶有明顯異味;羊也開始拉稀,得尿結石,一羣一羣地死;村民得皮膚病、癌症的頻率也比此前高了很多。按照掌高兔村民統計的數據,受煤礦排水影響最嚴重的7組,從2015年開始“因水污染得皮膚病的人”佔24.4%,共11人;7組養殖近1500只羊,得病死亡的羊佔35%左右;耕地被淹200餘畝。
根據媒體報道,一份小壕兔鄉《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顯示,2018年2月,有村民反映門克慶煤礦的污水被直接排放到掌高兔村的林地裏,毀壞植被8000多畝,還淹沒了一公里的柏油路。小壕兔鄉的答覆是:反映問題屬實,我鄉立即採取措施,對污水來源進行堵塞,目前在想長遠解決辦法。
去年5月,行爲藝術家堅果兄弟從陝西省環保廳的投訴欄目裏,看到了關於小壕兔鄉水污染的舉報。之後,灌裝了一萬瓶小壕兔鄉的生活用水,在北京和西安進行展覽,陸續有記者前去採訪,當地政府部門對此事也給予了關注。
2018年6月21日,榆林市環保局宣佈對小壕兔鄉水源污染問題立案調查。榆林市環保局聯合榆陽區政府對掌高兔村四戶村民家的飲用水進行採樣監測,對照《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水中鐵、錳含量均有不同程度超標,最大超標倍數4.2倍。榆陽區疾控中心於去年7月7日發佈的通報顯示,該中心對小壕兔鄉6個村11份生活飲用水進行了水質檢測,其中10份不合格,不合格項目爲鐵、錳等指標。
2018年7月31日,烏審旗政府發佈聲明,對巴彥高勒、母杜柴登和門克慶煤礦礦井水存放、外滲等問題進行徹查,並各罰款50萬元,對4名煤礦管理人員採取行政拘留處置。
然而,內蒙古烏審旗一位副旗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小壕兔鄉的水污染問題與三家煤礦無關,據烏審旗環境監測站監測,礦井水鐵和錳的含量不超過0.10mg/L和0.07mg/L,小於國家生態環境部制定的《煤炭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
在堅果兄弟的行爲藝術後,對村民生活而言,最直觀的變化發生在飲用水上。據榆陽區政府官網發佈的消息,截至去年8月31日,榆陽區環保局爲小壕兔鄉共安裝淨水器3445臺,特拉採當村、西奔灘村、掌高兔村、小壕兔村大壕兔組、東奔灘村、公合村等6個村已打深井12口。
人的飲水問題改善了,但是莊稼、牲畜怎麼辦?村民們覺得,打下更深的井取水,“治標不治本”。

▷村民面對着長勢不佳的莊稼
長不好的莊稼
“(煤礦)把排水管鋪到內蒙古與陝西的省界邊緣,水可以直接漫過來。”陳長峯指出,北高南低的地勢爲此前煤礦向小壕兔排水提供了便利。
內蒙古環保廳2018年6月致生態環境部辦公廳的266號文件顯示,母杜柴登和門克慶煤礦的礦井水蓄水池採用“沙土壩體+聚乙烯塑料防滲膜”模式,因防滲塑料布破損,礦井水向外環境滲漏,存在與地表水混合後向下游小壕兔鄉漫流的現象。
同時,該份文件指出,呼吉爾特村和小壕兔鄉接壤,該地區地形爲沙丘地帶,地下水水位較淺,地表水富集,自然水系發達,呼吉爾特村位於小壕兔鄉上游,常年存在地表滲流由烏審旗依自然地勢形成的泄洪溝渠向小壕兔鄉漫流的現象。
2018年7月7日,榆林市環保局稱,已開鑿3條總長度近200公里的排水水渠,對3個煤礦礦井水進行導流。
一年多時間過去,時下正值玉米收割時節,西奔灘村村民李玉枝總結出今年收成的規律,仍舊是“越靠內蒙古,地勢越低,越難種。”在尚未收割的一塊玉米地,深一度記者注意到,這些玉米杆子高度僅1米左右,臨近收穫的玉米長度不足5釐米。
種玉米和養殖牛羊,是小壕兔農民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掌高兔村村民王長奎共有20多畝地。他承認,今年的狀況的確比前兩年有所改觀,但自己仍有十餘畝地被煤礦疏幹水淹沒,僅剩的六七畝地,收成也並不樂觀,“以前一畝地能有1500多斤收成,好的時候近2000斤,現在只有七八百斤。”
牲畜的飲水問題也未能解決。在掌高兔村一戶村民家中,十幾米深的地下水打上來,肉眼可見依舊渾濁,並帶有明顯異味。
陳長峯把家裏的羊圈養起來,每天從家接深井水給羊喝。“一出去放個三四天,就又會有羊開始拉稀,拉稀拉個七八天就死了。” 王長奎也怕羊再生病,每天都在羊飼料裏摻些防治羊尿結石的藥物。
一名羊販子向深一度記者證實,如今在小壕兔已經很難收到羊。“不敢賣,也不敢發展了。” 王長奎說,近三年來,他的羊從三十多隻降到十來只,陳長峯家裏的羊更是從三百多隻的規模降到了八十多隻。
儘管村民們將牲畜的死亡,與煤礦排水的污染聯繫在一起。但在去年的後續調查中,榆陽區政府認爲,小壕兔鄉人與牲口的死亡均無法判定與環境問題有關。
2018年9月11日,陝西省環境保護執法局發文,敦請榆林市環境監察支隊就小壕兔鄉豬羊死亡、村民得病的情況向當地衛生部門調查覈實情況。此後的一份榆陽區環保局致榆陽區政府覆函中指出,“小壕兔鄉人口總數爲14542人,近三年死亡人數爲181人,不能判定死亡人員死因是由環境問題導致;小壕兔鄉羊子飼養量約12.8萬隻,豬飼養量約2萬頭,該鄉近三年豬、羊死亡率均在1%-2%範圍內,屬正常死亡範圍,未有異常情況發生。同時,未有村組上報村民因環境問題得病情況。”

▷村民質疑當地尚有未排乾的礦井水
跨省治理之困
去年玉米收成不好,西奔灘村的李玉枝曾試着向村裏反映,村幹部回覆,“煤礦下來的水,我們也管不了”。據掌高兔村幾位曾去鄉政府反映問題的村民轉述,他們也曾得到類似的回應,“跨省排污只有中央才能處理”。
“村幹部也沒辦法,我們一個老百姓就更沒辦法了。”問及之後是否考慮過別的渠道反映,李玉枝回覆道。
榆林當地一位不願具名的環保志願者透露,其曾就煤礦排放礦井水一事向環保部門舉報,據該名志願者轉述陝西省環保廳工作人員的回覆稱,“這一問題需要由生態環境部設立在西北和華北的區域督查局進行協調。”
“企業是內蒙古的,污染又轉移到陝西來了。”在這名志願者看來,榆陽區環保局多少有些力不從心。“內蒙古屬於華北地區,陝西屬於西北地區,這不僅是兩省間的跨界污染,而且也是跨地區污染的問題。單由烏審旗和榆陽區兩個縣級的行政機構進行治理,是沒有能力協調這樣的問題的。”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教授指出,我國法律都只規定了地方各級政府管理自己行政區域內的問題,但沒有政府間合作的具體規定,處於污染受害地的下游政府對上游污染企業沒有執法權,“現在仍缺乏綜合性的、跨行政區域的水環境管理法律。”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訴訟部副部長戴仁輝則認爲,設立跨區域的行政執法機構並不現實,“相當於把現在的法律體系和機制打破了。即便是設立區域聯盟,也是一種協調機制,由其彙總一個信息,再把信息反饋給相應的執法部門。”
在他看來,跨界污染治理,不存在管不管得住的問題,關鍵還是管不管的問題。對於地方政府“管不了”的回應,戴仁輝指出,這其實是指地方政府沒有辦法直接跨省執法,對企業採取處罰措施。“但這不是說政府就束手無策,什麼都不能幹了。地方管理部門可以做一些取證、檢測的工作,將這些信息提交給污染髮生地的政府或是環保局,也可以把受污染的情況跟上級部門彙報,由上級部門進行處理,這些渠道都是暢通的。”

▷當地的環保標語牌
“不敢再說了”
據多位村民證實,小壕兔鄉鄉幹部曾在會議上口頭答覆,水淹地較多的村民可以少部分開荒。2018年春,一名村民在自己水淹地附近的林地,用裝載機、推土機推出近20畝新地。2018年年末,該村民和他的其父親因非法佔用農用地被判處拘役4個月,緩刑8個月執行,並處罰金1萬元。
在村中走訪時,一些村民婉拒了記者採訪。“不敢再說了,萬一跟也進去了咋辦?”相對於媒體曝光,他們選擇了更爲“實惠”的方案:談賠償。
去年10月19日,小壕兔鄉政府對掌高兔村村民反映的煤礦廢水排放信訪事項做出答覆,“鄉政府2018年第二季度安排民政救災款項3萬元用於救助受水淹地影響的村民。目前,榆陽區人民政府正在與烏審旗政府就煤礦疏幹水等相關事宜的補償工作展開對接。”
記者向多名掌高兔村村民覈實,3萬元補償款於2018年年底下發,“一個村總共3萬元,到每家每戶也就幾百塊錢。”此外有村民稱,去年年底,鄉政府承諾,對受煤礦疏幹水影響的農田每畝每年賠償500元、賠償3年,該份補償款至今沒有到位。
10月28日,掌高兔村駐村幹部郭廣峯答覆深一度記者,“補償款不是立馬能解決的,政府爭取這些也要有個過程,和內蒙古雙方政府溝通都需要時間。”郭廣峯表示,對於需要多長的期限,此前已向老百姓做出預估。
此外,對於此次建築垃圾傾倒一事達成的賠償結果,村民和政府的說法也並不一致。多位掌高兔村7組村民表示,10月19日晚,鄉政府工作人員召集7組17戶村民召開村民代表會議,承諾由內蒙古方面向7組村民共計賠償20萬元,按各戶人家人口數量進行分配。此後,村民方纔同意勞務公司將垃圾清運。
對於村民口中的20萬元賠償,雙方政府均予以否認。參與此次會議的郭廣峯稱,在會議上並未提及賠償事項,“我們只是跟老百姓做一個溝通,讓他們支持圖克鎮政府把垃圾清運走。” 烏審旗圖克鎮人大主席徐峯則表示,20萬賠償款是“無稽之談”。“內蒙古的勞務公司在陝西地界倒了垃圾,現在由勞務公司負責清運,並復墾綠化,這樣就好了。”
如今,陳長峯總會回憶起,周圍煤礦還沒興起時的樣子。小時候出去放羊,不用帶水,背口鍋就出門了。在地勢較低的沙地裏刨個1尺深的坑,等上十來分鐘時間,又清又甜的水便會漫出來。“架起鍋來,直接燒水、做飯。”
邊上另一位村民打斷了他的回憶,“咱不說這些,你說再多也回不去了。”
(文中受訪村民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