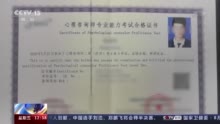余秀华:成名后对生活有些玩世不恭,诗歌也略有退步
2014年,因为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余秀华经历了天上地下两个极端的评价,但她无可置疑地红了,红到了现在。
“经历人们的评价太多了以后,我发现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满足所有人的看法。我是脑瘫,事情一复杂,我就做不好。”在网络舆论中红起来的余秀华如今试着尽可能不去在意别人对自己诗歌的评价。
近日,讲述余秀华真实经历的纪实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跟着电影片方,余秀华来到了上海。
6月28日,余秀华在上海大隐精舍参加了上海市民诗歌节活动:和余秀华谈诗。
两年多来,她出了三本书,参加了不少活动和对谈,离了婚,却从未从大众视野中消失。
活动当天她穿一件旗袍裙,高兴而娴熟地和现场读者招手。虽然仍是身有残疾、经历伤痛的女诗人,但和写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时候的她相比,大部分事情都不一样了。
“是人来养活诗歌,不是诗歌养活人”
在余秀华的诗歌之后,第二件被关注的事情,是她的离婚。丈夫是普通的农村中年男人,丝毫不懂文学,和她无法交流。
在余秀华成名前,她说起离婚,旁人都觉得是笑话。等她有了版税收入,立刻用20万元的代价结束了这段婚姻。
这几乎是一个女诗人的励志故事,诗歌给了她名气,给了她自立的资本,给了她生活下去的能力。
这也成了一些“草根”诗人奉余秀华为圭臬的原因。现场有个小伙子问她,“我也是来自农村,写诗不被家人理解,如果不是来到大城市打工、生活,根本不可能坚持写下去。你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她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所有写诗的人都没想过诗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对她来说,最初选择写诗是为了化解身体上的痛苦。余秀华从小就喜欢文字,没人陪她玩,她就看书、写诗。村干部看到了鼓励她投稿,第一次就发表了,她就义无反顾地写了下去,“无论干什么,对一件事特别钟爱、专注地做一件事就会化解你的痛苦,哪怕你专注的事情是打麻将、下象棋。对我来说,写诗是唯一化解之道。”
余秀华对诗的认识难得地清醒,即使现在诗歌带给了她很多,她仍然坚定地认为,想要靠诗成功成名,动机一开始就错了。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是人来养活诗歌,不是诗歌养活人。”她好像是对自己说,也好像是对借她的成功坚定了自己诗歌信念的一些“诗人”说,“我在农村写诗,也是做完饭、做好活儿,在活计剩余,有时间的时候写诗。一个人要在衣食住行都有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写诗,否则没有可能。”
如今功成名就,最初写诗的动机荡然无存。余秀华觉得“这两年写的诗歌水平有所后退”,“也不是完全后退,就是略微后退。”
她说自己这两年“玩世不恭的心理更多一些”,原来对待生活是十分认真的,但现在,生活和情感都变了,个人也很难维持在最初的状态。
女性的创作很多时候是发乎情感
“我现在住在新房子里难道不能写诗,难道要去找个破房子住?”
在现场,有读者问余秀华,成名之后生活改善了,之前的创作灵感是否也很难保持,她直接“怼”了回去。
“文学的才华是天生的,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只是写作的角度会不一样。随着生活改变,我可能再也写不出以前那些诗歌,但如果为了写诗歌让自己生活环境不变,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谈起如今的写作动机,余秀华顺手拿坐在台下的《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开起了玩笑,“我现在写诗是今天看到叶开很帅,有一点想他,所以写诗。”
这的确是余秀华对诗歌创作的态度,“女性的创作很多时候是发乎情感。”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她的诗歌里总写到爱情,她在物质条件极为恶劣的生活中,最在乎的是丈夫不能给她心灵上的理解,有人问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她说“长得好看的都喜欢”。
有人质疑她写的诗大部分都是情诗、艳诗,甚至是“荡妇体”。余秀华不在乎,“荡妇就荡妇。”
诗人周熙在对谈现场夸《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写得好:“大众可能没读懂她,很多人都只读到了‘睡’,其实那并不是重点,后面才是精华‘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余秀华打断了他,“重点就是睡”。
她好像更会应对媒体和公众了,但又恰到好处地保持着自己那份率直。
“我是脑瘫,事情一复杂,我就做不好。”她坦荡地解释。
余秀华在活动现场给读者签名。
成名两年多,余秀华出了3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我们爱过又忘记》。每本诗集中不乏重复,但也有不少新作。
“我是有底线的,如果是出版社要出书我就签约,那我不知道出了多少书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网上疯传的时候,涌向余秀华家的出版社编辑一天就有好几位,她选了又选,挑了两家同意出书,后来又出了一本情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节制。”她解释自己谨慎出书的原因,“那些著作等身的人,我真是非常怀疑他们的人品。”
如今余秀华似乎拥有了很多东西,但谈起未来,41岁的她难得地有些迷茫,“当我到了35岁时候,是个清晰的分水岭,我觉得自己已经站在未来的分水岭上,现在就是未来,没有什么未来,没有什么期待。”
“诗歌本身是人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才会有什么样的诗歌,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不容易的。” 余秀华说。
「荐赏」余秀华的诗歌两首
诗人简介:
余秀华,诗人,1976年生,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村民。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其行动不便,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余秀华从2009年开始写诗,主题多关于她的爱情、亲情、生活感悟,以及她的身体状况和无法摆脱的封闭村子。2014年11月,《诗刊》发表其诗作,有很多优秀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新闻媒体。
《 感谢》
◎余秀华
阳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杨树
和白杨树的第二个枝丫上的灰喜鹊
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
我坐在一个门墩上
猫坐在另一个门墩,打瞌睡
它的头一会儿歪向这边
一会儿歪向那边
阳光从我们中间踏进堂屋
摆钟似乎停顿了一下
继续以微不足道的声音
摆动
2014年12月5日18:39:23
诗评:
《易·谦》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谓尊者谦虚而显示其光明美德;谦虚。还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王弼注:“牧,养也。”高亨注:“余谓牧犹守也,卑以自牧谓以谦卑自守也。指以谦卑自守。在我选择的余秀华的一些诗里,诗人懂得谦卑自守,所以其诗显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感谢》里,诗人对生活已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抱有感恩的心理。所以诗中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真善美的情怀。怨怼荡然无存。
“阳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杨树
和白杨树的第二个枝丫上的灰喜鹊
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
“阳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杨树”,余秀华的诗里,阳光几乎好多首都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生在阳光中的人感受不到阳光,而诗人却深知阳光的美好,她以感恩的情怀对待阳光和阳光下的事物。那屋檐、白杨树、白杨树的第二个枝丫上的灰喜鹊。“灰喜鹊”让我们想到童话中的灰姑娘。这些都是她的莫逆之交。余秀华好像对“白”情有独钟。写灰喜鹊时,“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诗言志,洁白无暇是她的心志。
但生活对于她毕竟是苛刻的,她没有一个自由之身,她的诗与远方,只有把身边的事物无限放大,所以她发现了许多我们司空见惯却又视而不见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她也是百无聊赖的:
“我坐在一个门墩上
猫坐在另一个门墩,打瞌睡
它的头一会儿歪向这边
一会儿歪向那边”
诗里写了她和猫的无所事事的状态,写的相互掩映,栩栩如生。细节的呈现,使诗歌的质感很好。这也是诗人生命中矛盾解决短暂的平和状态。也是她要感谢的风浪过后平静的美好。有人说低处的低,低到尘土之下,卑微有卑微的美好。
最后一节阳光又出现了:“阳光从我们中间踏进堂屋”,“我们”时她和猫,这句写的诗味很浓,颇具想象力。“踏”写出了阳光的充沛和阳光在她心中的分量。仿佛有声音惊动了他们的安静。真是“鸟鸣山更幽”。“摆钟似乎停顿了一下”,有点时空相对主义的意味。因为她在似睡非睡的状态,所以摆钟停也就是时间停留了一下,似梦非梦,似乎是她在抵达神秘主义。但马上就过去了,像灵感。然后:
“继续以微不足道的声音
摆动”
时间好像微不足道的生命,也在不舍昼夜。总之,这种世界消失了所有矛盾烦恼的静谧,是诗人感谢的生命的状态,这也是诗人的语境理想,是诗意的栖居,是孤独的美。这种栖居是任何浮躁和虚荣所不能抵达的,只有谦卑。也是她的生命存在形式:云上写诗,泥里生活。
《春天》
◎余秀华
可疑的身份
无法供证呈堂。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
能够燎原的火,能够城墙着火殃及池鱼的火
能够覆盖路,覆盖罪恶的雪
我有月光,我从来不明亮。我有桃花
从来不打开
我有一辈子浩荡的春风,却让它吹不到我
我盗走了一个城市的化工厂,写字楼,博物馆
我盗走了它的来龙去脉
但是我一贫如洗
我是我的罪人,放我潜逃
我是我的法官,判我禁于自己的灵
我穿过午夜的郢中城
没有蛛丝马迹
诗评:
春天的意象也是在余秀华的诗里常常出现。但其他诗里的春天似乎很美好,而这首诗里我们似乎看不到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影子,可能诗人对自己的《春天》,别有用心,我们继续看这首诗。
“可疑的身份
无法供证呈堂。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
能够燎原的火,能够城墙着火殃及池鱼的火
能够覆盖路,覆盖罪恶的雪”
“可疑的身份/无法供证呈堂”,有点摸不着头脑,谁的身份?为什么“无法供证呈堂”?是诗人对自己春天的质疑吧:“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雪代表理性,火代表感性。诗人这样呈现感性的自己:“能够燎原的火,能够城墙着火殃及池鱼的火”,里面有褒义有贬义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褒,有“城墙着火殃及池鱼”是贬。诗人又这样呈现理性的自己:“能够覆盖路,覆盖罪恶的雪”,也是好坏兼备,“覆盖路”是不好;“覆盖罪恶的雪”是好。两个口袋一个是火,一个是冰雪之水。表明诗人的命运势同水火,处境水深火热。
“我有月光,我从来不明亮。我有桃花
从来不打开
我有一辈子浩荡的春风,却让它吹不到我
我盗走了一个城市的化工厂,写字楼,博物馆
我盗走了它的来龙去脉
但是我一贫如洗”
诗人在叙述自己世界里的物象时是这样的:有月光、桃花、春风、甚至有城市的化工厂,写字楼,博物馆。可惜“月光,我从来不明亮”、“桃花/从来不打开”、“春风,却让它吹不到我”、特别是,拥有“化工厂,写字楼,博物馆,但是我一贫如洗”。这样的世界可谓灰暗,这样的春天却形同虚设。“盗走”,说明春天是别人的,诗人什么也没有,尽管得到“来龙去脉”。
“我是我的罪人,放我潜逃
我是我的法官,判我禁于自己的灵”
这最后一节是诗人自己对自己的进行解剖,自己对自己进行心灵的进行审判。诗人是双面或多面人生,她的灵魂如浮萍漂泊不定,没有归宿,是她自己把自己放逐了,她毫不留情地欲揭开自己空虚的灵魂:
“我穿过午夜的郢中城
没有蛛丝马迹”
与幽灵一样。她的灵魂孤独的在尘世旷野中行走,不留痕迹,常言: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而卑微的活在人世间的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她的荒凉的世界几乎与春天水火不融,处于对抗的状态。这“春风不度雁门关”的荒凉到底是谁之过?表现了她内心最深刻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