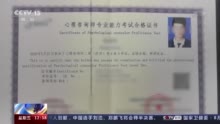餘秀華:成名後對生活有些玩世不恭,詩歌也略有退步
2014年,因爲一首《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餘秀華經歷了天上地下兩個極端的評價,但她無可置疑地紅了,紅到了現在。
“經歷人們的評價太多了以後,我發現不管怎麼做,都不會滿足所有人的看法。我是腦癱,事情一複雜,我就做不好。”在網絡輿論中紅起來的餘秀華如今試着儘可能不去在意別人對自己詩歌的評價。
近日,講述餘秀華真實經歷的紀實電影《搖搖晃晃的人間》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跟着電影片方,餘秀華來到了上海。
6月28日,餘秀華在上海大隱精舍參加了上海市民詩歌節活動:和餘秀華談詩。
兩年多來,她出了三本書,參加了不少活動和對談,離了婚,卻從未從大衆視野中消失。
活動當天她穿一件旗袍裙,高興而嫺熟地和現場讀者招手。雖然仍是身有殘疾、經歷傷痛的女詩人,但和寫出《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那時候的她相比,大部分事情都不一樣了。
“是人來養活詩歌,不是詩歌養活人”
在餘秀華的詩歌之後,第二件被關注的事情,是她的離婚。丈夫是普通的農村中年男人,絲毫不懂文學,和她無法交流。
在餘秀華成名前,她說起離婚,旁人都覺得是笑話。等她有了版稅收入,立刻用20萬元的代價結束了這段婚姻。
這幾乎是一個女詩人的勵志故事,詩歌給了她名氣,給了她自立的資本,給了她生活下去的能力。
這也成了一些“草根”詩人奉餘秀華爲圭臬的原因。現場有個小夥子問她,“我也是來自農村,寫詩不被家人理解,如果不是來到大城市打工、生活,根本不可能堅持寫下去。你是怎麼堅持下去的?”
她毫不留情地頂了回去,“所有寫詩的人都沒想過詩能改變自己的生活,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對她來說,最初選擇寫詩是爲了化解身體上的痛苦。餘秀華從小就喜歡文字,沒人陪她玩,她就看書、寫詩。村幹部看到了鼓勵她投稿,第一次就發表了,她就義無反顧地寫了下去,“無論幹什麼,對一件事特別鍾愛、專注地做一件事就會化解你的痛苦,哪怕你專注的事情是打麻將、下象棋。對我來說,寫詩是唯一化解之道。”
餘秀華對詩的認識難得地清醒,即使現在詩歌帶給了她很多,她仍然堅定地認爲,想要靠詩成功成名,動機一開始就錯了。
《搖搖晃晃的人間》劇照
“是人來養活詩歌,不是詩歌養活人。”她好像是對自己說,也好像是對借她的成功堅定了自己詩歌信念的一些“詩人”說,“我在農村寫詩,也是做完飯、做好活兒,在活計剩餘,有時間的時候寫詩。一個人要在衣食住行都有保障的情況下才能寫詩,否則沒有可能。”
如今功成名就,最初寫詩的動機蕩然無存。餘秀華覺得“這兩年寫的詩歌水平有所後退”,“也不是完全後退,就是略微後退。”
她說自己這兩年“玩世不恭的心理更多一些”,原來對待生活是十分認真的,但現在,生活和情感都變了,個人也很難維持在最初的狀態。
女性的創作很多時候是發乎情感
“我現在住在新房子裏難道不能寫詩,難道要去找個破房子住?”
在現場,有讀者問餘秀華,成名之後生活改善了,之前的創作靈感是否也很難保持,她直接“懟”了回去。
“文學的才華是天生的,不論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都會產生寫作的衝動,只是寫作的角度會不一樣。隨着生活改變,我可能再也寫不出以前那些詩歌,但如果爲了寫詩歌讓自己生活環境不變,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談起如今的寫作動機,餘秀華順手拿坐在臺下的《收穫》雜誌編輯部主任葉開開起了玩笑,“我現在寫詩是今天看到葉開很帥,有一點想他,所以寫詩。”
這的確是餘秀華對詩歌創作的態度,“女性的創作很多時候是發乎情感。”
《搖搖晃晃的人間》劇照
她的詩歌裏總寫到愛情,她在物質條件極爲惡劣的生活中,最在乎的是丈夫不能給她心靈上的理解,有人問她喜歡什麼樣的男生,她說“長得好看的都喜歡”。
有人質疑她寫的詩大部分都是情詩、豔詩,甚至是“蕩婦體”。餘秀華不在乎,“蕩婦就蕩婦。”
詩人周熙在對談現場誇《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寫得好:“大衆可能沒讀懂她,很多人都只讀到了‘睡’,其實那並不是重點,後面纔是精華‘火山在噴,河流在枯’……”
餘秀華打斷了他,“重點就是睡”。
她好像更會應對媒體和公衆了,但又恰到好處地保持着自己那份率直。
“我是腦癱,事情一複雜,我就做不好。”她坦蕩地解釋。
餘秀華在活動現場給讀者簽名。
成名兩年多,餘秀華出了3本詩集,《搖搖晃晃的人間》《月光落在左手上》和《我們愛過又忘記》。每本詩集中不乏重複,但也有不少新作。
“我是有底線的,如果是出版社要出書我就簽約,那我不知道出了多少書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在網上瘋傳的時候,湧向餘秀華家的出版社編輯一天就有好幾位,她選了又選,挑了兩家同意出書,後來又出了一本情詩集《我們愛過又忘記》。
“做什麼事情都要有節制。”她解釋自己謹慎出書的原因,“那些著作等身的人,我真是非常懷疑他們的人品。”
如今餘秀華似乎擁有了很多東西,但談起未來,41歲的她難得地有些迷茫,“當我到了35歲時候,是個清晰的分水嶺,我覺得自己已經站在未來的分水嶺上,現在就是未來,沒有什麼未來,沒有什麼期待。”
“詩歌本身是人的生活狀態,有什麼樣的生活狀態纔會有什麼樣的詩歌,所以我覺得我也是不容易的。” 餘秀華說。
「薦賞」餘秀華的詩歌兩首
詩人簡介:
餘秀華,詩人,1976年生,湖北鍾祥市石牌鎮橫店村村民。因出生時倒產,缺氧而造成其行動不便,高中畢業後賦閒在家。餘秀華從2009年開始寫詩,主題多關於她的愛情、親情、生活感悟,以及她的身體狀況和無法擺脫的封閉村子。2014年11月,《詩刊》發表其詩作,有很多優秀作品發表在全國各大報刊新聞媒體。
《 感謝》
◎餘秀華
陽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楊樹
和白楊樹的第二個枝丫上的灰喜鵲
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
我坐在一個門墩上
貓坐在另一個門墩,打瞌睡
它的頭一會兒歪向這邊
一會兒歪向那邊
陽光從我們中間踏進堂屋
擺鐘似乎停頓了一下
繼續以微不足道的聲音
擺動
2014年12月5日18:39:23
詩評:
《易·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謂尊者謙虛而顯示其光明美德;謙虛。還說:“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王弼注:“牧,養也。”高亨注:“餘謂牧猶守也,卑以自牧謂以謙卑自守也。指以謙卑自守。在我選擇的餘秀華的一些詩裏,詩人懂得謙卑自守,所以其詩顯示了獨特的審美價值。
在《感謝》裏,詩人對生活已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抱有感恩的心理。所以詩中字裏行間,都滲透着真善美的情懷。怨懟蕩然無存。
“陽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楊樹
和白楊樹的第二個枝丫上的灰喜鵲
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
“陽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楊樹”,餘秀華的詩裏,陽光幾乎好多首都有,生在福中不知福,生在陽光中的人感受不到陽光,而詩人卻深知陽光的美好,她以感恩的情懷對待陽光和陽光下的事物。那屋檐、白楊樹、白楊樹的第二個枝丫上的灰喜鵲。“灰喜鵲”讓我們想到童話中的灰姑娘。這些都是她的莫逆之交。餘秀華好像對“白”情有獨鍾。寫灰喜鵲時,“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詩言志,潔白無暇是她的心志。
但生活對於她畢竟是苛刻的,她沒有一個自由之身,她的詩與遠方,只有把身邊的事物無限放大,所以她發現了許多我們司空見慣卻又視而不見的東西,但更多的時候她也是百無聊賴的:
“我坐在一個門墩上
貓坐在另一個門墩,打瞌睡
它的頭一會兒歪向這邊
一會兒歪向那邊”
詩裏寫了她和貓的無所事事的狀態,寫的相互掩映,栩栩如生。細節的呈現,使詩歌的質感很好。這也是詩人生命中矛盾解決短暫的平和狀態。也是她要感謝的風浪過後平靜的美好。有人說低處的低,低到塵土之下,卑微有卑微的美好。
最後一節陽光又出現了:“陽光從我們中間踏進堂屋”,“我們”時她和貓,這句寫的詩味很濃,頗具想象力。“踏”寫出了陽光的充沛和陽光在她心中的分量。彷彿有聲音驚動了他們的安靜。真是“鳥鳴山更幽”。“擺鐘似乎停頓了一下”,有點時空相對主義的意味。因爲她在似睡非睡的狀態,所以擺鐘停也就是時間停留了一下,似夢非夢,似乎是她在抵達神祕主義。但馬上就過去了,像靈感。然後:
“繼續以微不足道的聲音
擺動”
時間好像微不足道的生命,也在不捨晝夜。總之,這種世界消失了所有矛盾煩惱的靜謐,是詩人感謝的生命的狀態,這也是詩人的語境理想,是詩意的棲居,是孤獨的美。這種棲居是任何浮躁和虛榮所不能抵達的,只有謙卑。也是她的生命存在形式:雲上寫詩,泥裏生活。
《春天》
◎餘秀華
可疑的身份
無法供證呈堂。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
能夠燎原的火,能夠城牆着火殃及池魚的火
能夠覆蓋路,覆蓋罪惡的雪
我有月光,我從來不明亮。我有桃花
從來不打開
我有一輩子浩蕩的春風,卻讓它吹不到我
我盜走了一個城市的化工廠,寫字樓,博物館
我盜走了它的來龍去脈
但是我一貧如洗
我是我的罪人,放我潛逃
我是我的法官,判我禁於自己的靈
我穿過午夜的郢中城
沒有蛛絲馬跡
詩評:
春天的意象也是在餘秀華的詩裏常常出現。但其他詩裏的春天似乎很美好,而這首詩裏我們似乎看不到生機勃勃的春天的影子,可能詩人對自己的《春天》,別有用心,我們繼續看這首詩。
“可疑的身份
無法供證呈堂。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
能夠燎原的火,能夠城牆着火殃及池魚的火
能夠覆蓋路,覆蓋罪惡的雪”
“可疑的身份/無法供證呈堂”,有點摸不着頭腦,誰的身份?爲什麼“無法供證呈堂”?是詩人對自己春天的質疑吧:“我的左口袋有雪,右口袋有火”,雪代表理性,火代表感性。詩人這樣呈現感性的自己:“能夠燎原的火,能夠城牆着火殃及池魚的火”,裏面有褒義有貶義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褒,有“城牆着火殃及池魚”是貶。詩人又這樣呈現理性的自己:“能夠覆蓋路,覆蓋罪惡的雪”,也是好壞兼備,“覆蓋路”是不好;“覆蓋罪惡的雪”是好。兩個口袋一個是火,一個是冰雪之水。表明詩人的命運勢同水火,處境水深火熱。
“我有月光,我從來不明亮。我有桃花
從來不打開
我有一輩子浩蕩的春風,卻讓它吹不到我
我盜走了一個城市的化工廠,寫字樓,博物館
我盜走了它的來龍去脈
但是我一貧如洗”
詩人在敘述自己世界裏的物象時是這樣的:有月光、桃花、春風、甚至有城市的化工廠,寫字樓,博物館。可惜“月光,我從來不明亮”、“桃花/從來不打開”、“春風,卻讓它吹不到我”、特別是,擁有“化工廠,寫字樓,博物館,但是我一貧如洗”。這樣的世界可謂灰暗,這樣的春天卻形同虛設。“盜走”,說明春天是別人的,詩人什麼也沒有,儘管得到“來龍去脈”。
“我是我的罪人,放我潛逃
我是我的法官,判我禁於自己的靈”
這最後一節是詩人自己對自己的進行解剖,自己對自己進行心靈的進行審判。詩人是雙面或多面人生,她的靈魂如浮萍漂泊不定,沒有歸宿,是她自己把自己放逐了,她毫不留情地欲揭開自己空虛的靈魂:
“我穿過午夜的郢中城
沒有蛛絲馬跡”
與幽靈一樣。她的靈魂孤獨的在塵世曠野中行走,不留痕跡,常言: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而卑微的活在人世間的她,沒有人知道,沒有人關心,她的荒涼的世界幾乎與春天水火不融,處於對抗的狀態。這“春風不度雁門關”的荒涼到底是誰之過?表現了她內心最深刻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