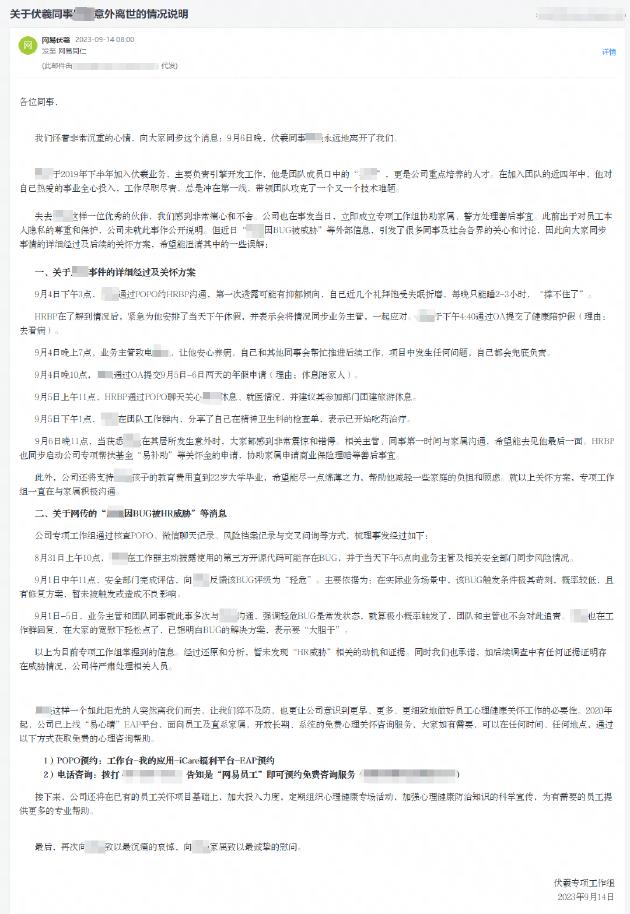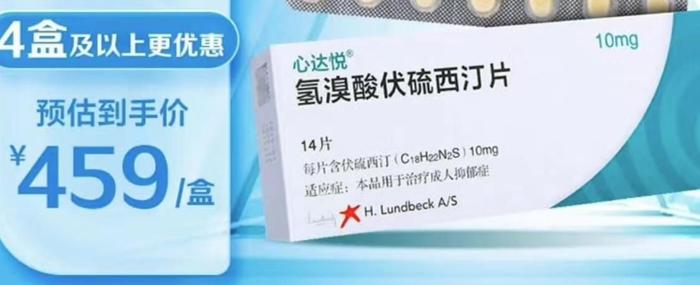滴滴司機被“抑鬱”大學生殺害:抑鬱症不背這個鍋,謝謝!
前幾天刷微博看到澎湃新聞的一則報道:
這件事不知爲何動靜這麼小,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我居然現在才知道。作爲媒體人,每天關注各類新聞已成習慣,尤其是社會新聞,如果媒體關注度足夠密切,我不可能如此後知後覺,除非……當時的報道就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的。
去年,曾發生過多起滴滴司機殺人事件,我當時也寫了文章爲被害者發聲,還做了應急語音供獨自乘車的女孩子們在必要時備用。如今滴滴司機被乘客殺害,社會關注度卻如此稀薄,這並不正常。
我們不能因爲乘客比司機多就不重視司機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價值,也不能因爲自己或家人不是網約車司機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要知道,滴滴司機幾千萬,出現殺人惡魔的概率只是千萬分之一,大多數滴滴司機都是安分守己的正經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爲生活奔波勞碌,披星戴月,早出晚歸,和其他職業的勞苦大衆沒什麼不同。
被害的女孩們是家中的掌上明珠,可被害的司機也是家中的頂梁支柱啊,他的生命同樣重要而可貴!曾經我也思考過,大家都在關注乘客的安全,可是司機的安全誰來保障呢?獨自開車,就不會遇到歹徒或者變態嗎?
只敢想想卻不願看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今年3月23日午夜時分,常德滴滴司機陳宏將乘客楊某淇送達常南汽車總站附近,楊某淇趁陳宏不備,連刺20餘刀致其死亡。案發後楊某淇自稱:殺人系因悲觀厭世精神崩潰,但無勇氣自殺,臨時起意殺人試探膽量,計劃事後投江自盡,後被朋友勸回投案自首。
事情發展到今天,就是我們開頭看到的樣子。楊某被鑑定爲抑鬱症,“作案時有限定(部分)刑事責任能力”。所以呢?想怎樣?抑鬱症也可以加入“豪華免死套餐”了嗎?
當然,法院還沒有最終判決,我們應當稍安勿躁,切莫亂帶節奏。
但,有些舉動,細思極恐;有些怪誕,已成事實。“豪華免死套餐”衆所周知,原有的兩樣——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精神病鑑定書,已經讓社會公平正義蒙上了一層灰色,一些“未成年人渣”有恃無恐,部分“間歇性精神病”爲所欲爲。如果這次殺人事件的最終結局和判決結果真的讓“抑鬱症”背了鍋,或免死,或輕判,那我覺得這個社會真的是沒救了。
倘若抑鬱症也成了罪惡的擋箭牌,那這不僅僅是對社會公義的褻瀆和對受害家屬的愚弄,更是對千千萬萬個真正的抑鬱症者莫大的歧視和侮辱!
抑鬱症的真實面孔,可能並不是我們認爲的那樣。
很多人持續一段時間情緒低落或者意志消沉,變得敏感脆弱、容易傷感,就覺得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鬱症了。有的人通過百度來確診,做各種測試題去對號入座;有的人則連自查都懶得做,一門心思“希望”自己得了抑鬱症,不斷給自己強烈的心理暗示。
曾有一段時間我也懷疑自己得了抑鬱症,因爲一件令我三觀盡毀、信仰崩塌的事(與愛情事業無關,具體不便透露)。持續幾個月的消沉和頹廢,終日菸酒爲伴,拒絕一切社交,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甚至窗簾都不想拉開。但自始至終,我都未曾有過輕生念頭,只是一時找不到生活的意義。後來,通過自我救贖和奮力擺脫,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之後,我諮詢過從事心理學研究的朋友,也做過一系列常規檢查和診斷。朋友給出的結論是,我那段灰暗的日子只是沉浸在比較嚴重的“抑鬱情緒”中,處在輕度抑鬱的邊緣,距離中度抑鬱還隔着一個“認知功能損害”,距離重度抑鬱則差着“輕生念頭”和“木僵狀態”兩座大山。
雖然我不是一個純粹的抑鬱症患者,但我非常能理解並體會到抑鬱症患者和“抑鬱情緒者”的心情和感受。他們並不是喫飽了撐的,也不是傷春悲秋刻意矯情,是真的活得很辛苦、很壓抑,感到生活沒有希望,想擺脫痛苦卻又無計可施,就像是“心情得了重感冒”。
以我對抑鬱症的瞭解,患上抑鬱症的人一般都比較善良,不會把自己的情緒發泄到別人身上。他們大多把攻擊指向內部,也就是自己。即使他們手中真的有一把刀,刀口也會對向自己。他們總是自責甚至自棄,除非極特殊情況或正當防衛,否則不會輕易傷害他人。
曾經在一本權威心理學雜誌上還看到過這樣的說法:殺人犯或者其他恐怖分子一般都不會患上抑鬱症。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抑鬱症患者就一定不會殺人,這太絕對。只是,抑鬱症的本質就是對自身的厭惡和排斥,是自己和自己的對抗。就算是情緒失控害人性命,也不會瞬間感到生命可貴而懼死,更不可能被誰勸到警局去自首。一個活在自由空氣中都消極厭世的人,他們可能受得了世人的譴責之聲和冰冷的牢獄之苦嗎?
所以,殺人就是殺人,不要拿什麼抑鬱症來做擋箭牌。別說受害者家屬不接受這份鑑定報告,就是我個人,以及千千萬萬真正的抑鬱症患者也不會接受這種站不住腳的“甩鍋”動作和推責行爲。
曾在某新聞報刊中看到過這樣一個極端案例,某大學教授被患抑鬱症的妻子所殺。教授生前對妻子照顧有加,怕她一個人在家悶着,還給她安排了一份圖書館的工作。但是妻子一直覺得很痛苦,認爲死亡纔是唯一解脫,並且覺得丈夫悉心照顧自己也一定很痛苦,不如和丈夫一起解脫,所以就導致了悲劇的發生。這位教授當場死亡,妻子殺害丈夫後自殺,但因爲發現及時被搶救了過來。
這場聞者壓抑的悲劇中有一個重點,那就是抑鬱症者並不畏死,殺人動機是爲了“一起解脫”,而不是什麼一時衝動、臨時起意。
由此可見,某些人把殺人罪責甩鍋給“抑鬱症”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我們反對殺人,也反對自殺,但是並不反對殺人者自殺謝罪。所以,逆天逃罪,其心可誅。
滴滴司機被害事件我會持續關注,真的不希望這又是一起“鑽法律空子”“疾病來背鍋”的爛尾案。
最後,我想說三點:
第一,理性關注事件進展。
這件事我也諮詢了學法律的朋友,在刑法上抑鬱症患者具有完全行爲能力,不同於其他精神障礙患者,他們完全能夠判斷自身危害行爲帶來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抑鬱症患者犯罪,不能以其患病爲理由影響量刑。除非是相當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到了無法控制行爲和意志的程度,否則還是該怎麼判怎麼判,故意殺人就要償命。
我看這位“抑鬱楊某”又不敢切腹自盡,又想殺人試膽量,倒挺像個報復社會的廢柴的,相信法律一定會給公衆一個滿意的交代。我們關注進展並期待結果,先不急於下定論起節奏。
第二,請尊重“抑鬱症”及“抑鬱症者”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抑鬱症患者將近一個億。也就是說,每13-14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患有抑鬱症。如果我們還覺得自己是個正常人,是文明社會的一份子而非野蠻人或者單細胞生物,那就請尊重並理解抑鬱症患者。他們不是異類,他們只是“情緒得了重感冒”。我們無需憐憫同情,也不必刻意關注,只需給予接納、肯定和平視即可。
也懇請各路媒體不要再刻意引導和污名化抑鬱症了,這個世界對抑鬱症人的惡意已經夠多了,堅決不能上演現實版的《我們與惡的距離》。犯法就是犯法,與疾病和地域以及特殊羣體無關。給萬事萬物貼上標籤,既無聊又無知,還透着那麼點無恥。
第三,望法律進一步完善,“一視同仁”很重要
法律給予特殊人羣“寬容政策”的初衷,是考慮到病人缺乏是非判斷力和自我控制力,發病期殺人“非本人意願”,故不屬於“故意殺人”。但我想說的是,若精神病患無意識殺人情有可原,那無辜被害的可憐人招誰惹誰了?他們的死又該由誰來負責呢?難道僅僅只用一句“認倒黴”就打發了嗎?精神病患者的命是命,無辜被害者的命就不是命了嗎?
愚以爲,有些法律真的存在漏洞,是時候徹底完善了。任何生命都是可貴的,任何罪惡也都要付出代價。純粹的法治社會不應該存在任何含糊不清的“免死金牌”,因爲它很容易被投機取巧者擄去用以逃避罪責。法律的初衷基本都是好的,但人未必都是好人,尤其在生死麪前,人性之惡超出想象。
如果重刑重罰不能對某些特殊人羣一視同仁,那我希望可以把部分罪責轉移到其監護人身上。法律總要講求個公平公正、人人平等,不能讓任何人白死,也不能讓任何人以任何名義肆意妄爲、逍遙法外。
個人拙見,直抒胸臆。愚鈍之處,切莫見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