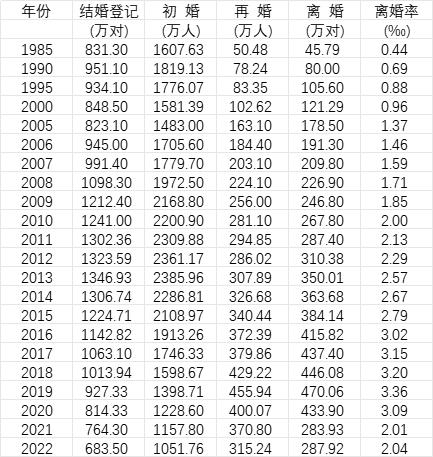李銀河憶王小波:他是我的“灰姑娘”
摘要:我和小波從結婚起就沒打算要孩子,除了兩人的喫住也沒啥花銷,省喫儉用攢的錢基本就都用在了旅遊上。記得小波好友劉曉陽當時說了句話,我還覺得有點不受聽,有人問起他什麼時候結婚,有沒有對象,他說:“怎麼也得比嫂子強啊。
李銀河和王小波合影
李銀河,這位總是和同性戀、性學、女性主義等敏感話題聯繫在一起的學者,其一生在很多人眼裏是驚世駭俗的傳奇。然而,李銀河自己講來卻樸實通透。63歲的李銀河說自己並不算名人,她只是始終堅持了“採蜜哲學”:“人間如花叢,我只是從中採擷一點點精華,對其他的一切不去理睬。一生只有短暫的幾十年,要好好享用自己的生命。”
第二次見面小波向我表白
我第一次見到王小波,是去找他父親請教學問方面的問題。我當時已經留了個心,要看看這個王小波是何方神聖。一見之下,覺得他長得真是夠難看的,心中暗暗有點失望。後來,剛談戀愛時,有一次,我提出來分手,就是因爲覺得他長得難看,尤其是跟我的初戀相比,那差得不是一點半點。那次把小波氣了個半死,寫來一封非常刻毒的信,氣急敗壞,記得信的開頭列了一大堆酒名,說:“你從這信紙上一定能聞到二鍋頭、五糧液、竹葉青的味道,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後頭還有一句話把我給氣樂了,他說:“你也不是就那麼好看呀。”就這樣,心結打開了,我們又接着好下去了。
王小波凌厲的攻勢是任何人都難以抵禦的。他向我表白時,我們只是第二次見面,也是第一次單獨見面。地點是我的辦公室,藉口是還書。那是一本當時在小圈子裏流傳的小說,是個蘇聯當代作家寫的,叫做《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雖然名不見經傳,但是在當時還是很寶貴的。小波一見到我,就一臉尷尬地告訴我:書在來的路上搞丟了。我十分無奈,這人可真行。
後來我們開始聊天,天南地北,當然更多是文學。正談着,他猛不丁問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嗎?”我那時候剛跟初戀情人分手不久,就如實相告。他接下去一句話幾乎嚇我一跳,他說:“你看我怎麼樣?”這纔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啊。他這句話既透着點無賴氣息,又顯示出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和無比的純真,令我立即對他刮目相看。
小波這個人浪漫到骨子裏,所以他才能對所有世俗所謂的“條件”不屑一顧,直截了當憑感覺追求我。從世俗的眼光看,一切“條件”都對他相當不利,我們倆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我大學畢業(雖然只是個“工農兵學員”,但是也勉強算是上了大學吧),他初中沒畢業;我在報社當編輯,他在一個全都是老大媽和殘疾人的街道工廠當工人;我的父母已經“解放”恢復工作,他的父親還沒平反;我當時已經因爲發表了那篇文章而小有名氣,而他還沒發表過任何東西,默默無聞。但是正如小波後來說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締結的。經典的浪漫故事都是兩人天差地別,否則叫什麼浪漫?
我與男版“灰姑娘”結婚了
我和他就是一個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來,我的這個灰姑娘天生麗質,他有一顆無比敏感、無比美麗的心,而且還是一個文學天才,早晚會脫穎而出。
我問過小波:“你覺得自己會成爲幾流的作家?”他認真想了想,說:“一流半吧。”當時他還不是特別自信,所以有一次他問我:“如果將來我沒有成功怎麼辦?”我想象了一下未來的情景,對他說:“即使沒成功,只有我們的快樂生活,也夠了。”他聽了如釋重負。
後來,小波發起情書攻勢。由於我們一週只能見一次,所以他想了個主意,把對我的思念寫在一個五線譜本子上,而我的回信就寫在空白處。這件軼事後來竟成了戀愛經典,有次我在電視上無意中聽到一段相聲,說:“過去有個作家把情書寫在了五線譜上……”那就是我們的故事啊。
經過兩年的熱戀,我和小波結婚了。當時,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許結婚的。但是,由於工作年頭長,他是帶薪大學生,有工作單位可以開結婚證明,這就和一般學生不同了。我們就鑽了這個空子。因爲怕人家深問橫生枝節,我們登記時找的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她當時正好在街道辦事處工作,負責結婚登記。她打個馬虎眼,我們也就矇混過關了。那是1980年1月21日。那個年頭根本不興搞什麼婚禮,只是兩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喫了一頓飯,兩家一共去了十個人,兄弟姐妹都沒去全,也沒有什麼儀式,就跟普通的親戚聚會喫飯一樣。後來我聽爸爸說,他們家給了五百塊錢,我心裏暗暗納悶,爲什麼是他們家給錢,不是我們家給錢?當時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深入學了社會學才悟到,這錢的性質是彩禮啊。
小波的一幫同學朋友還到我家舉行了一個祕密聚會。他們來我家時,其中一位騎着自行車,一手扶把,一手抓着個一人多高的金屬立式衣架,是朋友們湊錢給我們買的結婚賀禮。十來個人圍了一桌子,菜大多是外面買的熟肉和現成的涼拌菜,外加我下廚做了些。不得不慚愧地承認,我的廚藝不咋地。飯後大家嗑着瓜子聊天。記得小波好友劉曉陽當時說了句話,我還覺得有點不受聽,有人問起他什麼時候結婚,有沒有對象,他說:“怎麼也得比嫂子強啊。”曉陽長得是比小波好看多了,也是個大才子,滿腹經綸,小波後來有句話:“曉陽的雜文寫得比我好。”那他也不能這麼說話呀。這句話之所以使我不快,是因爲它有兩重含義:曉陽比我的小波強,曉陽的妻子比我強。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在我心中,小波是完美的,我是完美的,我倆的愛情更是完美的,所謂完美就是到頭了,哪能有比這個還強的?幸虧我不是小心眼,不然就跟他認真生氣了。
去留學瞭解一般人的看法
1982年我整三十歲。俗話說:三十不學藝。可我偏偏在那一年離開我喜歡的工作、新婚燕爾的丈夫、生我養我的中國,遠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去攻讀社會學。
記得寫入學申請時,我的英文半生不熟,所以請一位在北京的美國朋友幫我潤潤色。其中,我解釋自己出國留學動機的一句話令這位朋友大惑不解,我寫的是:“我想去留學,就是想了解一般人對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樣的。”她不明白這怎麼能成爲一個動機。這也難怪,她太不瞭解我的成長環境,太不瞭解當時的中國,太不瞭解剛剛成爲過去的那一段歷史了。
剛剛結束的那場政治運動以及我的青少年時代,對於一個正在摸索人生道路的孩子來說,是多麼讓人困惑啊。周圍的氣氛充滿狂熱、荒謬、扭曲、變態、粗暴、冷漠、無知和殘忍,幾乎每個人都處於半瘋狀態,正常的理智無處可尋。記得小波常引用一句不知出處的話:“人生在世只有兩個選擇,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惡棍。”在那個時代,清醒和善良是多麼稀少啊。因此,我申請去留學,的確是出於這樣的想法——想恢復理智,想了解一下在正常社會中生活的正常人們是怎樣想事情和做事情的。這種想法,那個來自正常社會的美國朋友怎麼能理解呢?
我申請留學還有一點考慮,就是希望吸收到更多的精神食糧。據說美國每人平均耗費的熱能是中國人的三十倍,換句話說,他們的平均物質生活水平是我們的三十倍。但是,我並不太看重這個,畢竟他們每天喫的東西不可能是我們的三十倍,他們的牀也不可能比我們的大三十倍。人的物質需求相差不大,滿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給對我來說沒有意義。更有意義的是精神的享受——深入心扉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以及所有的虛構之美,包括音樂、美術、戲劇以至優雅的生活。
申請順利成功,我獨自前往異國他鄉。飛機在匹茲堡降落,深夜的機場有一種輕輕柔柔的背景音樂,帶點異國情調,給剛剛離鄉一日的我帶來一絲淡淡的鄉愁。我不知道等候着自己的將是什麼樣的生活,但我感到這又是我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未來無論怎樣,都將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希望即將開始的這段生活是光明、快樂、色彩斑斕的,而不是晦暗、鬱悶、委瑣的。
在新奧爾良見識裸體舞
留學生的生活很清貧,也就是將將過得去吧。那幾百美元獎學金剛剛夠喫飯和房租,我一個人的時候還好,兩年之後,小波辦了陪讀,只是免學費,沒有生活費,兩個人花那一點獎學金就有點捉襟見肘了。於是,我們倆都打一點工。我每週有一天時間在一家飯店裏當服務生,那家飯店很有意思,是臺灣人開的,卻叫“北京飯店”。小波因爲英文不好,在後廚刷碗,還跟一個上海人一起去幹過一陣裝修房子的活兒。
小波還在底層街區遭遇過打劫。有一天打工回來的路上,有個瘦骨嶙峋的老美攔住他要錢,小波說:“我沒錢。”那人指指他鼓鼓囊囊的上衣兜問:“這是什麼?”小波老實告訴他:“是煙,不是錢包。”老美說:“那就給支菸吧。”小波就給了他一支菸,打發他走了。小波後來分析,他碰上的一定是個癮君子,情急之下才會打劫。
儘管生活拮据,我和小波還是設法省錢遍遊美國,甚至遊了歐洲。這在那個時期的留學生中並不多見,就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老一輩留學生也很少有能力去遊歐洲。匹茲堡大學地理系的一位華裔老教授對我們這種做法頗不以爲然。他當年留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一點點奮鬥成功,我們在匹茲堡大學時,他已經快到退休年齡了,房子、車子、老婆、孩子和終身教職全都有了。在他看來,我們還沒有什麼正經收入就花錢去旅遊,純屬不務正業,太過奢侈。其實,旅遊不一定就是奢侈,富有富的遊法,窮有窮的遊法。爲什麼窮人就不可以旅遊?我和小波從結婚起就沒打算要孩子,除了兩人的喫住也沒啥花銷,省喫儉用攢的錢基本就都用在了旅遊上。
第一次是小波來美國的次年,他哥哥小平到新奧爾良的圖蘭大學讀書。我們約好先去新奧爾良看小平,然後三人一起去佛羅里達玩兒。
新奧爾良是一個法國味道很重的城市。奧爾良是法國的一個城市,後來很多人移民到美國,按照他們的風俗習慣來建立這個新城,所以叫新奧爾良。法國社區窄窄的街道上有黑人音樂家在吹薩克斯,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所謂藍調音樂,感覺怪怪的,說不上好聽難聽,只是覺得異國風情十分濃烈。
我們在那一條條小街上信步遊覽,沿街都是各色店鋪,琳琅滿目。我平生第一次見識了裸體舞酒吧,那些舞者被叫做“go-go-dancer”,她們一點也不美,因爲不是什麼高尚的地方,按幾率也不會有太出色的姑娘。小平和小波還好,我在那個酒吧裏就太尷尬了,這不是女人來的地方嘛。我們只在裏面待了一小會兒就落荒而逃了。
小波是詩人,走得也像詩人
1996年10月,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原定時間是一年,可是在做了半年之後,忽一日接到好友林春電話,說小波出事了。雖然當時沒有人告訴我出的什麼事,只是說病了,但我有了很不好的預感。從接電話開始,一直到登機回國,我的心跳一直很快,心裏發虛,全身像要虛脫一樣。在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沈原說了一句話:“小波是個詩人,走得也像詩人。”我就一下全明白了。我現在不願回想,那些日子我是怎樣熬過來的。
小波過世之後,我有一天翻檢舊物,忽然翻出一個本子,上面是小波給我寫的未發出的信,是對我擔心他心有旁騖的回應:“……至於你呢,你給我一種最好的感覺,彷彿是對我的山呼海嘯的響應,還有一股讓人喜歡的傻氣……你放心,我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全搞不到一塊,尤其是愛了你以後,對世界上一切女人都沒什麼好感覺。”
憶起我們橫穿美國的旅行;憶起我們共同遊歷歐洲,飽覽人文風光;憶起我們回國後共同遊覽過的雁蕩山、泰山、北戴河,還有我們常常去散步作傾心之談的頤和園、玲瓏園、紫竹院、玉淵潭……櫻花盛開的時節,花叢中有我們相依相戀的身影;秋葉飄零的時節,林間小道上有我們隨意徜徉的腳步。我們的生活平靜而充實,共處二十年,竟從未有過沉悶厭倦的感覺。平常懶得做飯時,就去下小飯館;到了節假日,同親朋好友歡聚暢談,其樂也融融。生活是多麼美好,活着是多麼好啊。而小波竟然能夠忍心離去,實在令人痛惜。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們曾經擁有過這一切。
我現在想,我的小波他也許在海里,也許在天上,無論在哪裏,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也不乏艱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經歷了愛情、創作、親密無間和不計利益得失的夫妻關係,他死後人們終於發現、承認、讚美和驚歎他的天才。我對他的感情是無價的,他對我的感情也是無價的,世上沒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