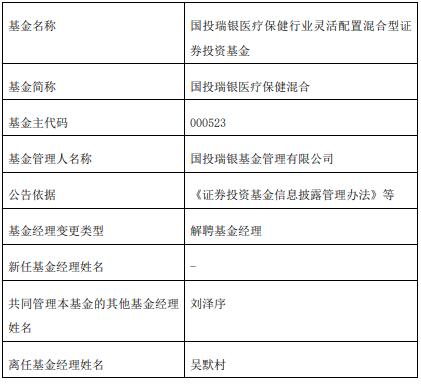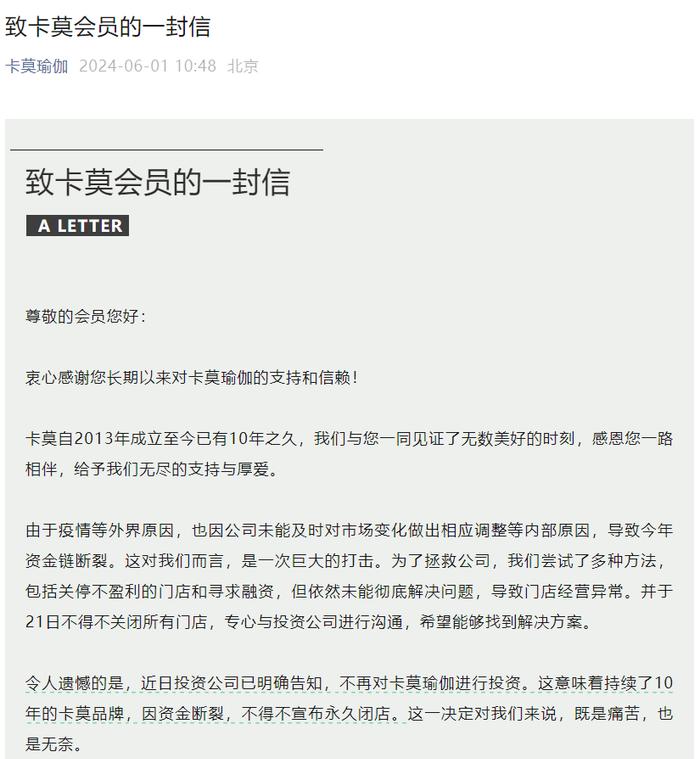北京的十萬種百年煙火味道
作者:劉暢·摩登中產
來源:格隆匯
蒸騰熱氣中,仍留着規矩和敬畏。
一
百年以來,北京煙火氣中,一直藏着複雜的味道。
燉菜裏煮着關外的風雪,糕點裏裹着江南的精緻,從燕山撲下的長風,掠皇城,穿衚衕,最後繚繞銅鍋之上,化作氤氳熱氣。
冀北的憨厚混合皇城根的自得,形成特有的北京味道,那味道不光有舌尖味,更有人間義。
在中國,文化常有兩種傳承,一種寫進書本,一種散落民間。文字是易碎品,但煙火中的文化,卻能傳承千年。
老北京飯館棲身市井,煙火氣中常藏着失傳的義氣。
京劇名家馬連良在飯館用餐,北平警備司令小舅子與人爭搶雅間,鳴槍鬧事。馬連良去說和,飯館免遭事端。
抗戰勝利,國民黨要員構陷馬連良通日,佔據馬宅索要財物,還得供喫供喝。每晚打烊,那家飯館的大廚,都不顧疲倦主動趕去作夜宵,爲朋友解憂。
煙火氣中,亦藏着久違的規矩。
北京東城東興樓,如果客人敲盤催菜,跑堂要扛着鋪蓋卷,從客人面前跑過謝罪。
爆肚老店金盛隆從不打折,客人給小費,前廳後廚會一起跟着喊,謝謝爺。那是祖傳的禮貌。
喫慣霸王餐的巡警,結賬時把警哨往桌上一摔。老闆面不改色,直接收走。店雖小卻見慣風浪,京城鉅富那桐,張學良的親戚都是常客。
南城的烤肉宛同樣有規矩,客人領號等座,過號不候。日僞時期,大漢奸王克敏攜小妾前來,嫌門口喧鬧,鑽回車裏等位,錯過了號。
把門老闆認號不認人:照顧您,對別人不公平,不能壞了規矩。
王克敏黑下臉,要手下砸場。混亂中,店裏走進日本憲兵隊的隊長,一樣乖乖排隊拿號進來,王克敏悻悻離去。
作家侯磊形容那時的北平,“無論有錢沒錢,都講禮義廉恥,都一樣喝豆汁兒”。
解放前,餐館夥計稱醋爲“忌諱”,而不直接問您喫醋麼。孩子們談及長輩,用“怹”敬稱“他”,用“恁”敬稱“你們”。表達答謝,有勞駕,費心,破費多種措辭。
80年代,蕭乾感慨,很多禮數都被“修”掉了,人們連“謝謝”也不說了,還得成天在廣播裏教。
那些最後的傳統,還是在煙火氣中頑強地傳了下去。
爆肚老店金盛隆已經傳到第四代,依然貫徹着老輩的囑咐,一不漲價,二不打折,三是不發“貴賓卡”。
老闆說,來的客全一視同仁,不分三六九等。
那些客人慢慢成了家人。在北京惠豐餃子樓,有位80多歲的常客,早晚一碗餛飩,中午要二兩餃子,每天雷打不動。
後廚只要看到單子上寫“高老爺子”,便自知餡料、火候與鹹淡。
老人熟識店裏的每個面孔,有人請假,他會問:小王怎麼沒來。進了門,他先要在店裏轉一圈,和所有人打完招呼再坐下。
每逢節日,他必會買好煙和水果送來。過年,一定要爲餐館的年輕服務員發紅包。
不收,他眼睛一瞪,呦,看不起我?
即便煙塵氣辛辣嗆口,也透着禮。
二
煙火氣中,不斷融進新風味。
1983年,法餐餐廳馬克西姆在崇文門開業。穿過旋轉門拾階而上,燈光昏黃柔和,兩側壁紙都摹自盧浮宮的名畫。
那幾年,崔健常在這裏抱着吉他,爲外國客人演唱。還和餐廳老闆的女兒,一位保加利亞的混血姑娘,談了一場戀愛。
那個時代的青年,渴望外面的世界,而那時的北京,也敞開懷抱。
1988年,東直門內大街還不叫簋街。第一家24小時營業的曉林餐廳,亮着夜色裏唯一的燈火。
僅僅幾個月後,屋外坐滿飢腸轆轆的外國人,能一直等到凌晨3點。有北京老饕,從太陽宮騎行1個多小時過來。
1995年,三里屯有了第一家酒吧,刷夜過後的潮流青年們,湧向這裏慰藉空虛的腸胃,年輕的慾望融進了古都的夜色。
各地口味不斷融合。北京人開的金鼎軒,菜品涵蓋了粵式點心和淮揚菜。花家怡園改進北方的燉法,做出火爆一時的魚頭泡餅。
北京是個移民城市,口味多元,時常能創造新菜品。
2003年,受到街區改造和非典的影響,簋街不少餐館生意凋零。有人偶然看到報紙上的江蘇龍蝦節,便牽頭提議效仿。
第一屆簋街龍蝦節期間,每晚7點前後,整條街便瀰漫着麻小的味道。等餐的食客與車輛佔據馬路,出租與公交都無法停靠。
這座城市從不排斥新的味道。
它包容街角的成都小喫和萬州烤魚,也吸收口味清淡的沙縣小喫,更不用提個性粗獷的蘭州拉麪。
隨着城市化浪潮席捲而來,無數打工者湧向首都。
1997年,葉小虎從河北來到北京的北新橋滷煮店。21年過去,他成了廚師長,和北京老闆金鵬遠“就像搭夥過日子一樣”。
每天打烊,他都會從湯鍋中取一碗老湯,第二天兌入新煮的食材,無論大小腸還是肺頭,都被熬得軟爛濃郁。
來北京的第一天,他就喜歡上這碗濃湯。不同的人、各異的文化,也融入了滷煮的香氣。
有的哥進門就問,今天的腸洗得乾淨麼,夥計說,沒洗的還給您留着呢。“成,必須沒洗的,乾淨的不好喫”。
也有人穿着西服,自帶刀叉,一板一眼地分割大腸和肺頭,然後用銀勺喝湯。走之前,對老闆說了句“good night”。
相同的是,碗底的湯都已喝得精光。
30年間,人們的收入有了高低之分,但味蕾卻從未分出階層。
北太平橋下阿香的宵夜攤前,曾同時停着賓利、奧迪與奧拓。大車司機在煙塵中吞嚥炒餅,金融街的投資人則握住一把烤串,談着幾百萬的生意。
阿香說,王健林也來過兩次,喫完,他從車窗裏遞過四五千元的小費,讓她買件衣服。
曾在保利劇院門口烤串的老李,甚至不知道範冰冰曾經光顧,還一手握串,一手攥紙巾,拍了照片。
超跑俱樂部的成員把蘭博基尼和法拉利停在路邊。著名導演蹲在攤前喫相狼狽,網紅們提着裙子,滿嘴流油。
後來因爲城管嚴查,老李搬到了五環外。重回工體西街開店時,保利俱樂部已被查處關閉,女神久違露面。
街頭依舊熙熙攘攘,很快有新食客融入夜色,開啓新的故事。
三
融匯四方味道的北京,進入了互聯網時代。
北新橋滷煮老店的玻璃窗內,師傅寫意地揚起右手,菜刀刀把朝天,嗤地釘進案板。舉着手機的觀者肉眼高潮,贊出一聲“講究”。
當年老闆曾夜市擺攤,口碑全靠食客口口相傳。如今,客人多是從大衆點評慕名而來的年輕人。
他們拍下老湯徐徐入碗的視頻,發到抖音上,引來更多人氣。
此前,謝霆鋒帶着十多個人來到店裏,爲美食節目取景。照片通過微博傳遍網絡,還有00後好奇留言,這是香港的牛雜麼?
幾年前,老北京人,想要滿足舌尖的記憶,需要長途跋涉。
從朝陽紅廟拆遷離去的老爺子,要坐數站公交,只爲故地紫光園的一口炒疙瘩。
不少因拆遷遠赴天通苑或海淀的居民,每週都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地鐵來惠豐餃子館喫餃子。
有年冬至,一個老主顧一口氣買下20斤餃子,要帶給來不了的老街坊嚐嚐。
2016年,惠豐餃子館與美團點評合作,開啓外賣業務。小哥們進店的催促聲,爲店裏帶來新的熱鬧。
不到年底,店裏已賣出35萬份餃子,比去年翻了一倍多。
那些穿着黃衣的外賣小哥,穿行於這座古老的都市,送去十萬種味道。
時代變了。過去,每當桌上剩下菜品,店長都要找廚師問責,開會討論原因。“客人的口味說變就變,尤其是年輕人”。
如今,大衆點評的留言成了最及時的反饋。
去年,一篇《北京,有2000萬人假裝生活》刷屏,作者說,這裏僅存的煙火氣只屬於坐擁五套房的老北京。
其實煙火並未消失,只是變換了形態。煙火中有規矩,亦有潮流。
兩年前,稻香村有店面恢復了久違的炸肉串。消息刷遍朋友圈,引發80後集體出動,追憶兒時味道。
幾平米的門臉一天能賣出一萬串,因爲隊伍太長,每天只放100張號。
用醬汁在餅皮作畫的煎餅,捲進了雞排和小龍蝦。靈感取自驢打滾的糯米果,成了帶娃母親賺外快的副業。昨天還在刷屏的奶茶店,今天就開到衚衕口。
從BAT離職的創業者,帶着流量思維,把西安的肉家饃開進了北京的各大商區。撩撥90後小確幸的喜茶,把數百米的長隊帶到了SOHO樓下。
幾年前,北京人劉婕從外企離職,開了衆宜軒老北京涮肉。
她在高碑店租下雕樑畫棟的院落,紅牆青瓦的大門口,特意不掛招牌。大衆點評上,幾乎所有網友都會留下一句“費了好大功夫才找到”。
久而久之,這成了無形的口碑。酒香不怕巷子深。
新舊口味,傳統現代,在北京上空交融,形成這個時代的味道。
最終,它們會融進北京的十萬種味道之中,並衍生出新滋味。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