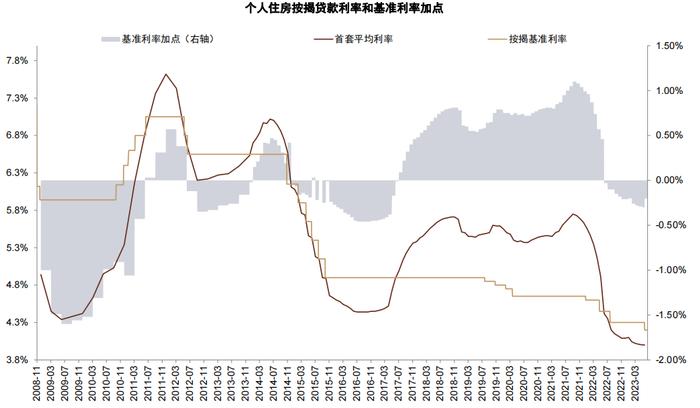[生活隨筆] 不用“格子”,如何讓辦公空間隱祕起來?
現在年輕人夢想的辦公環境,或多或少都以Google總部爲原型。在創造力稀缺而珍貴的當下,Google由於爲員工提供開放創意型的辦公空間,被大衆想象爲獲得商業成功和員工滿意度雙贏的標杆企業。
再看另一些年輕有爲的公司,Instagram、Twitter,無不是開放辦公空間的擁躉,一些企業甚至還有極大的室外辦公區域,工作看上去就像聚會一樣輕鬆愜意。
相應地,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佔據寫字樓格局絕對主流的“格子間”(Cubicle)型辦公室,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實質上,都被淘汰了。
歷史總是循環的,格子間曾經就像如今的Google辦公室一樣,可是一個“革命者”:它試圖改變的,是一種更爲原始的大通間。早期的開放型大辦公室其實是公司等級制度的直接表現:一排排工位密密麻麻,進門處的位子屬於級別最低的員工,級別越高的員工工位離管理者越近,然而整個辦公室都是缺乏隱私的,管理者擁有能夠監視整間辦公室的獨立房間,祕書坐在門口,扮演着守門人和傳話人的角色。
1968 年,美國密歇根州赫爾曼·米勒研究公司(Herman Miller Research Corporation)的設計師羅伯特·普羅普斯特(Robert Propst),設計了一套組裝辦公桌,桌面上設置了能夠展開的隔斷,這就是現在爲大家所熟悉的“格子間”的發端。普羅普斯特的本意是通過一套方便組裝的預製件,使辦公環境更加靈活,並且鼓勵員工在這個屬於自己的、有一定隱私性的小空間裏,改變久坐不動的狀態,疲憊時可以自在地活動身體。不過,隨着經濟的發飛速展,白領人數的爆發式增長,普羅普斯特的設計反而成爲公司單位空間使用率最大化的工具,“格子間”一個接一個排滿辦公樓,成了“封閉、狹小,製造壓抑”的代名詞。
據調查,如今發達國家的絕大多數公司都已經拋棄“格子間”,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嘗試將辦公室打造成“開放辦公空間”,一些小型創業公司,乾脆直接租用聯合辦公空間。但我自己作爲公司的管理者,除了關心這一趨勢之外,更關心年輕員工是不是真的喜歡這樣的開放空間。做了小範圍問詢之後,我發現,原來不少所謂的“開放辦公空間”,不過是“一夜回到50年前”罷了——隔斷是消失了,卻完全沒有在隱私性和公共區域的利用上有任何進步。有人告訴我,公司只是簡單地擺了一些餐桌般的大號桌子,讓幾個員工圍坐在一起,這導致大家工作時都不好意思抬頭,因爲太容易和坐在對面的同事四目相對,實在太影響工作專注度了。他們對我說,與其這樣,還不如坐回格子間。
的確,開放辦公空間聽上去容易,實踐起來卻很難。這背後是公司所要求的共同體、效率和個人所追求的隱私、自主之間的平衡問題。還有公共區域,如商討重要問題與接待客戶的會議室、供員工隨時討論問題的沙發區等等設置在哪裏、如何佈置,纔會得到有效利用,都是很大的學問。
K11 Atelier 就是以重新定義現代辦公空間爲初衷而設計的新型辦公樓。我們通過對建築細節、燈光、空間、景觀的把握,營造出融合藝術美感和工作室匠心的氛圍。如果有機會在K11 Atelier工作,我希望大家都能體會到設計者的用心,「In Art We Work」。
*圖片來自網絡
查看原文 >>